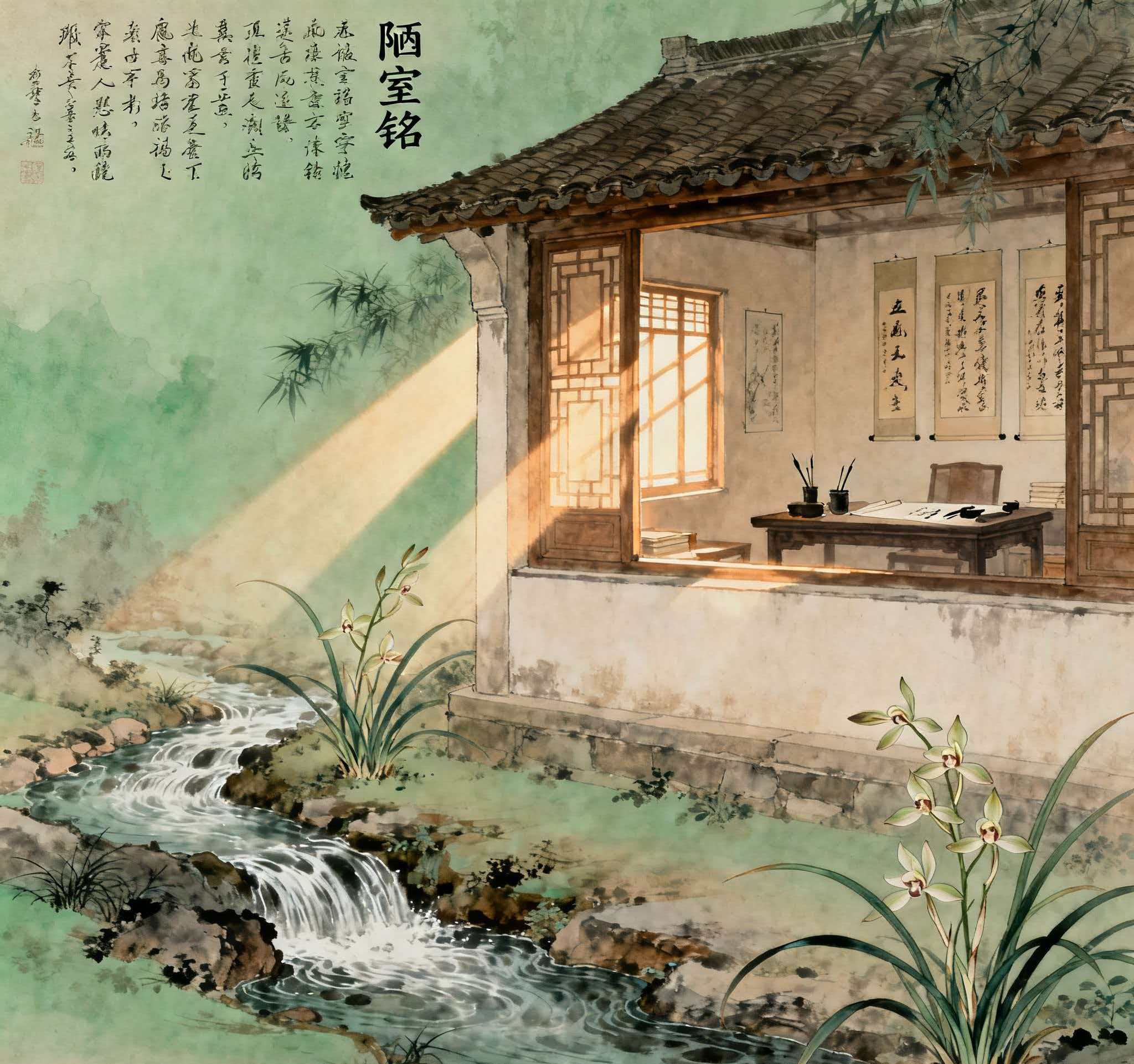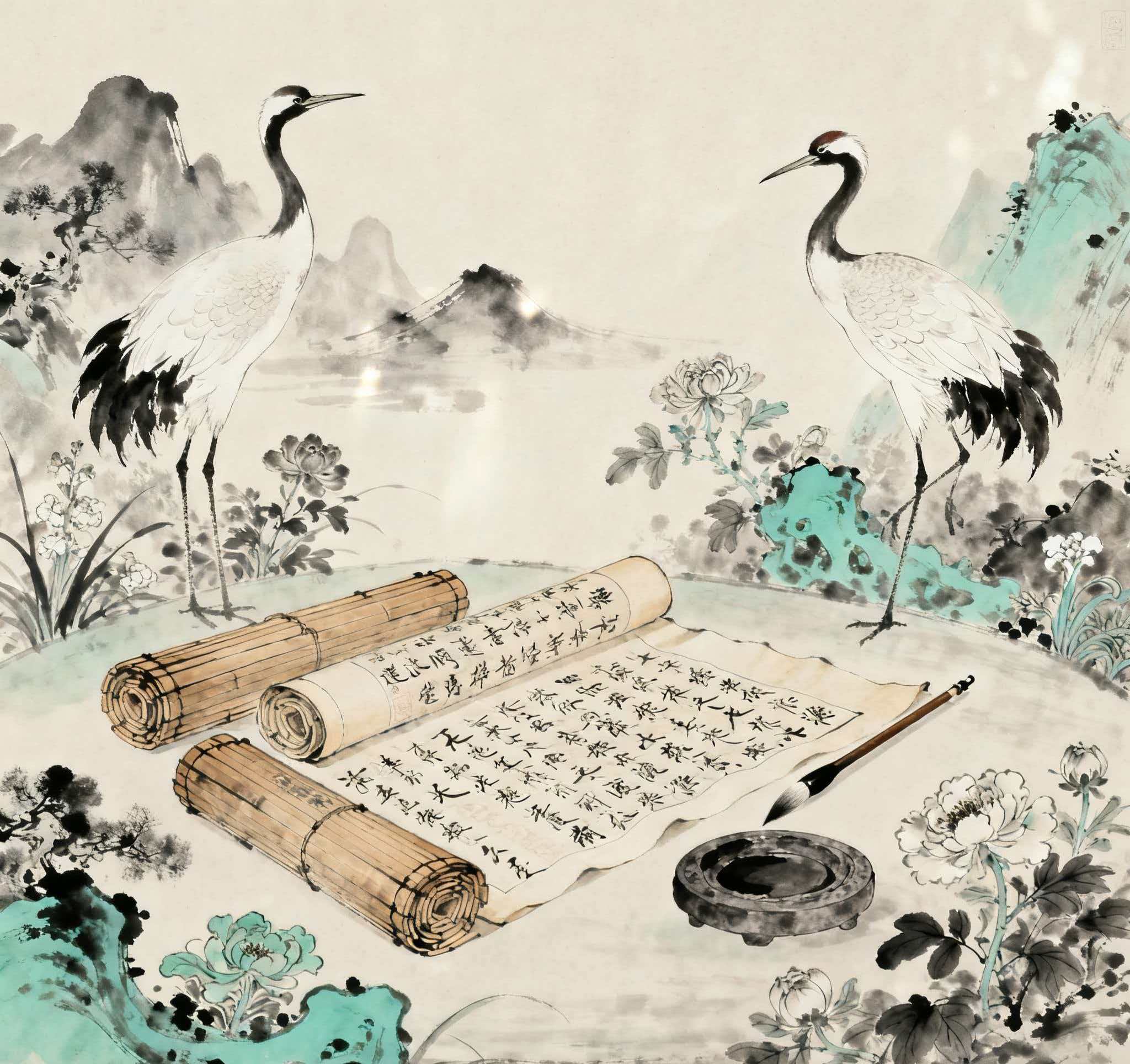小说:红烛

红烛的光在窗纸上晃,把苏晚的影子拉得细细长长。她指尖攥着真丝睡裙的下摆,指腹蹭过绣着的并蒂莲,连呼吸都放得轻。
门轴“呀”地响了声,陆时衍走进来。他刚送完最后一波宾客,墨色西装上还沾着点酒气,却先伸手把窗台上的风灯调暗了些——怕那光太亮,晃得她不自在。
“累了吧?”他声音比平时低,带着点哑。苏晚抬头时,正撞进他眼底的光,那光里没有宴席上的应酬,只有她熟悉的温软。她摇摇头,却没忍住往后缩了缩脚,拖鞋上的珍珠扣轻轻磕在地板上,发出细碎的响。
陆时衍没再往前走,反而拿起桌边的茶盏,倒了杯温好的蜂蜜水递过来:“先喝点,解解乏。”杯沿碰着她的指尖,温热的触感顺着指尖往上爬,苏晚的耳尖一下子就红了。
她小口抿着茶,余光瞥见他在解领带,手指骨节分明,动作慢得很。红烛噼啪响了声,溅出个小火星,苏晚吓了一跳,手里的杯子晃了晃,茶水差点洒出来。
陆时衍立刻伸手扶住杯底,指尖不经意蹭到她的手,两人都顿了顿。他先笑了,声音里带着点无奈的温柔:“别怕,就是烛花。”说着,他拿起银剪,轻轻剪掉烛芯上的黑结,火光顿时亮了些,把他的侧脸照得格外清晰。
苏晚放下杯子,忽然想起下午化妆师说的话——新婚夜的红烛要烧到天明,这样往后的日子才会红火。她偷偷看他,看他把剪下来的烛芯放在碟子里,看他转身时衣摆带起的风,心里像揣了只小兔子,蹦得厉害。
“在想什么?”陆时衍走到她面前,微微俯身。他的气息里有酒气,也有她喜欢的雪松味,混在一起,让她心慌意乱。苏晚咬着唇,小声说:“在想……烛火会不会真的烧到天亮。”
他笑了,伸手轻轻碰了碰她的发顶,动作温柔得像在碰易碎的珍宝:“会的。”他顿了顿,目光落在她泛红的眼角,又补充道,“而且往后的每一天,都会像今晚的烛火一样,暖烘烘的。”
红烛的光映在两人交握的手上,苏晚看着他无名指上的戒指,和自己的凑在一起,刚好是一对。窗外的夜很静,只有烛火偶尔的噼啪声,和两人渐渐平稳的呼吸声,缠在一起,成了往后无数个日夜里,最温暖的开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