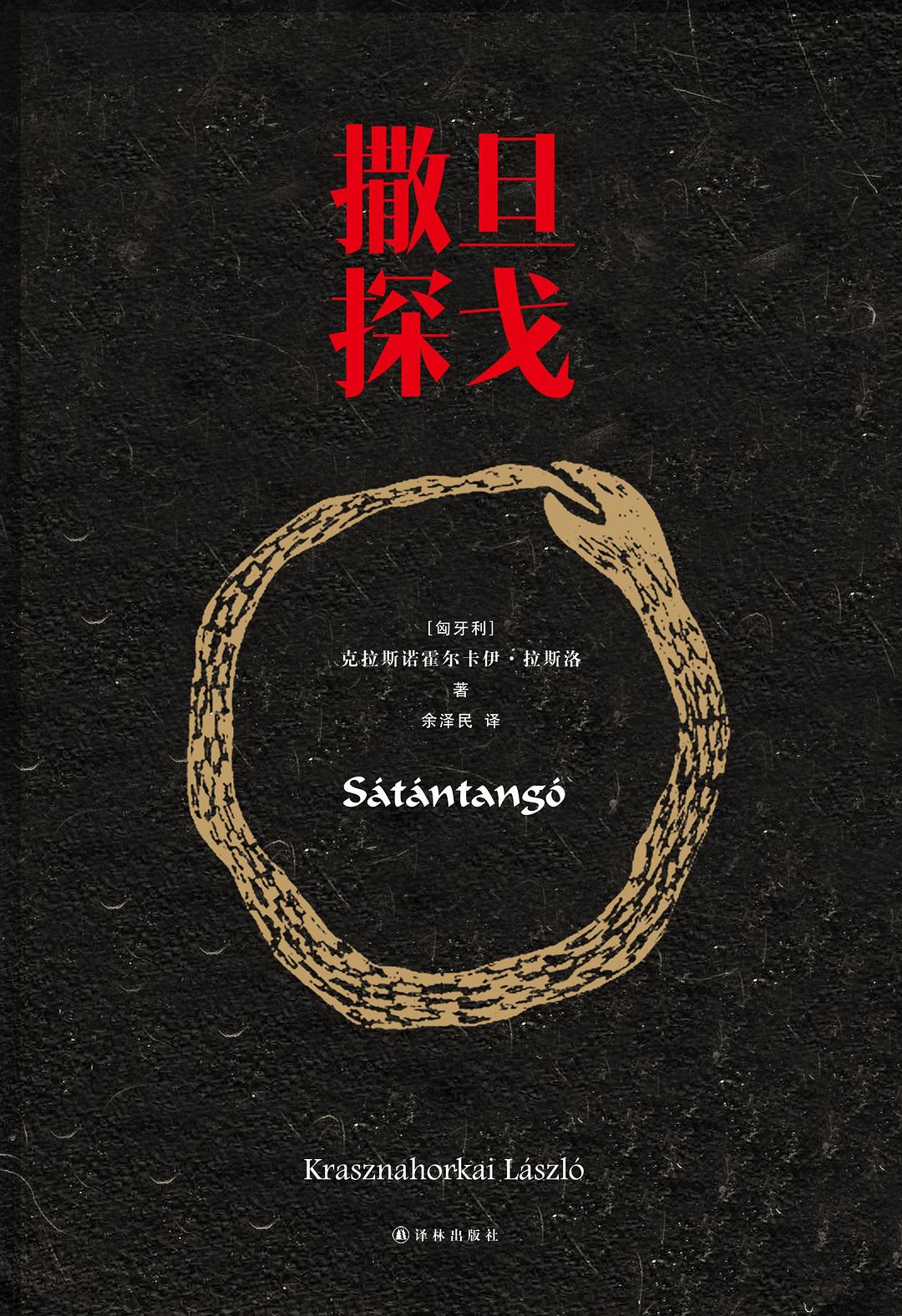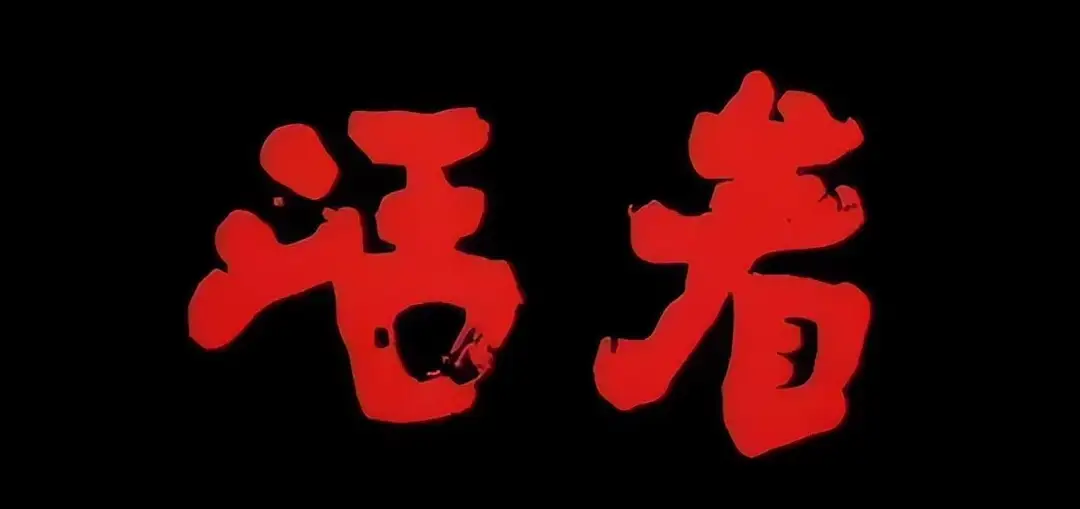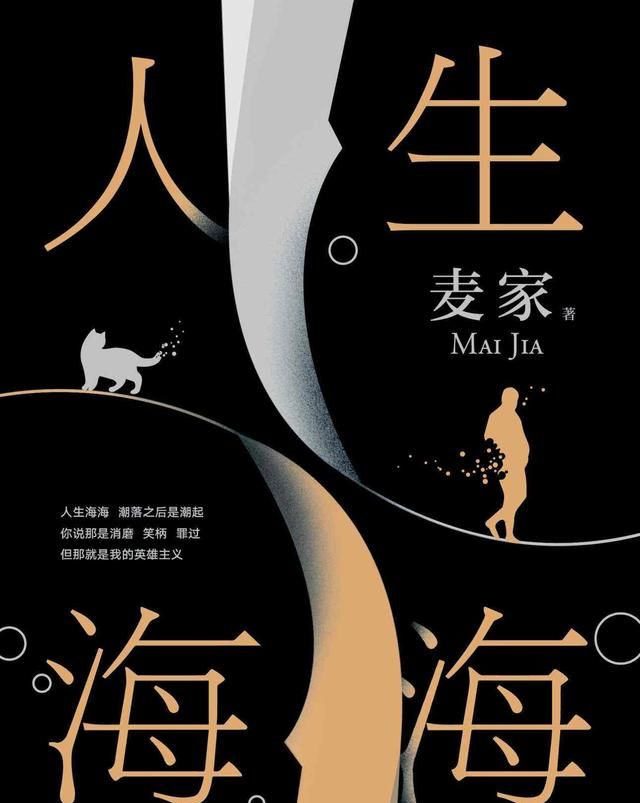河水流过的文明印记——《额尔古纳河右岸》书评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从不是一本单纯的“部族史”,而是用诗意的笔触,为我们展开的一幅鄂温克族在大兴安岭深处,与驯鹿、森林、风雪共生的文明长卷。当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用一生的记忆串联起部族的兴衰——从狩猎迁徙到定居转型,从萨满跳神到现代文明的冲击,额尔古纳河的流水,不仅带走了岁月,更承载着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对传统的坚守与对命运的从容。
书中最动人的,是迟子建对“人与自然共生”的细腻描摹,每一笔都浸着大兴安岭的凛冽与温柔。鄂温克人以驯鹿为伴,跟着它们追逐苔藓的踪迹迁徙:春天把营地扎在向阳的山坡,看驯鹿啃食新生的灌木;冬天躲进背风的河谷,用松枝燃起篝火,听风雪拍打着桦皮帐篷。“我”的父亲是技艺精湛的猎手,能从雪地上的脚印判断熊的踪迹;母亲擅长鞣制鹿皮,缝出的靴子能抵御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萨满妮浩为了拯救族人,一次次献祭自己的孩子,萨满鼓的声响在森林里回荡,既是与神灵的对话,也是对生命的敬畏。这些场景没有刻意的猎奇,却让我们看见:在远离城市的森林里,生活不是“原始”的代名词,而是人与万物相互依存的智慧——驯鹿提供衣食,森林给予庇护,鄂温克人则用“不滥杀、不掠夺”的规矩,守护着自然的平衡。
而小说最深刻的,是对“文明消逝”的温柔叹息,却从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对过往的深情回望。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伐木声打破了森林的宁静,公路修到了营地边缘,年轻一代开始向往城市的生活:“我”的儿子安道尔离开森林去城里上学,回来后再也不习惯睡在桦皮帐篷里;族里的人陆续搬去政府修建的定居点,只有“我”和少数人还守着最后的驯鹿群。迟子建没有指责“变迁”的对错,只是平静地记录:曾经用来传递信号的篝火,渐渐被手机取代;曾经热闹的氏族聚会,慢慢变得冷清;曾经能听懂驯鹿语言的猎手,越来越少。这种“平静”里藏着巨大的伤感——不是对现代文明的抗拒,而是对一个民族独特生活方式逐渐远去的不舍。就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无论如何奔流,都带不走那些刻在血脉里的记忆:萨满的鼓声、驯鹿的铃铛声、族人围坐篝火时的笑声。
书中的“人”,更是森林里最鲜活的风景,每个人都带着自然赋予的坚韧与纯粹。酋长瓦罗加沉稳睿智,在部族面临迁徙与定居的抉择时,始终守护着族人的意愿;萨满妮浩一生都在“牺牲”,却从没有抱怨,她说“神灵选中我,是让我替族人承担苦难”;“我”的丈夫拉吉达,在一次狩猎中为了保护驯鹿,永远留在了暴风雪里,可“我”想起他时,最先浮现的不是悲伤,而是他笑着递给“我”一块烤鹿肉的模样。这些人物没有“英雄”的光环,却有着比英雄更动人的生命力——他们接受自然的馈赠,也承受自然的考验;他们珍惜生命的美好,也坦然面对死亡的降临。在他们眼里,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回到森林的怀抱”,就像落叶归根,驯鹿归林,是自然轮回的一部分。
迟子建的文字,带着大兴安岭特有的“冷”与“暖”——冷的是风雪的凛冽、文明的消逝,暖的是人与人的牵挂、人与万物的温情。她写雪:“雪下得很大,像无数只白蝴蝶在空中飞舞,落在驯鹿的角上,像开了一朵朵白花”;她写驯鹿:“它们低头啃食苔藓时,睫毛上挂着霜,看起来像温柔的老人”;她写族人的离别:“安道尔走的时候,抱着我哭,说‘妈妈,我会回来的’,可我知道,森林留不住他了”。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额尔古纳河的流水,缓缓淌进心里,带着淡淡的伤感,却也有着治愈的力量。
合上书时,仿佛还能听见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还能看见驯鹿群在雪地里留下的一串串脚印。《额尔古纳河右岸》从来不是要“挽留”什么,而是要“记录”什么——记录一个民族曾经的生活,记录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相处方式,记录那些在时光里渐渐模糊,却不该被遗忘的文明印记。它让我们明白: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温度,每一段过往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像额尔古纳河,无论流向何方,都永远记得自己的源头。这,便是迟子建留给我们的礼物: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慢下来,去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去珍视那些即将逝去的美好。
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从不是一本单纯的“部族史”,而是用诗意的笔触,为我们展开的一幅鄂温克族在大兴安岭深处,与驯鹿、森林、风雪共生的文明长卷。当最后一个酋长的女人“我”,用一生的记忆串联起部族的兴衰——从狩猎迁徙到定居转型,从萨满跳神到现代文明的冲击,额尔古纳河的流水,不仅带走了岁月,更承载着一个民族在时代浪潮中,对传统的坚守与对命运的从容。
书中最动人的,是迟子建对“人与自然共生”的细腻描摹,每一笔都浸着大兴安岭的凛冽与温柔。鄂温克人以驯鹿为伴,跟着它们追逐苔藓的踪迹迁徙:春天把营地扎在向阳的山坡,看驯鹿啃食新生的灌木;冬天躲进背风的河谷,用松枝燃起篝火,听风雪拍打着桦皮帐篷。“我”的父亲是技艺精湛的猎手,能从雪地上的脚印判断熊的踪迹;母亲擅长鞣制鹿皮,缝出的靴子能抵御零下四十度的严寒;萨满妮浩为了拯救族人,一次次献祭自己的孩子,萨满鼓的声响在森林里回荡,既是与神灵的对话,也是对生命的敬畏。这些场景没有刻意的猎奇,却让我们看见:在远离城市的森林里,生活不是“原始”的代名词,而是人与万物相互依存的智慧——驯鹿提供衣食,森林给予庇护,鄂温克人则用“不滥杀、不掠夺”的规矩,守护着自然的平衡。
而小说最深刻的,是对“文明消逝”的温柔叹息,却从没有激烈的控诉,只有对过往的深情回望。随着现代文明的渗透,伐木声打破了森林的宁静,公路修到了营地边缘,年轻一代开始向往城市的生活:“我”的儿子安道尔离开森林去城里上学,回来后再也不习惯睡在桦皮帐篷里;族里的人陆续搬去政府修建的定居点,只有“我”和少数人还守着最后的驯鹿群。迟子建没有指责“变迁”的对错,只是平静地记录:曾经用来传递信号的篝火,渐渐被手机取代;曾经热闹的氏族聚会,慢慢变得冷清;曾经能听懂驯鹿语言的猎手,越来越少。这种“平静”里藏着巨大的伤感——不是对现代文明的抗拒,而是对一个民族独特生活方式逐渐远去的不舍。就像额尔古纳河的水,无论如何奔流,都带不走那些刻在血脉里的记忆:萨满的鼓声、驯鹿的铃铛声、族人围坐篝火时的笑声。
书中的“人”,更是森林里最鲜活的风景,每个人都带着自然赋予的坚韧与纯粹。酋长瓦罗加沉稳睿智,在部族面临迁徙与定居的抉择时,始终守护着族人的意愿;萨满妮浩一生都在“牺牲”,却从没有抱怨,她说“神灵选中我,是让我替族人承担苦难”;“我”的丈夫拉吉达,在一次狩猎中为了保护驯鹿,永远留在了暴风雪里,可“我”想起他时,最先浮现的不是悲伤,而是他笑着递给“我”一块烤鹿肉的模样。这些人物没有“英雄”的光环,却有着比英雄更动人的生命力——他们接受自然的馈赠,也承受自然的考验;他们珍惜生命的美好,也坦然面对死亡的降临。在他们眼里,死亡不是终点,而是“回到森林的怀抱”,就像落叶归根,驯鹿归林,是自然轮回的一部分。
迟子建的文字,带着大兴安岭特有的“冷”与“暖”——冷的是风雪的凛冽、文明的消逝,暖的是人与人的牵挂、人与万物的温情。她写雪:“雪下得很大,像无数只白蝴蝶在空中飞舞,落在驯鹿的角上,像开了一朵朵白花”;她写驯鹿:“它们低头啃食苔藓时,睫毛上挂着霜,看起来像温柔的老人”;她写族人的离别:“安道尔走的时候,抱着我哭,说‘妈妈,我会回来的’,可我知道,森林留不住他了”。这些句子没有华丽的辞藻,却像额尔古纳河的流水,缓缓淌进心里,带着淡淡的伤感,却也有着治愈的力量。
合上书时,仿佛还能听见额尔古纳河的流水声,还能看见驯鹿群在雪地里留下的一串串脚印。《额尔古纳河右岸》从来不是要“挽留”什么,而是要“记录”什么——记录一个民族曾经的生活,记录人与自然最本真的相处方式,记录那些在时光里渐渐模糊,却不该被遗忘的文明印记。它让我们明白:每一种文明都有自己的温度,每一段过往都有自己的价值,就像额尔古纳河,无论流向何方,都永远记得自己的源头。这,便是迟子建留给我们的礼物:在快节奏的时代里,慢下来,去倾听那些被忽略的声音,去珍视那些即将逝去的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