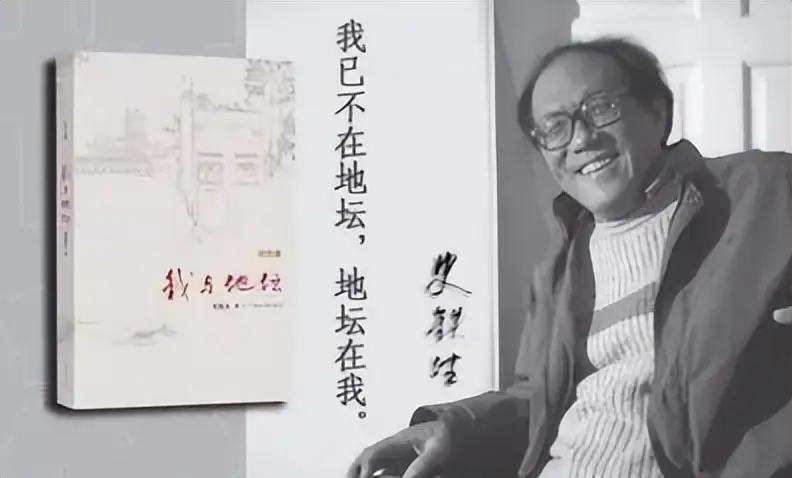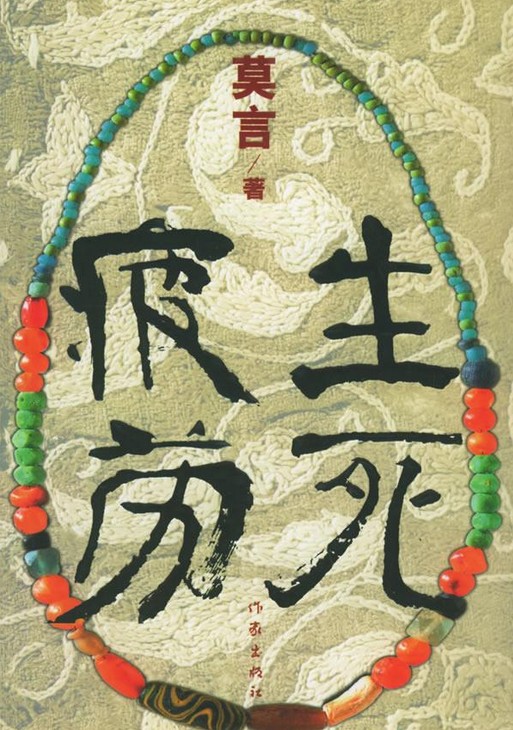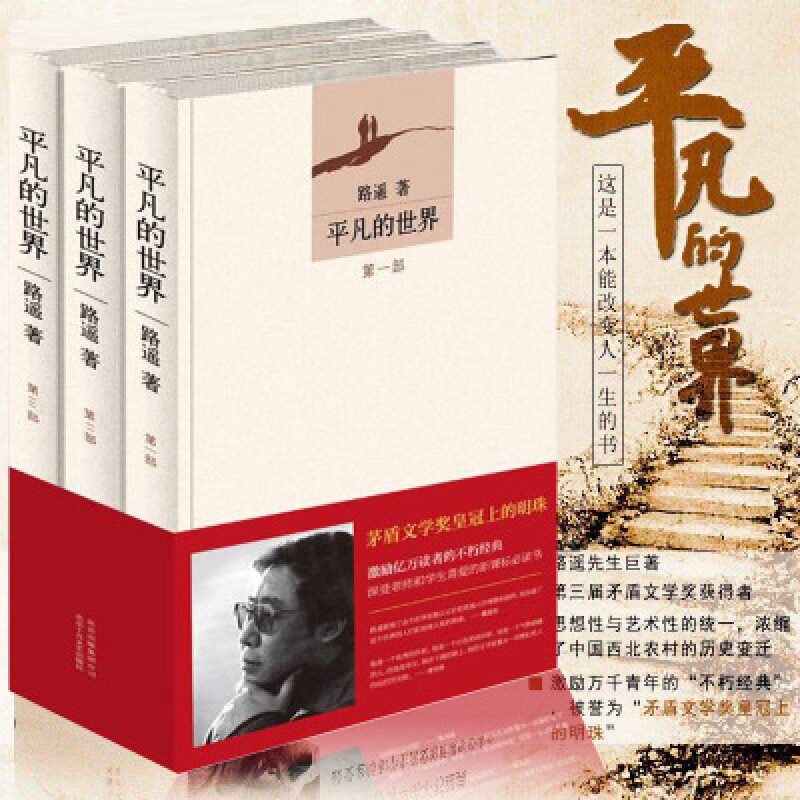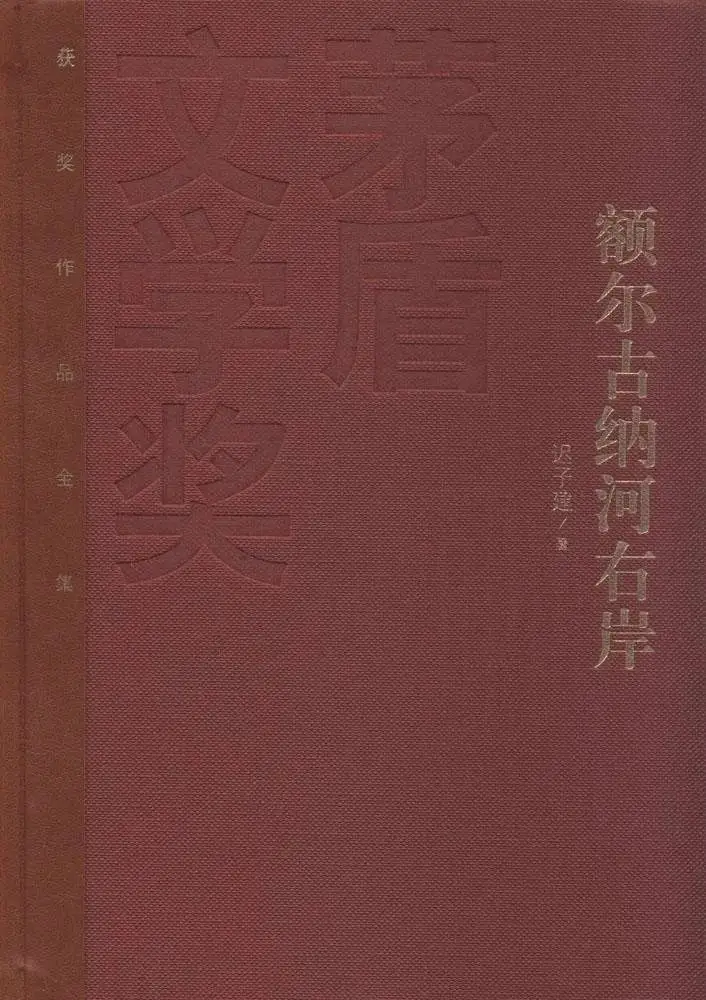书虫眼里的文明年轮——评《蟫》的历史叙事与文献之美
当一条以书为食的红蟫,成为跨越百年的历史见证者,崔欣的《蟫》便在虚构与真实的交界处,搭建起一座连接古籍与当代的桥梁。这部融合了文献考据与文学想象的作品,用独特的双重视角,让被时间掩埋的藏书往事重新焕发生机,也为读者打开了一扇窥探古典文献世界的小众窗口。
小说最精妙的设计,在于“蟫”这一叙事载体的选择。红蟫以百年寿命栖身《慈云楼藏书志》,它啃食的是纸页,更是书页间凝固的时光——从兵荒马乱中藏书的流散,到同族在现代化防虫手段下的消逝,它的记忆既是个体的生存史,也是一部微观的藏书文化兴衰史。这种以“非人”视角观照人类文明的写法,既避开了传统历史小说的宏大叙事套路,又让冰冷的古籍背后的人事温度变得可触可感,当红蟫的记忆与文献学硕士小施的考证相互印证时,历史不再是遥远的文字,而是有情感、有遗憾的鲜活过往。
而作品的另一重魅力,在于其对“文献学”这一冷门领域的真实还原。作者并未将古籍研究简化为情节背景,而是将版本比对、稿本溯源的专业过程自然融入故事——小施从研究《郑堂读书记》未果,到转向名不见经传的《慈云楼藏书志》,其间对文献流传脉络的梳理、对藏书家生平的考证,都透着严谨的学术质感。这种“专业”并未构成阅读门槛,反而让“书海探案”的过程充满张力,读者既能跟随情节感受历史的厚重,也能在不经意间收获古籍版本学的基础知识,正如复旦大学吴格教授所言,实现了“古典文献学素养”与“感性审美体验”的双重收获。
更难得的是,小说在历史与现实的对照中,埋下了对“文明传承”的深层思考。当现代化图书馆的恒温恒湿环境让红蟫成为“最后一只书虫”,当纸书在数字时代逐渐边缘化,《蟫》所书写的不仅是过去的藏书故事,更是对“如何保存文明记忆”的追问。红蟫用生命延续的记忆,小施用学术守护的文献,本质上都是对文明根脉的坚守——藏书家的私人情怀、研究者的专业执着、甚至书虫的本能依赖,最终都指向同一个主题:文明的延续,需要有人记得那些被遗忘的细节。
或许正如短评中读者所言,有文献研究背景的人会更易与书中内容产生共鸣,但即便不懂版本学,也能被红蟫的坚守、藏书家的遗憾所打动。《蟫》的价值,就在于它用文学的温柔,包裹了学术的严谨,让那些躺在图书馆深处的古籍,以及背后的人与事,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毕竟,每一部被遗忘的典籍,都是一段等待被唤醒的文明记忆,而每一个愿意倾听这段记忆的人,都是文明的守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