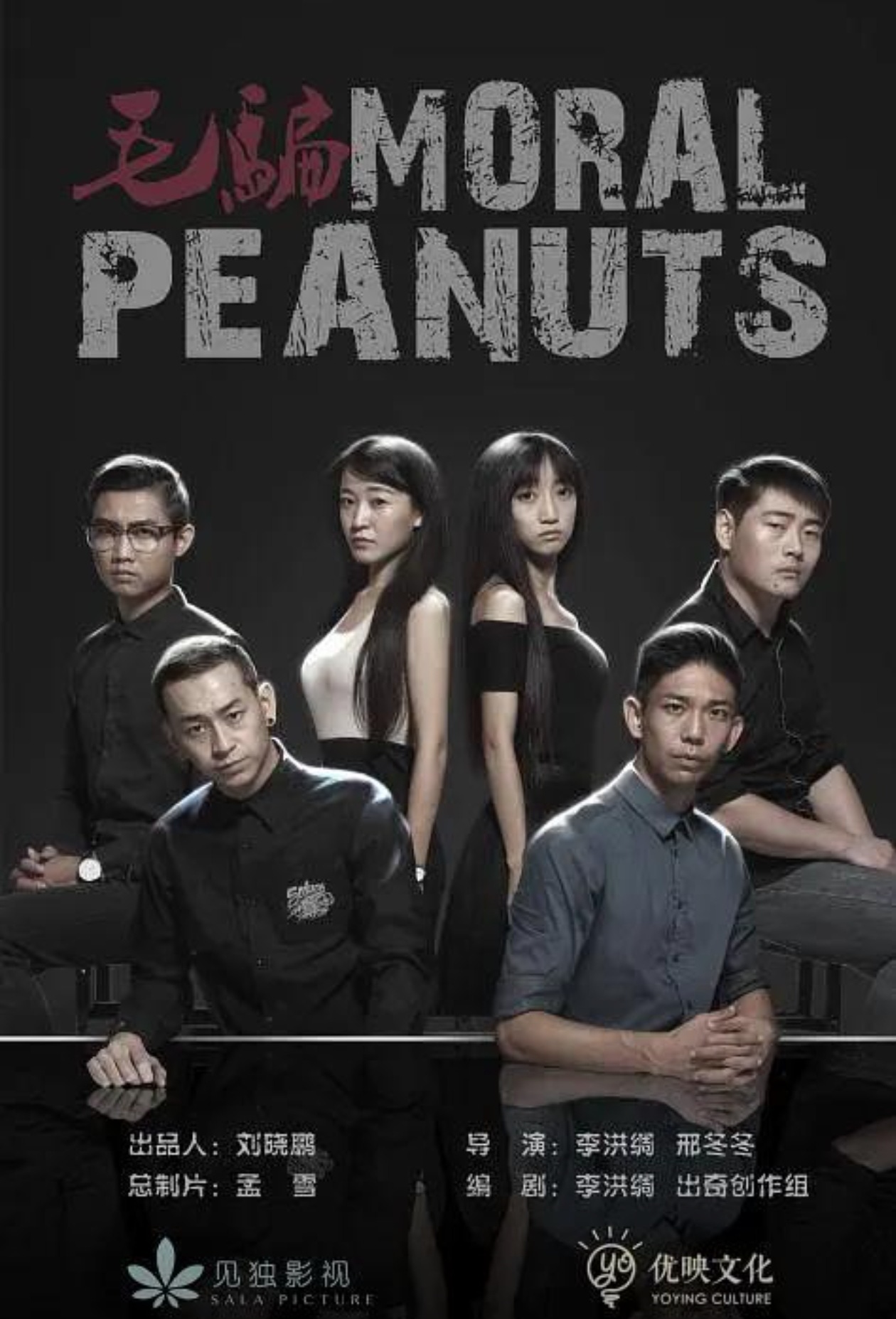影史迷梦与感官诗学:毕赣《狂野时代》的百年叩问

当银幕上舒淇饰演的“大她者”将胶片植入易烊千玺所饰“迷魂者”的脊背,那个“人类不再做梦”的未来世界里,一场跨越百年的光影幻梦就此开启。毕赣时隔七年带来的《狂野时代》,早已超越个人记忆的呢喃,以“眼耳口鼻身意”的六识架构为骨,以影史脉络为血,在商业与艺术的张力间,完成了一次对电影本质的狂野追问。 一、角色共生:在规则与叛逆间照见电影灵魂 毕赣用双主角的镜像关系,搭建起影片的核心叙事张力。易烊千玺的“迷魂者”是电影艺术的肉身化身——这个被称作“电影怪兽”的存在,肉身沉睡百年,灵魂却在多重梦境中穿梭,从默片时代的杂耍艺人到民国谍影中的追凶者,从深山还俗的小和尚到对抗异化的叛逆者。他的表演剥离了偶像光环,在不同时空的身份切换中,用蜷缩的脊背、迷茫的眼神与爆发式的反抗,精准诠释了艺术在规则夹缝中的挣扎与坚守。当他在30分钟长镜头里带着吸血鬼少女奔逃向海边晨光时,每一步都踏在“梦境不死”的信念上。 舒淇的“大她者”则是拉康理论的完美具象化。她既是摄影机与导演的象征,用达盖尔银版照相机捕捉影像,用旁白把控叙事节奏,如同毕赣本人在幕后构建着这场百年幻梦;又是规则的维系者,潜入梦境追捕“迷魂者”,试图唤醒这个打破“时间单向流动”秩序的叛逆者;更藏着“原初大他者”的温柔,为“迷魂者”穿戴特效妆容时的专注,恰似电影艺术对创作者的滋养与塑造。而赵又廷的特邀出演、李庚希的特别亮相,以及黄觉、陈永忠等“毕赣宇宙”常客的加持,让每个角色都成为影史碎片的承载者,在梦境中完成与经典的对话。 二、感官建构:在光影细节中复活电影记忆 毕赣从未停止对视听语言的实验,此次更是将“通感”美学推向极致。影片以六识划分篇章,让每个感官都成为通往影史的通道:视觉篇里,清末戏院的微缩模型复刻着梅里爱的《月球旅行记》,默片式的光影呼应着《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的表现主义风格;听觉篇中,被拆解重组的合唱声轨随角色浮现分层流淌,特雷门琴的空灵声响暗喻着艺术坚守的稀缺;味觉篇的深山庙宇里,小和尚敲下的牙齿与苦妖幻化的父亲身影,让“苦”成为记忆最真切的味道。 那些标志性的毕赣式符号在此获得新生:燃烧的树不再只是毁灭的象征,更暗合民国默片向有声片过渡的产业革新,以火焰的动态对抗永生世界对时间的消解;镜子铺的对峙戏致敬《上海小姐》的镜像迷宫,破碎的镜面既映照出角色的身份迷茫,也暗喻传统与革新的碰撞;而贯穿始终的旧钟表、KTV场景与贵州方言的余韵,则让宏大的影史叙事始终扎根于可触摸的情感土壤。长达30分钟的一镜到底更是神来之笔,镜头跟随角色从魅惑密室穿入逼仄街巷,最终抵达晨光中的海边,将梦境的连贯与现实的断裂熔于一炉。 三、时代叩问:当电影成为做梦的最后权利 “人类不再做梦”的设定,是毕赣对当下的精准隐喻。当AI与商业逻辑不断压缩艺术的生存空间,“迷魂者”的执着便有了沉甸甸的现实意义——他沉迷梦境并非逃避,而是在守护人类最珍贵的感知能力。影片中,“大她者”从追捕者到理解者的转变,恰是艺术对规则的温柔征服:当她看见“迷魂者”在梦境中品尝的苦痛与甜美,终于明白电影不是虚幻的泡影,而是“复活生命经验的容器”。 毕赣的“狂野”,在于他敢于用艺术电影的骨架承载影史的重量。从复刻《水浇园丁》的经典桥段致敬电影诞生,到用胶片植入情节隐喻创作本质,影片的每处细节都在回应“电影是什么”的终极命题。结尾处,蜡烛剧院在燃烧中坍塌,闪着光亮的观众逐渐融化,既是对“观众远离影院”现状的哀思,也是对电影不死的信念宣言——正如毕赣所说,他希望观众带着“复活的做梦能力”回到生活中。 这部获得戛纳特别奖的作品,或许仍会因碎片化叙事引发争议,但它无疑是一封写给电影的情书。当最后一帧光影消散,那些关于记忆、感知与坚守的碎片,早已在观众心中拼贴成答案:电影从来不是被动接收的产品,而是让人类在无梦时代依然能触摸灵魂的永恒梦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