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指 月 街
文丨冉正万
嘈杂的嗡嗡声降下去,主持人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介绍他时特别强调,不要看他右手,也不要被他右手的故事左右,一定要好好看他的作品。这是农业产品外包装设计展示年会,设计师坐在各自的展台前,展台上摆放着他们最新设计的作品。他是近年炙手可热的设计师,是业界风向标。多年前一次事故中,他失去右手。当时作为还没出道的青年设计师,这无疑是致命打击。他不气馁,用左手学会写字画图,几年后重新亮相,在设计大赛中一举夺魁。其后屡次获奖。事故变成故事,总是能给当事人加分。同行虽有不服,却又不得不服。获奖和一只手比起来,宁愿要手不要奖。当别人问他,用左手是不是反而比右手容易。他作了肯定回答,却又害羞似的脸红。坊间传言,他左手每个指头都是一个小脑袋,五种想法可以同时出现在设计图上,他可任意挑选一种,还可同时交出五种设计方案。
当年,他一边自学设计,一边在工厂当检修工。一次正在检修,没人告诉刚换班的操作工,一来就合上电闸,叶片刹那间高速旋转,只听见嗞的一声,缩回右手发现手短了一截。他捡起断手就往医务室跑,希望他们立即送他去医院。医务室的实习生倒也麻利,骑上电摩就走,还叫人从背后扶住他。到了医院,医生说不能接,断手落在油污里,裹满了废机油,清洗后组织受损,不能用。医生建议他用别人的手,前提是有人愿意捐赠遗体。他的期待落空后只好装了个假肢。
他不苟言笑也不合群,每次年会结束都不留下吃饭,不像其他同行那样互加微信,酒至酣处称兄道弟,强调合作。强调合作并非全是酒话,行业不景气时合作是现实需要。他们以为他不参加是因为自卑,因为他总是将断手藏在身后或袖子里。有人像哲学家一样说,他对他的设计有多自信,对自己的断手就有多自卑。有人出于同情真诚地邀请他和大家聊聊天,他像不食人间烟火似的婉言拒绝。越是这样,别人越容易记住他。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嗜好的残疾人会让人莫名忌惮。毫无偏见的客气让人不舒服,除此之外又别无他法。
“回去干什么呢?看书吗?”
在同辈心目中,五个脑袋暗含讥讽,他不可能混饭吃,只有一只手嘛,肯定比其他人刻苦。付出已经得到回报,但要稳居一线,非博览群书不可。青灯孤影,苦思冥想,寻找被别人漠视的细节和表现手法,既能勾起人的欲望又有道德感,让视觉冲击不仅成为一种策略,还要达到人们想要但无法实现的效果。对已经完成的作品从不满意,永远只为下一个杰作苦心孤诣。待人接物有些冷漠,这是为了用全部热情照亮自己的创作。
是不是这样呢?他没说过。
他总是穿一件宽大的中式对襟盘扣上衣,瓦灰色,其他人这么穿会被当成装模作样,在他则被理解为方便隐藏假手。衣服式样和颜色,与他不苟言笑的稳重很匹配,像真正的艺术家。比他年轻的设计师都崇拜他,视他为楷模,尤其是出身卑微的新手,认准不努力决不可能成功,笃信天资必须建立在勤奋的基础上才坚实,才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从小衣食无忧不为生计发愁,仅仅出于爱好的从业者则无所谓甚至不以为然,对地方性年会也不重视,对成名的渴望不强烈,让天分在松弛的构想里滑翔,灵感有可能凝结成钻石,也有可能烟消云散。后者往往只闻其名,很少见到其作品。他似乎产量颇高,又受当地媒体追捧,作品常常出现在地铁LED屏上,DM杂志上。某位后浪看见,会检讨自己上次见面是否向他问过好,如果没有问好,那可真是太糟了。和行业外的朋友谈起他时津津乐道,其实连他住在哪里都不知道。

他住在哪里(住在什么样的房子里),家庭关系如何,孩子多大。虽然心里痒痒的想知道,但最终以尊重他人隐私的善意按下了好奇心。从参会材料看,他不属于任何公司,以个人工作室、独立设计师名义活动。他是只有一个士兵的将军,这又给他添上一层神秘色彩。
不过,所有的传奇都不得不让位于他那只手。就像谈论一道菜时,你不得不顺便谈到盐,有盐才有味道。有两个说法最有趣。一是说他在医院里并非没找到“手源”,当时就找到了,是一只上了年纪的男性的手。医生给他接上后,外观差别很大,他很不喜欢。最让他难堪的是,有一次他发现这只手摩挲着一颗麻将,他不知道它从哪里得来,摩挲了多久。当愉悦感传递到心里时,他极其反感并觉得恶心。他讨厌打麻将,父母都喜欢,经常邀人在家里打,打完就吵或者边打边吵。他从小觉得麻将脏,那么多人天天摸,汗味、唾沫,还有人边打边吃东西,麻将从来不洗。毕竟是手术连接的手,通畅性大大降低,指挥它做什么倒也没问题,可它自作主张做了什么常常在预料之外。有一次他正画图,感到右侧身体焦虑不安,停下来才知道是右手在搞鬼。它不愿意空着,要拿个东西才舒服,给它笔没兴趣,给它橡皮没兴趣,直到从垃圾桶里找出丢掉的麻将,它才像见到亲人一样激动得浑身哆嗦。最后发展到睡觉要拿着麻将,吃饭要拿着麻将,上厕所也要拿着麻将。像面和心不和的伴侣,让他烦不胜烦,只用左手就能像常人一样生活,留之何用?于是痛下决心将它截掉。第二个说法是医疗事故,医生错将一只少妇的手给了他,它倒是挺关心他的,给他夹菜,温柔地抚摸他的脸,小便时拿着那个东西不放。最大的麻烦是影响工作,不管左手有没有空,它会突然伸过来,拿起左手搓揉,甚至希望十指相扣。为了事业,他不得不忍痛弃之。
这类故事是同行相聚时抢话题和打趣的佐料,而情节每次都朝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总能让人忍俊不禁。任何创作都不是创作,是为了消遣抖机灵。换句话说,他们不是对他这个人感兴趣,而是对他的故事感兴趣。人之于社会不是看他作出过什么贡献,而是他有无让人可以改编重写的故事。
知道他的人当中,被他勤奋打动的不止一个。但愿意深挖他故事的只有一个人。这人是电视台下面的文化公司的运营总监。文化公司也搞设计,运营就是干杂活,负责联络协调。这个工作很适合她。她敏感又爽快,聚会时笑声像水晶玻璃一样明亮爽朗。同行知道她的一切,第一任丈夫是被人抛弃后带着孩子跟她结婚的,第二任没有孩子,但有一堆债务。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爱说谎,却抱怨自己上了女人的当。两次婚姻都让她蒙羞。从不堪的状态走出来后,发誓再也不卷入别人龌龊的生活,不再成为悲剧和闹剧的主角。尽管如此,她依然保持着善良与尊严,始终怀着希望,再怎么心烦意乱也对弱者寄予最大同情。在这种性格怂恿下,找到空隙后马上过去和他说话。
“你好。”
他点了点头。
调皮的大眼睛闪着笑意:“你快乐过吗?你什么时候最快乐?”
“照镜子的时候。”
“为什么?”
“我的左手变成了右手。”
有人过来向他索要资料,她笑着走开。他很机智,她想,继而觉得不但机智,还很豁达。平时点头之交,从没有深入交谈过。她为曾拿他开玩笑感到惭愧,现在决定弥补。她问他要不要参加主委会的晚餐。这是明知故问。他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不去。她说,我也不想去,我们去找个小地方坐下好吗?他回答一个字:行。她没有把握却又愉快地遐想,我会变成他的镜子吗?
她没有征求他的意见,将会面地点安排在指月街赛维利亚,从凯宾斯基出来右转五十米就到。指月街给人阴沉沉的感觉,街道窄,两旁楼房又高,像终年见不到阳光的峡谷。赛维利亚是休闲简餐厅,老火车卡座似的隔间,适合两个人小坐。吃什么她一向颇有主张,平时自我标榜是路盲(仿佛漂亮的人儿必须是路盲),对美食地图的熟悉程度却远远超过道路。乘电梯时只有她和他,不锈钢轿箱照见两人身影,她的心莫名地跳了一下,脸上泛起不易让人察觉的红晕。不锈钢板分了三截,上下光滑如镜,中间加镂花蚀刻,镜像因此模糊不清。她有意看了看他的双手,自己的双手,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她还是碰碰他的肩膀,意思是看啦,我们的左手变成了右手。他笑了笑,心领神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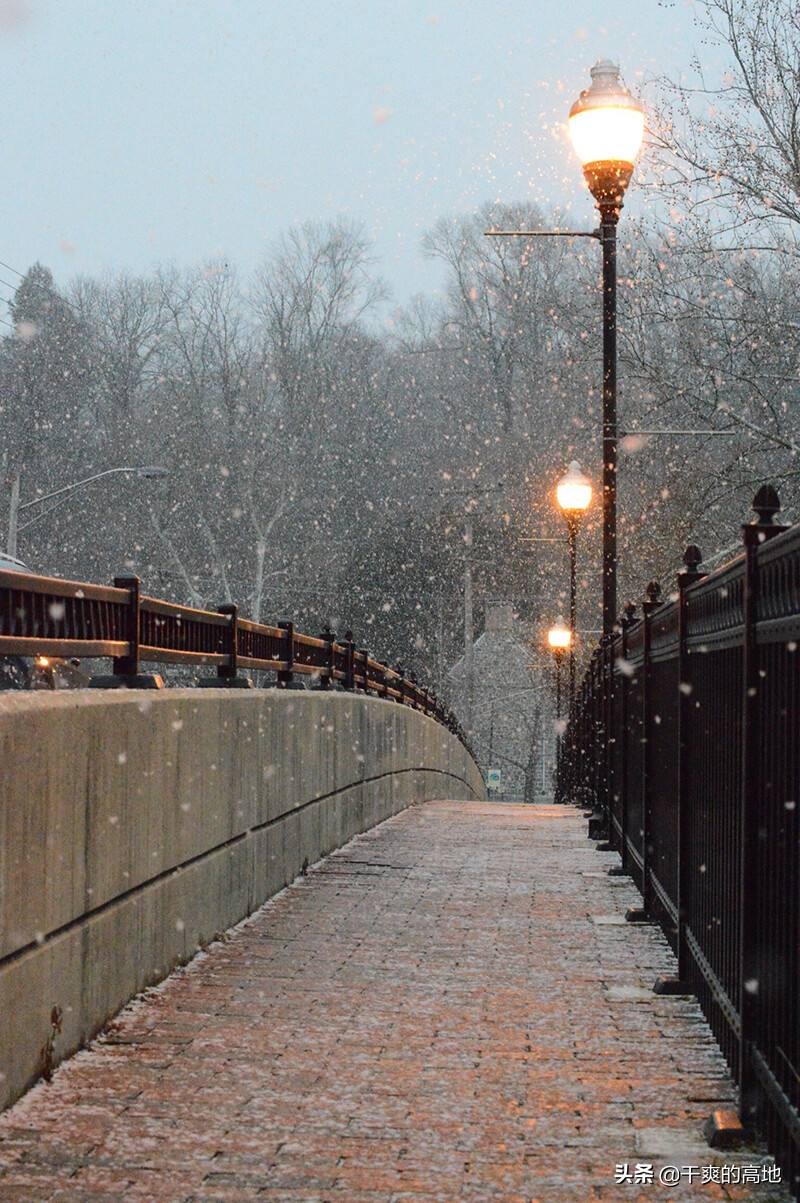
“你喜欢照镜子吗?”
“很少。”
电梯在一楼打开时,斜对面立着一面有放大功能的穿衣镜。她没看见,他则看到镜子里有一张熟悉的面孔,直到坐在赛维利亚,他才想起那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怎么不像自己熟悉的自己呀?
她给他调蘸碟,夹菜,不是因为他右手不方便,而是出于对人一贯的礼貌。他把右手藏在桌子底下,一次也没拿出来。不过他的左手怎么也不如从小习惯用左手的人熟练,好几次夹在筷子上的菜中途落到桌子上,像经不起狐狸夸赞的乌鸦。她看不下去,隔着桌子喂他,他则尽量躲开,声称自己能行。桌子太宽,他不配合,她就无法将蘸了酱汁的东西送进他嘴里。她不无嗔怨地问,你怕遇见熟人吗?不是,他说,只有即将被卖掉的牲口才会被强行喂食,他不想被卖掉。她说你又不是牲口,笑着把煮好的虾滑夹进他的蘸碟,并建议他用勺子。他没用勺子,用筷子把它叉了起来,看着多余的酱汁往下滴,最后一滴摇摇欲坠,“我喜欢这种感觉,”他说,“多么神奇,颜色下面深上面浅,但并非静止不动,内部上上下下,在一滴小小的蘸水里沉浮。”“你喜欢从生活里找灵感?”“是的,不过我更喜欢生活本身。”说到设计,他说最期待的设计是简单而又容易复制的那种,走到哪里都能看见,“像看到亲人一样,多幸福呀。”比如日本人村上隆的太阳花,连小孩都会画,自从诞生以来,全世界无处不在,珠宝、坤包、腕表、汽车摇头太阳花摆件和香水瓶,无不与标志的太阳花联名。二〇一一年夏天谷歌首页,二〇一二年梅西百货庆祝表演都用上了太阳花。现在太阳花已经走出时尚圈,进入流行文化的众多角落。她举起水杯和他碰了一下,“你也有出圈那一天。”结账时,看见吧台上有一个太阳花笑脸,两人相视而笑。她自然而然地勾起他的手臂,依偎着走到街上。
由玻璃衍生出的镜子比比皆是,伪装成各种饰物或符号的太阳花一眼就能看出来,平时很普通的街景顿时生动,镜子诡谲多变,太阳花天真活泼。人来人往,除了她和他,没人看见什么镜子和太阳花。她从那些镜子里看到的全是变形人,包括她自己,她觉得有趣,仿佛看到人的多面性和可塑性不但可在同一时间里显现,还具有无限可能性。镜子里的形象不像人也不像所知之物,没有定性,变化无常,只有挽在手里的人实实在在。她笑着看了他一眼,挽得更紧了。他没看见她的笑容,也没感觉到手上的力量加重。他在想一会儿怎么办,带她回住处是否急了点。如果他误会了她的友情,今后相处可就太难堪了。而她有意却被自己拒绝,又会让她心头不爽。总之处理不好大家都会尴尬。他有点后悔和她吃饭,当时应该找个理由回家,不过,他平时就觉得她漂亮、热情,幻想过此情此景,只是没料到真会发生。他最快乐的时候不是照镜子,是设计交付后甲方爽快结账。照镜子和太阳花是他无聊时看手机看到的内容,没想过要说给谁听,更没想到她会如此感兴趣,错把他当成有见地的设计师。他想告诉她,我和那些参加年会聚餐的人没什么区别,他觉得唯一值得夸耀的,是知道自己几斤几两,有自知之明。
他住华宫巷公寓,从指月街步行只用八分钟就到。公寓层高五米五,买下来后自己加楼板,下面做工作室,上面阁楼里住人。只有四十多平,但对一个设计师来说足够宽敞。她对房间的布置大加赞叹,他却关灯不让她看,说一会儿再看。既然来到了这里,就不应该有所顾虑,他想。身体也在提醒他催促他拥抱探索抚摸,做此时此刻最应该做的事情。她吃吃笑,说没想到你这么急迫。她没有反对,叹息说好久没这种感觉了。他牵着她的手带她上楼,她感到小小的恐惧和刺激。阁楼上没窗户,不开灯像墨水瓶里一样黑,还感到窒息。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不应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她想。她感觉他很体贴,对他“很久没做这种事”表示理解和同情。他要做什么会先问一声,可以吗?她鼓励他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他依然彬彬有礼。毕竟是艺术家,不像其他人那样毛手毛脚。她先是感到满足,渴望,既而感到神奇。接下来却越来越觉得不对劲。他的指头仿佛长了眼睛,指肚长了嘴,大鱼际像活蹦乱跳的小鱼,小鱼际像长了羽毛,指肚和掌丘则像装了弹簧的小球。这让她感到非常不自在。仿佛它们在窥探她的皮肤,他的手指游走到哪里,哪里就会即将化掉似的承受不住。虽然什么也看不见,却能预感到他的手下一步将落到哪个部位,未落将落之前,这个部位情不自禁地一哆嗦,一种莫名其妙的难受,被鱼吮吸似的不痛不痒,明知小鱼没有牙齿也没有毒,不可能咬人,可怎么也不放心,那毕竟是一张吧嗒不停的嘴。她想叫他停止,却又不好意思开口,毕竟不是在抓在掐在咬,是在认认真真悄无声息地抚摸。她想起她抓到过的一只蝴蝶,她一点伤害它的意思也没有,恰恰是因为喜欢它才捉住它,可它不停地挣扎,挣断了翅膀落到地上再也飞不起来。当时觉得抱歉,深感内疚,不能因为喜欢就抓在手里呀。我成了他手里的蝴蝶了吧,她在什么也看不见的床上嘲笑自己。不行,我必须阻止,再这么下去会断气,会难受死。被挠胳肢窝的孩子会笑得浑身发软,碰到不是敏感区的手臂或肚子都会忍不住笑,继而手指不用触碰,只要做个挠痒动作,他就会笑得咯咯叫并求饶。她现在不但浑身发软,还感到恐慌,他的手越来越像从洞穴里钻出来觅食的动物,灵活、迫切、小心翼翼却又经验十足。不行,我不能让自己的翅膀断掉。像即将淹死的人作最后努力,她猛然从他怀里挣脱,凭着本能寻找开关。不是求生似求生,嘴里咕哝着,灯呢?灯呢?这一幕给她留下难以磨灭的印象,在今后的梦境里会反复以各种形式出现。就要淹死时,她无意中碰到开关。

灯光刺得她什么也看不见。她知道这是正常现象,因此并不紧张。视力恢复正常后,她看到一只断手,吓得她连滚带爬从床上摔到地上,头碰在床头柜上也不顾。她觉得她看到的是巨蟒的头,是鬼怪骷髅,想到自己被这只假手抚摸过,她既怕又想呕。既而发现,他没用假手抚摸,他的右手没有断,五根手指都好好的,和左手一样长,颜色稍白。那只断手不是手,是一个假肢似的手套。再看右手,并不比左手白,两只手颜色一模一样。头碰出血了。
“哈……”
她带着小小的恐惧佯装惊喜,惊喜是一厢情愿,其实只有恐惧和难受。血挂在脸上,她不准他管,连谈论也不行。这点血带给她的痛苦和震惊远不如假手。
他倒很冷静,把右手往她面前伸了伸,像演砸了的老演员似的若有所失,但知道此时应该坦然面对。
“既然看见了,那就好好看吧。”
他说。把假肢递给她。
“别别别。”
她躲闪着,这东西太诡异太恐怖。
“这也太太太神了了了吧。”
她干巴巴地说。满脸崭新的假币般局促不安。
想到他用这只手摸自己,不禁一阵恶心,像被胳肢得停不下来的孩子一样担心被偷袭,担心这仍然是伪装,它其实是蛇头或鱼头。这喜剧般的梦魇特别让人反胃,如同本想好好喝杯牛奶,喝完后,杯子底却是一只四脚朝天的苍蝇。
“说说看,这是什么情况,我真的惊掉了下巴。”
“对不起。”他说,“我不是存心欺骗你。”
“我知道。”
“那年,我在深圳,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刚出道,很难接到合同。不过,最主要的还是我不擅交际。其实也有几个关系不错的朋友,他们经营状况不错。可我不想找他们,我宁愿凭实力找陌生人合作。很快到年底,我没钱回家。几年没回去,很想回去看看。我用纱布把右手包起来,装成受伤的样子,去找做企业的朋友。意思是作为设计师,我现在不能干活,希望他们帮一把。没人愿意帮我,可能是我前言不搭后语,没让他们看出我的难处。这是我另外一个毛病。假装受伤没法赚钱,但我发现在街上,在公交车上,反正有人的地方,别人都会让着我,怕碰到我的右手。绷带和纱布让我获得平时得不到的空间,我平时就不喜欢和人接触,这意外的收获让我惊喜。回到家没拆纱布,决定继续装下去。春节没回家,我吊着绷带参加春季作品推介会,缠纱布的手的吸引力远远超过我的作品,也超过其他人的作品,仿佛它才是真正的设计。当然,这确实是一个设计,只有我一个人知道的设计。设计学会邀请我参加年度设计作品大赛,我戴着那套行头参加,不出意料地得了个金奖。我不可能一直缠着纱布,我在网上订制了一个假肢,其实是一个手套,我自己设计的,手套做好后,冒充残疾人来到贵阳。在这边没有一个熟人,全是陌生人,这正合我意。仍然不擅交际,但这只假手弥补了这个缺陷,让我很快站住了脚。”
她有点走神,她想知道的是它为什么那么灵活、离奇。她特别厌恶欺骗,再小的欺骗也受不了,如若不是,她不会离两次婚。第一个骗她没有父母,其实他母亲还在。第二个骗她只有三十五岁,其实已经四十。他们以为她在乎的她一点也不在乎,他们以为她不在乎的,她耿耿不寐。
“截肢的故事,是谁编的,不会是你自己吧?不是你又是谁?”
“不完全是我,我说的没那么详细。”
“你平时用哪只手工作?”
他难堪地举了举右手,放下去后像弹钢琴一样疯狂地弹着膝盖,幅度不大速度极快,四根指头像四个跃跃欲试的拳击手,拇指不时向四根手指形成的洞穴弹进弹出,像它们的教练或者指挥官。左手则老实巴交地挠挠头发,然后像四脚朝天的雨蛙一样仰躺在大腿根。
“我可以把它砍掉,今后再也不用它。”
“不不不,没这个必要。这是你的生存之道,即使要砍也等我走了再砍。”
她从阁楼下来,感觉浑身没劲,直到钻出电梯来到大街上,看见街灯和围墙,深深地呼吸了两口,整个人才从腻烦中缓过劲来。
她离开后,他关好灯盘腿坐在床上,除了右手,身体其余部分一动不动,回味着今天的失败和尴尬。这是他一个人独处时常用的坐姿,这让他感觉安静,可惜不能像坐禅者那样入定,常常是刚有超越什么的意念,刹那间却被什么东西切断,像蜥蜴的断尾一样掉进现实。他时而苦笑,时而冷笑。剁掉右手的冲动依然在,只是觉得技术上有难度。要是有个医生来帮忙我不会犹豫,他想。问题是不会有这样的医生吧?他不无自嘲地笑着。既可怜又心不在焉,一种轻悲袭上心头,感觉无助又无力。
怎么办?躺着不行,坐着不行,行走要好点,可在房间里走速度和距离都不能驱散心头惶恐。曾经的聪明变成咽不下去的愚蠢。手机拿起又放下,里面没有一样东西想看。打开电脑,不是为了做什么,也不是希望电脑本身出现奇迹,而是要给手找个可以触摸的东西。这时手机短信铃声响了一下。拿过来看是银行贷款信息。无意中翻出一个电话,名字后面备注有打醮二字。
几个月前,一个卖酒的人请他设计包装盒。酒在茅台镇灌装,要求他设计的包装让人即使不看文字,只看外包装都知道这是茅台镇的酒。这一点不难,尽量让它像人尽皆知的飞天茅台就行。卖酒的人请了一桌,请他们出谋划策。他不想去,酒老板一再坚持,要他多听听其他人的建议。饭桌上,坐他旁边的人很少说话,回家时得知两人住得近,于是打同一辆车。在车里,这人的话多起来,说了些什么记不得了,下车后互留电话,告诉他有什么事可找他。
犹豫了一会儿,把电话打了过去。没说手的事,只说最近不顺利,不知道怎么办。对方很热情,要马上过来看望他。他说用不着,不能这么麻烦他。说得越多,他越觉得不应该打这个电话,过度热情等于纠缠不休。

对方说了句让他觉得另有所指的话,你的手是不是发炎了?还没想到如何回答,对方说,上次我看见你不时抠你的手套,好像有点痒。他的心落下一半,承认这只手不舒服。戴手套的时间一长,出不了汗就会发痒。对方说,你去买支皮炎平。
他松了口气,不再像刚才那么难受。把今天发生的事理了一遍,觉得其实从她问他照不照镜子,就已经出现问题而自己没发现,所以千不该万不该,吃完饭都不应该带她回来。今后怎么在这行混下去呢?她即使不告诉第二个人,他也会感到难堪。而她不告诉第二个人的可能性几乎为零。想到这里,意识到最大的问题不是面子,而是自己不得不离开贵阳,去某个陌生城市从头开始。
这时她的短信来了:“还没睡吧,我知道你不好受,其实我也不好受。”
“谢谢。”他故意冷漠地回复。
“我不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幽灵,我也是人。”
“我知道。”
“我觉得现在最好的办法,是脱去手套,把右手彻底亮出来。其他人只是一时好奇,最重要的是你自己慢慢适应自己。”
“谢谢。”
“希望你好起来。晚安。”
“谢谢。”
最后这一句谢谢,比前面几个真诚。
关掉电脑,如果可以,最想关的是大脑。正准备关手机,有打醮二字的电话打来。说他不相信手发炎,一定有别的事情,他真的可以帮他,不要不好意思说出来,每个人都会遇到一时摆脱不了的困境,他和他还不算朋友,他愿意帮他,是他儿子因为抑郁症住院,他现在在医院护理他。他接受他的帮助,他儿子都会感到高兴。他害怕他继续说下去,老实承认遇到的问题。对方听完后没作任何评价,对他说:
“只要你照我的话去做,我保证你从明天起,不再为右手烦恼。现在是子时,你从你平时吃的东西里选九种食物去喂流浪猫,记住,只能喂流浪猫,不能喂家猫。要喂九只,不多也不能少,喂完后回家,今后不会有人在意你的右手是否真残,你想继续戴手套没问题,想亮出来也没问题,不会有人在意你的右手,他们只关心你的才华。”
喂猫一点不难,他想,不时有猫在楼下叫唤。吃的哪里去找九种呀,有三种就不错了,平时除了早餐,要么叫外卖,要么出去吃,不喜欢做饭,把做饭当成负担。
“只要用心,准备九种一点也不难。”他说。
这话让他想起年少时老师和父母的教诲,只要功夫深,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对方不和他辩论,已感到黑暗里出现一个洞,他正从洞里走出来。
冷藏室里一盒烤鸡,一盒小龙虾,小龙虾打包回来时间太长,不能吃,丢掉。烤鸡是前天的外卖,当时想一个人喝瓶啤酒,外卖送来后没胃口。三个生鸡蛋,可将其中一个煎成蛋饼;一根火腿肠,直接剥皮即可。榨菜和酸萝卜,猫不吃吧,他想。还好,烤鸡里有两块烤鱼,这可以算一种。冷冻室塞满了冰,菜刀撬开冰后找到一块五花肉,一条猪肝。还差四样。继续挖,在后壁找到三个饺子和半袋小汤圆。煎鸡蛋时想起茶几下面有夹心饼干,有点软,吃了一块,觉得猫应该能吃。再去冰箱里搜索,没有找到猫喜欢吃的食物。热水解冻五花肉时掉下一条黄鳝,刚才被冰裹住没看见。他深感幸运,像高考时蒙对一道大题一样幸运。
在华宫巷遇到的第一只猫是黑猫,他没养过猫,对它们无爱无恨,像人群中擦肩而过的陌生人。他给它火腿肠,觉得猫的智力和性子像三四岁的小孩,在他准备的食物中,火腿肠是首选。掰碎放地上,黑猫很给面子,吃得一粒不剩。前面有个胖大姐猪脚火锅店,他心想那附近应该能找到,啃过的骨头一定会吸引它们。没有,看来和人的口味并不相同。沿文昌北路往南走,走到鸿雁巷,仍然没碰到。出乎预料,在红绿灯灯杆下遇到三只,他给它们撕掉骨头的烤鸡、黄鳝,切碎的猪肝。发光的眼睛让他感到害怕,他不敢接近,把食物放在地上后,后退出十余步。几分钟后上前查看,发现食物已被取走,他松了口气,甚至有几分欢欣。从人行横道穿过文昌北路,在大方手撕豆腐店遇到两只,胖大姐猪脚火锅店遇到一只。这个胖大姐和刚才那个是什么关系,是两个胖大姐还是同一个?为什么胖大姐都喜欢卖猪脚,相距这么近就开了两家?旁边有一条小街,没看到街名,街边有小花台,里面一定有流浪猫,但他不敢进去找,怕被人当小偷。只好在文昌北路上寻找,文昌北路是大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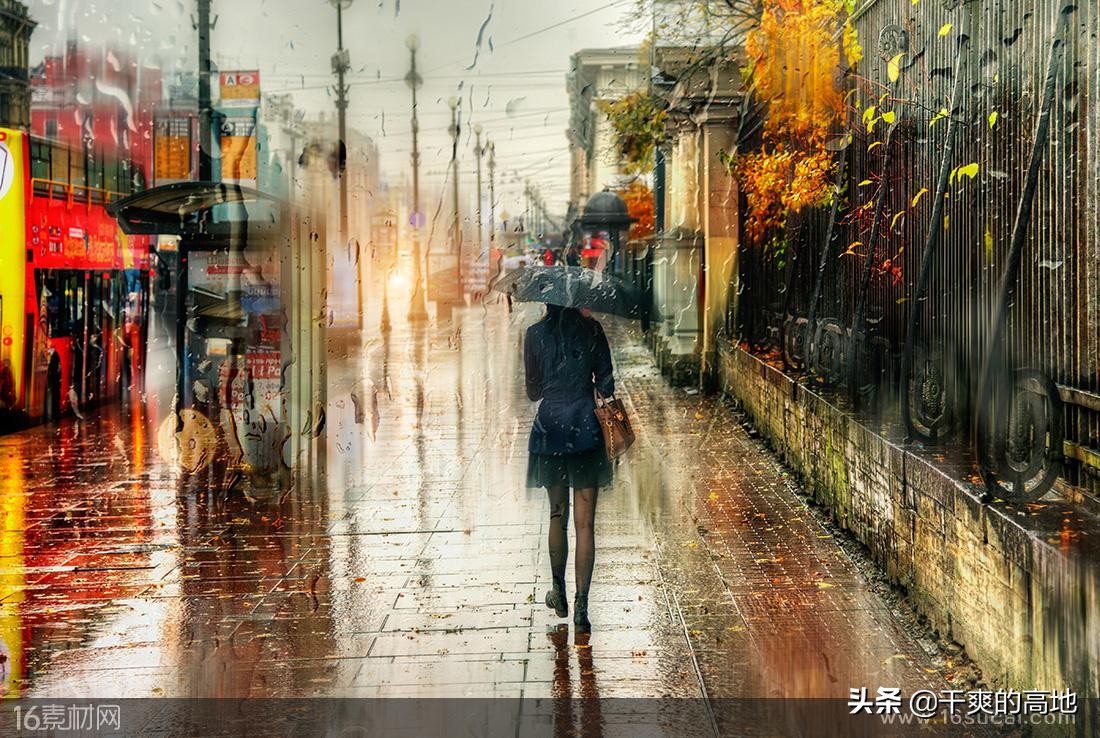
刚来贵阳时,曾在莲花坡一带寻找过房子,中介把他带进一座没电梯的建筑,楼道里印满了疏通下水道和开锁的广告,巷子狭窄零乱,夏天在里面散步不但凉爽,出来吃东西也方便。和父母的房子很像,在父母的眼里,这种消费不高、邻里相亲的地方才是家,才可长住久安,其他地方则充满了何以为家的危机感。他一点也不喜欢,没开门进去就叫中介换地方。
已经走到文昌阁和老东北遗址,他有点担心,再往前走是文昌南路,文昌南路最有名的是家乐福,那里人多车多,不会有流浪猫。走到一面生锈的铁门面前,犹豫着是回头还是继续往前走。侧身时发现身后跟着两只猫,一白一黑。他感到这不是幸运,是她在帮助自己。
他蹲下去,先将饺子掰开摊在地上。黑猫抢上前吃饺子馅,白猫原地不动,他摇晃饼干示意,叫它过来。白猫举起右手,像要球的NBA球员,他以为它叫他丢过去。好的好的,抛过去时很准,打在手爪上,但它没接住。既像被它打掉,也像特别想接住但忙中出错。饼干掉到铁水篦下面,黑猫白猫喵了一声,和他一起看着铁水篦,这是一块不可能撬起来的铁水篦。
他苦笑了一下,蹲了很久才离开。没回家,随便走,三次经过指月街。看似让脚带着自己走,第三次经过时,知道脚不可能替他着想,一切缘于内心的选择。遥想当年,给指月街取名的人,应该是看到月亮后得到的灵感吧,以月喻教,以月喻法。现在,走在指月街看不到月亮,也没人抬头看月亮,也不会想指月二字。想到这里,有所释然。指月街靠护国路一头,有家开了三十余年的素粉店,生意极好,店外只有两张不锈钢长方桌,十张小塑料凳,大多数人要么站着吃,要么打包带走。路过不吃,看到别人吃得很香,会咽口水。他每次来,都要顺便吃一碗。今天他排在最前头,接过装在纸碗里的素粉,他没像平常那样,一定要有座位,因为只有一只手嘛。今天他站着吃,左手端碗,右手使筷。这碗素粉,比他任何时候吃过的都好吃。

冉正万,贵州人。在《人民文学》《花城》《十月》《中国作家》等刊发表过长、中、短篇小说若干。出版有《银鱼来》《天眼》《纸房》《八匹马》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跑着生活》《树洞里国王》《苍老的指甲和宵遁的猫》《唤醒》。曾获花城文学奖新人奖、长江文艺短篇小说双年奖,贵州省政府文艺奖一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