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这部小说,回过头来,我想说一说写这部小说的初衷。”这是刘震云新书《一日三秋》开篇的第一句话。乍一看不像是前言更像是后记,一上来刘震云就把他创作小说的初衷写给读者的,什么悬念什么包袱,什么隐喻什么话中话,不要乱猜,刘震云直接写清楚。这部小说由现实中的一个念想,萌芽、成长、开花、结果自然而然提笔创作出来的。读这本书时,读者有时感觉故事戛然而止,话没说尽没说完;有时感觉一个人的事说着说着转到了另一个人的身上,一件事隔个几十年在他人身上才能看到答案。刘震云将所有疑惑的答案都写在了开篇前言中,以至于书中如何天马行空,如何匪夷所思,最终都要回到这篇前言上,读之前要看,读之后也要看,在这个意义上这篇前言也算是后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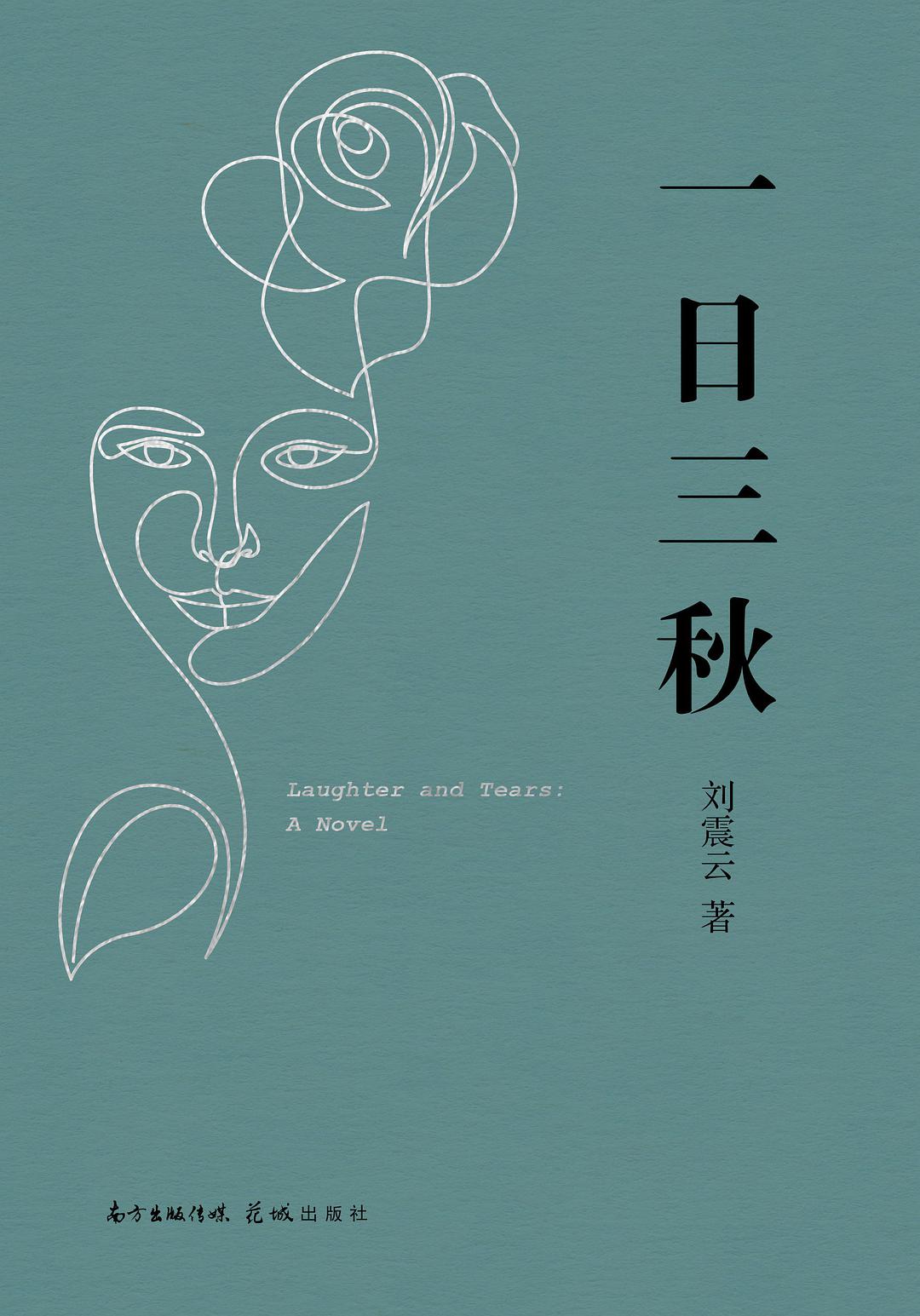
《一日三秋》 刘震云 著 花城出版社
书中的故事起源于“六叔的画”,这些画的故事原本只存在于六叔的脑海里,随着六叔去世,这些画也随着他灰飞烟灭。刘震云算是六叔的知己,六叔的那些画作也就他能欣赏得来,而随着六婶的一把火,刘震云只能凭着自己的记忆重新构建六叔的世界。六叔的画中有误入延津去人梦里听笑话的仙女,有在黄河上跳舞的“红尘知己”,有男人肚子里装了女人,也有描绘如《清明上河图》一般的延津渡口的集市。六叔的画中有日常生活中的人和事,也有因为不敢说或说不清而幻化成的很意识流的东西。刘震云书中的故事可以说还原了六叔画作给人的最初感受,在现实与魔幻之间反复横跳。
故事的正式开始,是由花二娘的小传开始的。短短几页叙述,目的要为全书的故事打定个基础。花二娘是个在延津等人,一等就是三千年的不老奇女子,她夜里专门去延津人的梦中听笑话,笑话好就赏人一颗红柿子,笑话不好就在梦中将人压死。花二娘是个闲人,她到处听笑话;花二娘又是个苦人,她为什么到处听笑话,是她一直在苦等一个永远不会来的人。这份苦本身就是她自己身上的一座山,延津人是苦中苦,只能笑只能幽默不能喊苦,以至于书中的延津人平时不备点笑话都不敢入睡,这种硬性要求的幽默,构成了书中一切魔幻与荒诞的基础。刘震云选择以这幅画作为故事中一个重要的开端,引起了书中那些民间传说似的故事。
在《一日三秋》中,花二娘在延津人的梦里听笑话的事是不容置疑的,不需要先决条件,也不需要讲述为什么。花二娘的存在是故事中最没有悬念的部分,但很奇怪在整部书中,花二娘自开头的小传后,隐身大半本书后才在故事快完结的部分登场。在书中的前半部中,花二娘只出现在吴大嘴死后旁人的闲聊与樱桃附身后的诉说中,还有老董偶尔念叨两句,司马牛畅想下自己准备写的《花二娘传》,花二娘的出现仅此而已。
当读书过半,读者相比书中的延津人更确信花二娘的存在,第二章有关花二娘的内容,开始发挥作用,花二娘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进了延津人的生活中,走进了读者的意识中。我们会发现书中不管是附身的事、还是算命的事都与花二娘的故事一脉相承。我们只要能接受花二娘的逻辑,樱桃、老董、马道婆、孙二货的魔幻部分也就不显得突兀、生硬了。

刘震云在话剧中表演 本报记者 武亦彬 摄
陈长杰和陈明亮两代人的故事,组成了书中的现实部分。陈长杰、李延生、樱桃本是延津豫剧团的名角儿,靠着一部《白蛇传》在本地知名。时代的发展败落了豫剧,也败落了这三人的人生,三人褪去了光环,成家就业由仙界回到了人间。回到人间就难免油盐酱醋茶,剧中的“法海”陈长杰和“白娘子”樱桃,生活中结了缘,却相生相克矛盾不断。后来樱桃出了事,陈长杰便带着他和樱桃的孩子背井离乡走出了延津去了武汉。
樱桃为了寻求解脱上了吊,本成逍遥自在一孤魂,然而却遇上了野鬼里的恶霸,没解脱了的樱桃又想起了“许仙”李延生,要他“背”着自己去武汉“找儿子”。陈长杰为了寻求解脱出走延津去武汉开始新生活,而李延生因为身上被迫“背”着个人,为了寻求解脱也来到了武汉。就这样一代人的故事就像命定似的,起源于延津,解脱在武汉。但他们真的解脱了么?
陈明亮作为陈长杰和樱桃的孩子,第一代人的故事注定对他的一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跟着陈长杰来到武汉的明亮,挤过大宿舍也跟重组家庭中麻木地生活过,但终究没有归属。武汉是上代人的解脱地,并非是明亮的归属地,于是便有了后面明亮自己一人历经两个月一路讨饭讨回延津的事。爷爷奶奶已经过世,留在延津的明亮虽然有了归属,但却没了亲人。陈长杰既为了明亮也为了自己的生活考虑,只好把明亮寄养在当年的好友李延生家,靠瞒着媳妇偷偷给明亮寄生活费,远程“云养子”,而后因为种种原因,陈长杰顾小家舍儿子。明亮只能退学早早地奔向社会,去猪蹄店打工当学徒,走上了一条孤独且艰难的路。之后的打拼、成就、家事、家乡事等等,一日三秋恍如隔世。
刘震云以两代人的故事,将六叔的画作落到了地上,生了根发了芽。《一句顶一万句》中,一出一回诠释出了宿命般的故事。而这本《一日三秋》两代人出出回回,依旧延续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内核。明亮再如何成功,他终究也是个小人物,在延津这个地方很奇怪,刘震云用老董那双看不见的眼和胡说的嘴,讲述了小人物有多小。有的小到上辈子是个畜生,有的上辈子虽荣华此生却只能是个扫大街的。他们的故事拼起来,依然是一地琐碎搓成了一地鸡毛。
从陈长杰那一代人我们更多体会到的是生活的窘迫与无奈,没有多少激情,就消沉失去了过往的光芒。明亮在武汉时也是这种感觉,但母亲的来和去,奶奶的来和去,使他突破了这种困境。我们在阅读时始终觉得,明亮的生活中有光,属于小人物的光。多年不见的父亲突然想见明亮,结果去了之后才发现,亲情不止需要问候还需要金钱。成年人的潜台词都在刘震云的文字里,那些描述秦薇薇窘迫拮据的片段,足以让读者让明亮懂得此行的目的。还有郭子凯口中的文化差异,乍一听都是生活的无奈,刘震云通过讲理绕着绕着,你会发现又回到了简单的问题上,名利是小人物生活的动力,凡人再多冠冕堂皇终究绕不开这些俗事。
书中一个带有人畜双重身份的孙二货也是如此,流氓孙二货,野狗孙二货,小人物的奸诈与底层互害的逻辑是刘震云擅于描写的部分,这部分属于流氓孙二货,无耻的彻底,但又是个怂货,一辈子在一亩三分地里称王称霸。痴呆后,孙二货则完全通过明亮的行动与心理描述诠释了这样一个无知无畏蛮横耍混的人,他人生最后的无力感暴露无遗。比较惊喜的是野狗孙二货,笔触透着温情,用狗的一生写出了人性的温暖,顺着花二娘的逻辑总感觉这条狗身上附着什么。
世道沧桑、人情冷暖组成的现实和柳暗花明、荒诞幽默组成的魔幻,层层叠加在这部《一日三秋》中。故事中很多人怕自己活成别人口中的笑话,于是努力活着,然而总是有成为笑话的时刻。“法海”娶了“白蛇”最后成了悲剧;马小萌的新开始从旧事被抖搂出来开始;郭宝臣扫地供儿子出国却再也不见;孙二货横行霸道老了却认明亮是“兄弟”;老董的儿子子承父业“不瞎学不到精髓”,这些书里的故事,都好似笑话一样传到读者的耳边。他们为了活好自己的一生付出了多少努力,可越努力越可笑。
文学从来都不是对现实的模仿,而是一种再造,小说中的现实,不是生活中的现实。刘震云打破了“看起来真实”和“看起来魔幻”的事物之间的界限。书中让人信服的不是故事情节,而是一种语调,一种质朴却又扎实可信的语调讲述离谱的故事,不可信也变得可信了,而且语调也让拼凑起来的故事完整,自成逻辑。
这本书超脱人们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小说叙述方式又非常的自然,就像老人讲本地传说一样,跟亲眼所见似的,以最自然的口吻讲述最难以置信的事。所以,开头的前言就得常挂在嘴边,因为一不留神就把画中的事当成身边事了。
《一日三秋》中的故事,无论多么荒诞和离奇,都是现实的反映,一个朴素的现实。(责编:陈梦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