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火车进站
文丨梁鸿鹰
1
对小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生的孩子们来说,还有什么比火车进站出站更激动人心的呢?我们盼望已久,欢呼雀跃,流着鼻涕,张着大嘴,一次次将热切的目光投向车厢或出站口那越吐越多,最后又必然烟消云散的男男女女,乐此不疲。
越是物质贫乏,越是时间充裕。家乡小城的火车站曾经是我少年时期与小伙伴们经常去消磨时间、观看风景的地方,它诱惑着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浪掷了过多的精力。谁能知道为什么呢?小时候的我们就是命好,不用对付无穷无尽的习题,不必上任何补习班,我们是时间的富翁,闲暇的专宠,可在无穷无尽的时间里游戏。火车站被我们选为游玩之地,是因为这里人多,宽敞,热闹,有小城上最吸引人的建筑物。最重要的是,火车站有火车这个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庞然大物,这个乌黑的钢铁设备,是我们见得到的最伟大的文明象征,是大家想象所及的最了不起的可移动存在,梦中绝对的精神与物质主角。它体积庞大、能量无限、威力无边、坚不可摧,声响和体魄足以慑服任何一个见到它的人。除了飞机,谁也设想不出还有什么东西能超得过它。火车既可任意移动,又能构成实实在在的危险,那个时候经常听说火车轧死了人,很少听说汽车出人命,而且火车不停地带来新的可能,把欢乐、悲伤和关于未来不确定的向往,从一个地方运到另外一个地方。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埃尔兄弟导演的只有五十五秒的电影短片《火车进站》在巴黎上映。火车冲着镜头呼啸而至,吓得观影者几乎要抱头鼠窜,火车这个当时伟大的发明迅速为世上的人们所知晓。
火车日夜在小城经过与停留,它经常闯入我们的梦境,火车威风凛凛,声嘶力竭,以笨拙的身躯,粗重的喘息,漫天的烟雾,穿越茫茫黑夜,踏平风霜雨雪,向北方县城沉睡的人们宣示自己的存在。顺着延伸向远方的铁轨,大米、白面、苞谷、大豆、红薯干、布匹、缝纫机、自行车等等,会如约进入一户户人家,火车还会运来我们远方的亲人,送来投亲靠友的素不相识者,无论人们是有嫁妆还是没嫁妆的,得意的还是失意的,手脚干净的还是不干净的,火车都不会拒绝。火车让各种各样的期待或意外发生,让喜讯或噩耗、忧愁或愤怒不期而至,把人们对生活的期盼带到小镇。在小镇的日常生活中,从来没有任何场所、物体,能够比得上火车给人们的那么充足的想象。慑服大家的,也许不是体量、声响,而是带来的未知与可能。耳边火车嘶鸣的机会,每天虽只有数得着的几次,却必不可少,它们提醒着市民们的生活与世界上最先进的设施有关,小镇和外部世界存在着正常联系。
一个家庭从外地来什么样的人,或与有多大派头的人来往打交道,就能给小城的居民带来多大的想象。谁家从火车站接来了什么样的人,是乡下人,还是城里人,是大地方的,还是小地方的,是当官的,还是平头百姓,很快就能被人知晓,转化为小伙伴们相互攀比的话题。我经常梦想着能够到车站去接人,把远方的亲人虚构为即将乘火车来到家里的客人,或将听来的故事安到自己的头上,在梦里让那些住在大城市的人都尽快降临到自己家里。
小孩子参与进到车站里接人行列的机会稀少到几乎为零,我们被大人轻视,当成碍手碍脚的绊脚石,在他们眼里,到车站的路途过于遥远,何况自行车匮乏。而在我们看来,到车站这点路根本算不上什么,我们就想去车站接人。有次我梦见自己跟父亲去车站接从北京来的二姑一家三口。去接的当然不止爸爸一个人,自行车也不止一辆,在那个阳光充足的下午,拗不过苦苦的请求,爸爸同意带我去。妹妹听到这个消息时自行车已经启动,她在后面拼命追,拼命哭,我则坐在后座上幸灾乐祸。
后来,二姑一家三口真的来了,仿佛是忽然之间降临的,完全没有经过到车站迎接这个环节。二姑是个有意志力、有主见的女性,穿扮得十分洋气。她走路风风火火,高昂着头,长长的头发在阳光之下飞扬飘逸,她双眼炯炯有神,黑色的眸子又大又有神采,这种自信、坚定和洒脱,从见第一面起,就深深铭刻在我的心里,永难改变或磨灭。我、妹妹、爸爸,与二姑一家一同去逛了小城那个局促得过分的动物园,看了被我们看过无数遍的孔雀和猴子。那只大孔雀依然拒绝开屏,它很悠闲,也很懒惰,永远站着或走动着,没有坐卧的时候,也不会给你开屏。猴子更不争气,不怎么跑动,拒绝做出任何有意思的举动。

又一次,从北京乘火车来的四舅,在冬季的一个大清早悄然而至。他高高的个子,虽只有四十多岁,却已银发满头,据说是因为过早摘除了脾脏。四舅在林业部长期从事森林资源调查统计,是工程师,俄语很好。他到家的时候我正赖在炕上不肯起来。穿好衣服后发现他在喝牛奶,吃着我们很少吃到的面包,酸酸的,甜甜的,十分松软的那种。四舅总是很和蔼,说话轻声细语,举止斯斯文文,他只比妈妈大两岁,看得出,家里虽来来往往着很多妈妈的亲人,可在情感上,他与妈妈是最亲近的。亲近的人之间话语往往不多,想必有些话专门放在心里随时留给对方。妈妈与四舅之间有很默契的对视,有偶然的深入交谈,恰好让对方都感到很惬意。姥姥对四舅问长问短,声量不大的胶东话抑扬起伏,语速极快。妈妈很习惯地在旁边听着,并不插嘴,睁着大大的眼睛专注地看着自己的母亲。四舅此次是专程来接我姥姥到北京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姥姥中了一次风,已有行动不便的表现;二是我妈妈的肺病此时极严重了,后来听说她当时是“空洞8期”,即肺结核晚期。姥姥有五个儿子,只有这么一个宝贝女儿,向来对女儿唯命是从,如有不测,老人家肯定受不了打击,最好的选择就是别让她在跟前。蒙在鼓里的姥姥则抱怨女儿女婿嫌她老了,不中用了。几天之后,家里来了一辆小汽车送他们到车站。姥姥和女儿离别的时刻终于到了,那个下午特别冷,老天阴沉着脸,风一阵紧过一阵,姥姥已经穿好了外套,朝着女儿默默地看过去,“承真,妈走了”,“承真,常来信啊”,这也许就是姥姥和四舅对妈妈仅有的几句话,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记得了。任我怎么努力,也无法完整还原出当时的情形,只记得妈妈坐在靠近厨房的一张矮凳上。她并没有起身,更没有抬头呼应母亲的凝视和告别,她喘着粗气,脸色阴沉,有没有说什么话,是否流下眼泪,我是一点都想不起来了……
2
前往火车站看热闹,是小城里的男孩子们的专有活动项目。这种活动有种莫名的隐秘性,有连我们这些参与者也不太明白的讲究和规则。通知谁不通知谁,什么时候出发,都要保密。信息传递在暗中进行,而行动时却又是炫耀的、公开的,大家三五成群,戴着风镜,或者柳条编成的“草帽”,吹着口哨,或胡乱哼着歌曲,手里拿着小木棍之类,一路小跑来到车站。
我们经常专门静等火车进站停下来,旁观从车上下来的人,议论顾客的破绽与尴尬。我们每次都不会没有收获,那时人们的纯朴、厚道,有特定的表现方式,比如笃信礼尚往来,笃信关系维持靠的是携物走动。坐火车的人大多肩扛手提,因事先已完成了心意变物品的换算,诉求已折算成粮食与瓜果,达至心目中见面礼与“面子”的大致相当。物品的多寡与诉求的大小当然要成正比,即使无所求,空手也被视为严重不恰当。作家李佩甫说,家里来的亲戚曾经给他妈妈带过穿起来的蚂蚱。中国人的伴手礼就这么丰富而必不可少。当时我们总能发现,火车进站停车后,下来的人各有各的狼狈,有人被踩掉了鞋,有人被烟头烧了头发,或者带的土豆黄瓜豆角西红柿掉了一地,被后面的人踩了个一塌糊涂。

我们望眼欲穿,我们心急火燎,等到火车终于进站,终于停下来了,此时我们发现,大同小异的大包小包连同它们的主人,陆陆续续从车厢里被吐出来。车上下来的每个人照例都灰头土脸,面目模糊,没有几个清秀的。个别干干净净的女孩子被自己的母亲或长辈紧紧地牵着,就像是被守着的稀世珍宝。姑娘们并不左顾右盼,她们几乎一律梳着笨重的大辫子,把自己套在宽大的上下一般粗的衣服里。她们后来会怎样?在这个小城的火车站,长大后是会经常露面,还是一去不复返呢?但愿她们不会变成安娜·卡列尼娜那样的人——在火车上邂逅意中人,在火车站结束生命。
有一天,我忽然被来自出站口的越走越近的一个红色光团吸引,近了之后才发现,红色光团是个红色小头巾,小头巾渐行渐近,装点着一个小姑娘白白净净的脸庞。我看清楚了,小姑娘圆嘟嘟的小嘴,尖尖的鼻子,双颊停着两朵小红晕,她眼睛极细长,单眼皮,眉毛也极细长,显得很机敏。她宽额头,头发被紧紧地梳在脑后,一缕都没有散落出来。姑娘和我年龄相仿,看着眼熟,就是想不起在哪儿见过。她从检票口出来的时候,手里的小篮子被旁边的人挤到了地上,西红柿、茄子、黄瓜、豆角什么的,稀里哗啦撒了一地,见此情形,我一下子脱离开小伙伴们,不顾背后的嘲讽,跑过去帮她捡,蹲下来的时候看到她穿一双黑色方口条绒布鞋,里面的棉袜异常洁白,折射过来的光亮刺中了我张皇失措的双眼。她没有领情的意思,她只顾自己捡,并不抬头看我,捡东西的急迫使她的脸更红了,有一种羞涩与难为情在里面,但并不怯懦。她站起来后我才发现,姑娘的身材苗条,个头不小。
选自梁鸿鹰首部散文集《岁月的颗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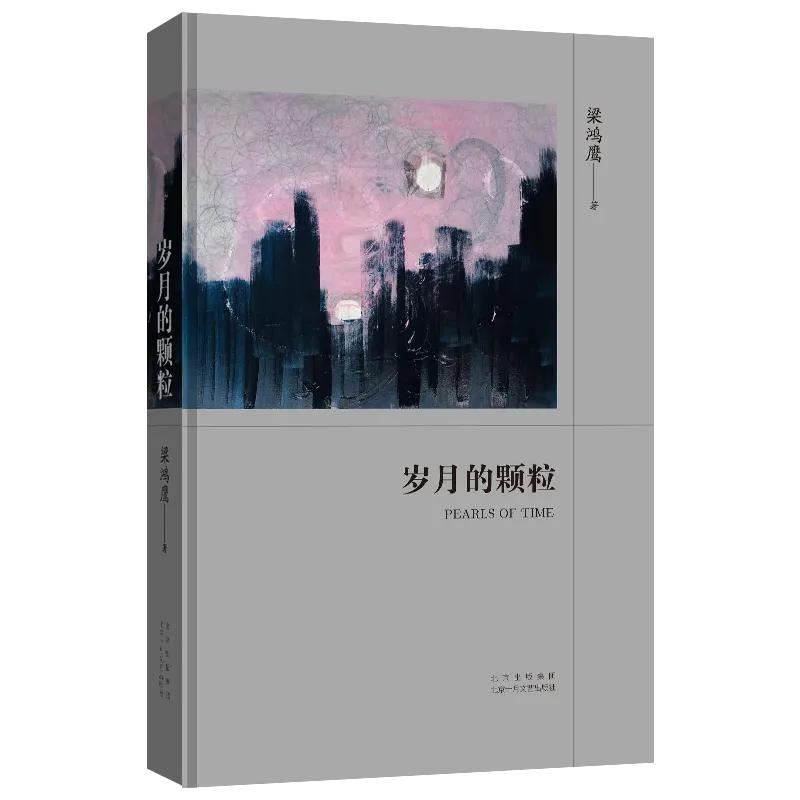

梁鸿鹰:毕业于内蒙古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南开大学中文系,世界文学专业硕士。中国作家协会,著有译著《圣经中的犹太行迹–圣经文学导论》《阿西莫夫诠释人类万年》《致命的冒险》等多部,在报刊发表文艺评论、随笔等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