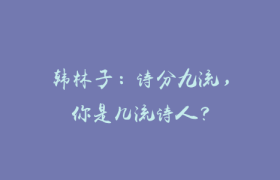林菁:《坐着坐着天就黑了》是您第四部深圳题材小说集,如果从2011 年开始写这一系列小说算起,正好八年,八年出版四部集子,速度够快。
邓一光:问题在哪儿?
林菁:速度。收在其中的《香蜜湖漏了》荣登2018 年度“城市文学”排行榜短篇小说榜首,小说在《花城》杂志首发时,内容简介里有一个词让我过目难忘:“速度感”。这些年城市化进程的发展速度大家有目共睹,您身在其中,对“速度”有什么切身感触?
邓一光:我个人更多的感受在于人身上发生的“速度”。本世纪前,人们的生活变化和生命体验基本是年代感,无论物质拥有还是内心轨迹都是有限的,大体能够观察到较为完整的生成,人们能够通过写作记录下文明进程如何作用于人的成长塑造,甚至可以清晰地捕捉到个中细腻的细节变化。本世纪,文明进程突然提速,尤其第二个十年,城市化进程和意识形态冲突加剧,量子力学颠覆了传统文明的基础构成,观念更迭非常快,人们在一个快速通过的时代根本无法形成个性,基本只能被动接受格式化过程,个体生命的差异越来越小,对生活的陌生化程度越来越高,矢量失衡现象非常普遍,世界的客观和个体的主观都在形成碎片化,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形成对人的判断方式和标准在这个时代失效了,人们从那个时代学到的观察世界的方法不管用了,从容驾驭长篇书写的可能性正在失去。
林菁:是否可以理解为,您质疑现代化“速度”?
邓一光:小说家有责任为读者持续提供新的经验类型,然后阐释它们。格式化并非新经验,现实主义已经为人们提供了大量工业时代格式化人格的优秀文本,直到今天,它们还在影响人们对文学的想象,但那不是我的时代,我需要新的经验来源。
林菁:您说《香密湖漏了》源于“和一些作家在香蜜湖吃饭,他们的移民经历比我早,饭局上交流时全是曾经的历史,我心里一动,说要写这顿饭局,第二天就写了。”这听起来不可思议,仿佛那顿饭是一个导火线,引爆了您藏匿已久的故事?
邓一光:我以为能从更早一些进入这座城市的人们那儿了解城市真实的过去,这个想法可能难以实现。人们关心今天发生了什么,未来会发生什么,很少谈论过去的事情,即使谈,也缺乏历史观考量。对大多数人来说,过去的经历消失掉了,他们根本不愿意去回忆,好像有某种奇怪的羞耻感,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具有羞耻感的还有城市,它一直在强调正确性、历史机遇什么的,在类型讲述上把自己的过去抽象化,很多真实的历史经过筛选快速屏蔽掉,城市在自己的表述中是断裂的、二维的,而且你很少见到这座城市的知识分子反思。在一座几乎由移民构成的城市,你看到的是一个个“全新”的人,他们没有来处记忆,没有成长记忆,有的只是改革开放这样一个共同的制式化生存和发展模型,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我当然不相信这个,我想找出那些记忆。故事中人物的记忆是弥足珍贵的,我想讲一个前世今生的故事,它必须具有历史感,是一个纵深的故事。
林菁:您在《香蜜湖漏了》创作谈中提到:“一座湖泊漏了,只是万千自然规律中的一种,根本不构成问题,湖会在别的地方出现,你在几十万年后见到的它,与几十万年之前的它没有什么实质区别。正如湖是一种自然现象,人的生命被投入社会后,就成为历史现象,但人类历史与自然历史不同,它的代偿能力可远没有自然界那样值得信任,这就是我在写下这个小小的故事时感觉到的深深不安。”能具体谈谈您的不安吗?
邓一光:自然的起源和规律不由人类决定,人类还没有达到自然已有的那种均衡和从容,它只能属于而不能成为主宰。地球人不过是自然的一个偶然产物,这个种群也可能是其他生命。文学为什么总在从头开始认识这个世界,以确认自己的观察和判断?不是未知世界让人困惑,那个结果人类早就接受了,而且以此为动力,乐此不疲地把它们当作神秘世界来挑战。新的文明桂冠,是我们把自己遗失掉了,不知道自己是谁了,我们开始创造神圣化的“我们”,进入一个种属异化时代,很难说这不是一种生物规律,就像基因突变,在更大的范围内,它也是一种规律。
林菁:《风很大》里有一句:“她希望有力而深刻地生活,在日后宣称自己真实地生活过,但不曾做到……”这句话估计能触痛当下许多人,不单只是《光明定律》《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里的“精英”主人公,像《金色摩羯》里的倪小萱们,《你可以做无数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里的简小恬们,大家都在自己的轨道上努力“挣扎”。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能在日后宣称自己真实地生活过?
邓一光:我是一个生命经验匮乏的人,说不好现实世界中人与生活的关系,个体生命要求的答案会完全不同,我不能给出一个规约式的答案,这个恐怕会是个无解的话题。我个人不多的经验,身心合一的生活就是真实的生活,这样的生活你不会怀疑它,它就是你要的,它的真实性会被你以生命的方式确认和信奉。
林菁:您的哪篇小说里出现过这样的人?
邓一光:故事通常不会去写完成了的人物,而会写改变着的人物,至少这个人物是困惑着的,在解决着困惑的,所以,故事中的人注定了永远都不可能完成。
林菁:《我现在可以带你走了》开放式的结尾有些许“诡异”,类似的还有上一部小说集中《深圳蓝》里的《停下来是件不容易的事》和《一步之遥》。这可以看做您对宇宙未知领域所持的敬畏之心吗?
邓一光:从终极角度讲,没有人知道他来自哪儿,他属于哪儿,他究竟是谁,这个人类宿命引发了人们绵延不断的生命追问,也产生了生命过程中最大的困惑,认真想想,这种情况并不诡异。
林菁:您是指无穷尽的宇宙规律?
邓一光:我们对宇宙的了解只是极少一部分,超过三维的理解就谈不上了,就好比我们在问文学是什么,其实作为想象力方式的一种,文学从来没有被穷尽过,至今我们读到的故事基本都停留在动物立场的丛林法则和人性立场的人文主义上,没有超越可怜的时间思考边界,科幻文学试图突破三维空间,进入时间世界,但它仍然徘徊在趣味性上,我们需要的那只折叠黑洞并没有出现。就算人类进入四维世界,那也只是高维世界的阴影边际,在边际之外,可能有一个悲天悯人的世界,是超越我们现在理解和认知范畴的真实存在,甚至于那也不是止境。更多时候,我们不能依赖科学写作,科学解决不了人的所有问题。
林菁:您对星座有研究?当初为什么选取“摩羯座”这个点来串起《金色摩羯》整个故事?
邓一光:我对星座没有研究。写这篇小说那天,霍金去世,他是摩羯座中特别另类的生命。《金色摩羯》的主人公有着摩羯座典型的小野心,特别适合初闯大都市的年轻人的某些意志,这是一个巧合,在故事里,也不过是一种象征。另一个巧合是,那一天还是爱因斯坦的诞辰日。但我不相信巧合,不相信那天发生在我生活中完全不相干的一对纠缠,我只是解释不了到底发生了什么,只能通过一次写作来解决我个人的一点困惑,所以在小说结尾,我写下了一句话,“一个永远也没有停止生长的金色摩羯座孩子,他像一颗訇然陨落的流星,穿过阴云密布的卢伽雷氏症天际,坠入温暖的黑洞之中。”
林菁:《金色摩羯》里嵇慕儿说,“找个说客家话的原住民比登天还难”,而您又专门为客家原住民写成了《宝安民谣》,《宝安民谣》里写到“厂妹”,而《你可以做无数道小菜,也可以只做一道大菜》里,厂妹又成为书写对象,有点像文本里嵌置的超链接,这种处理很妙,是否有意为之?
邓一光:我没有为原住民写小说的初衷。我离他们非常遥远。我是为我自己写下那个故事。今天这座城市的人文生态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已经成为历史,属于文明堆积层内容了。我试图去寻找这段历史,并不在乎它将串连起哪些人,那不是我能决定的。我请史志专家黄玲老师为我开过书单,甚至在主编“深圳短小说八大家”丛书的时候固执地把客家人谢宏纳入作者名单中,因此遭到质疑,我的回答是,一套以深圳命名的文丛,竟然没有本土作家的文字,这是最大的文本可疑。必须说,了解客家历史和文化基本只能在史料中完成,活着的文化已经稀释到难以捕捉,几乎是做不到的事情。用你的“链接”理论来说,我找到了无数模块,甚至建立起一些网页,却因为缺少关键的参数无法传递指令,这让人沮丧。
林菁:您在这座城市里有具体的客家人朋友吗?
邓一光:有几位。我想告诉你他们当中三位的名字,他们是梁佛金、麦菲和洪志芳。每次提到他们,我总会想起西雅图酋长那句著名的话:如果我们放弃这片土地,把它转让给你们,你们一定要记住,这片土地是神圣的。你要知道,这种感觉非常不好,你生活在一个地方,却不知道它的历史和文化,感觉就像缺氧。
林菁:这部集子里的好几篇小说中,您让主人公用客家方言说话,还有贵州方言,几篇小说都是在《人民文学》和《中国作家》这些北方刊物发表的,北方人完全不懂客家话,似乎您并不在意读者是否理解?
邓一光:语言和人类活动交织在一起,它干脆就贯穿于人类所有的活动中,哪怕具体的人死了,语言还活着,具体的语言死了,抽象的语言还活着。有时候,语言比人物更重要,你可以在故事中置换人物,但语言你换不掉。比如你提到的《宝安民谣》,凌家在安史之乱后从中原迁至岭南,经历过高宗南渡、满清入主中原和太平天国,多少代祖先不在了,凌家人也都移居海外生活,但凌九发还守着祖宅,那是他的家族精神、他的语言。在表达人的生存情境时,文学必须承认包括语言在内的人类活动的有限性和历史性,维根斯坦认为人类“懂得”的有限性不是作为一种缺陷,而是作为认识的必要条件而存在,这对北方人同样管用。
林菁:您的小说里有不容抹杀的幽默感,它们是您信手拈来的,还是在事后回头添加的佐料,用以稍稍化解精神追问过程中所产生的困惑压抑呢?
邓一光:幽默从来不是轻松的,它是故事中最沉重的那一部分叹息。幽默是一种生命立场和生活态度,当它被作为一种工具的时候,比如当作添加剂的时候,它的精神就消失了,徒劳为方法论。海德格尔认为艺术作品不消耗材料,而是使材料本身的色彩和力量凸显出来,它关心的不是有用,而是让存在者显现自身。我觉得你把艺术作品和材料颠倒过来理解,也是可以的。
林菁:不少批评家谈到您的深圳书写企图,如同狄更斯之于伦敦,您这些年致力于书写深圳,是否有意在构筑自己的深圳文学地图?
邓一光:关于深圳文学地图的话题,评论家恐怕有自己的逻辑,他们并不是在说我,而是在说他们自己。这个话题很容易陷入“命名”,以此来讨论语言和存在的关系,瞧,那里有一个被称作“深圳文学”和“地图”的东西,另一端是某人的书写,人们用诸如贴标签的方式把二者联系起来,使某人的书写在现成的词语中形成关联,以便理解,甚而具有新的意义。实际上,从到深圳后开始写第一个故事,我就明确表示,我会通过写作建构“我的城市”,我也是那么干的,你在现成的故事仓库中找不到我的故事胎衣,我的地图建立在主体经验上。
林菁:每个人眼中的城市是不同的,但一般的写作者会局限于某种性别、某个代际与阶层。而您的作品似乎并不受这些影响,且显得游刃有余,您是怎么做到的?
邓一光:我的书写有自由的一面,也有固执的一面,是性格原因,也是好奇心所致。
林菁:每个作家都宣称,他走进人物的心中,驱使他们开始属于他们的社会活动。
邓一光:自由书写取决于作家在与人物共情时是否找到稳定而适合的过渡性客体,你必须通过强有力的想象力“成长”为你的人物,而不是自然或者客观生成。
林菁:这几年,您的短篇数量开始少了,是否与长篇写作有关?
邓一光:2017 年一个短篇也没写,写长篇了。这两年写得也不多,主要是和观察的累进变得复杂有关。当你进入地幔,甚至认为看到了地核,你的野心开始膨胀,开始预谋一次地壳运动,且慢,短篇不需要这个,它不是沧海桑田的生命,你得退回到足够新鲜的细节上去,足够新鲜,不然一个字也写不出来。
林菁:您曾在访谈中提到“城市隐结构”,认为“城市隐结构中那些一代又一代消匿者留下的文化记忆,它们反过来塑造了城市。”发掘城市的隐结构,揭示那些蛰伏的隐喻,是否可视为您深圳系列小说一以贯之的追求?
邓一光:恐怕是所有具有自觉意识的小说家的追求。
林菁:为什么?
邓一光:作为城市显形结构的城市意志不难把握,那是城市作为整体的文本,你只需要雄心和耐力,但城市文化和精神在几乎所有的城市表达上都是倾斜的,不真实,那些被遮蔽了的地下城堡才是小说故事应该去往的地方。小说家在故事结构和主题上所做的工作并不多,他还需要一个更为复杂微妙的世界,康定斯基把它称为隐性结构,他认为艺术作品首先应该是一种内在精神的产品,必须以触及人类灵魂的原则为唯一基础。我现在知道当年在包豪斯学校当教师的他为什么那么讨厌装饰性的神权世界了。
林菁:孙郁老师曾在《文体家的小说》一文中提到:“‘文体家’是对文学家的最高尊称……文体,不是一己个性的天然形成,而是辛勤磨砺,十年为期的道行功德,一旦圆熟,片言只语亦彪炳独树,无可取代……”您的文风很特别,读上几段,我也能认出是您的作品,您是否意识到自己的特别之处,进而有文体方面的探索?文风特色太明显的话,是否会有“副作用”?比如读者读着读着,偶尔会出戏,意识到文本背后作者的存在?
邓一光:关于文体自觉性的话题挺诡异,我有点走神,突然想到香港汉森公司开发的智能人Sophia,她是世界上第一个获得国籍的机器人,据说非常聪明,拥有数种语言风格,不知道她是否打算写小说,那是一些什么样的故事。文体自觉是个高度话题,标准很高,语言风格很多人都拥有,说到形、义、音之美,说到文体贡献,特别说到独特思想,恐怕多数人远不具备,我不认为我属于这类人。
林菁:您的城市不仅仅是人的城市,比如您会关注流浪猫狗的问题,在《风很大》《勒杜鹃气味的猫》《如何走进欢乐谷》里都有体现。流浪猫狗引发了您关于城市什么样的思考?
邓一光:猫狗不但是城市人排解孤独、替代亲情的宠物,而且狗还以接受城市管理法规为代价,获取了合法生存权,是正式的城市居民。关于猫狗商品化、遗弃、节育、虐待、相关法律、政府职责和民间组织功能等内容,社会学家和记者们有很多研究,至于我,我觉得我和TA 是一组镜像,我更关心作为城市生活主体的全部生命在生命塑造、种群关系异化、生态危机和重建中,那些和我密切关联的事情。
林菁:深圳是一座科技城,许多高新技术都在此安营扎寨。科技或许会带来关于人变异和尊严的新一轮探讨。您对人工智能有没有什么展望或者看法?接下来的小说会涉及这类话题吗?
邓一光:去年,全世界关注的几件与中国科技有关的事件,中兴芯片事件、华为5G事件、霍建奎基因编辑事件都发生在深圳。2015 年,我写过一个电影,文体局约的,写一位深圳科学家在一场基因编辑造成的人类危机中的经历,电影没有拍。时隔三年,霍建奎的深圳团队宣布人类首对基因编辑婴儿出生,引起全世界强烈反弹。那个时代已经来了,目前我没有涉及智能人内容的写作计划。我还没有找到通往其他世界的那条通道,无法改变作为人的立场的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