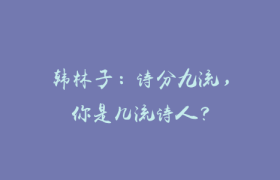一
修辞并不是一种纯粹的技能,修辞是一种意义实践活动,与某种社会实践密切相关,它既维系着生命内在意义的生成,也维护着人类交流的丰富性。这一活动处在“集体图式”(或集体象征图示)与“个人感知”(或个人感受力)之间,集体图式为意义实践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参照框架,个体感知则赋予修辞以即时性的生活语境或偶然的经验语境。集体图式的过度固化会导致意义的僵化,反过来,如果完全缺乏话语共同体所共享的意义参照框架,个人感知则会陷于紊乱。这两种极端状况都会使意义活动归于无效。
并非集体图式总是创造性的,或一定会有利于个人及其社会性的意义实践。支配着意义实践的是什么力量?修辞活动处在什么样的意义参照框架之中?换个表达,个人的修辞方式或社会性的意义实践处在什么样的支配性语境中?
一个极端的情形是,语言被收归国有或集体所有,语言的集体图式及其意义实践被国有化或集体化,在这一极端情况下,个人的修辞活动必须从属于集体象征图式,个人修辞像私有财产一样被禁止或成为原罪。这里引用一个诗人的例证,昌耀1957年写作发表了被称为《林中试笛》的两首小诗,其一是《车轮》:
“在林中沼泽里有一只残缺的车轮,暖洋洋地映着半圈浑浊的阴影。它似有旧日的春梦,常年不醒,任凭磷火跳跃,蛙声喧腾。 车队日夜从林边滚过,长路上日夜浮着烟尘。但是,它再不能和长路热恋,静静地躺着,似乎在等着意外的主人。”
无论在青海还是内地,那是一种常见的木轮高车,或许是破损之后被扔在了路边。作为诗人早期习作,诗写得很一般,不过是对事物或感觉现象的一种写生,或稍稍增加了一点思古之幽情,据说诗人是在深入地质勘探队员生活时一种瞬间所见,他注意到林中沼泽一个残缺的大车轮,把它以写生的方式书写了出来,即使仔细检查遍字面意义或象征意义,也没有任何反对什么的意思。再看《林中试笛》的另一首《野羊》:
“在晨光迷离的林中空地,一对暴躁的青羊在互相格杀。谁知它们角斗了多少回合,犄角相抵,快要触出火花。—是什么宿怨,使它们忘记了青草;是什么宿怨,使它们打起了血架?这林中固执的野性啊,当猎枪已对准头颅,它们还在厮打。”
据说这一情境是来自于一位猎人的讲述。但在当时的社会语境或集体象征图示中,有人对昌耀提出了质疑。他因这样两首并不成熟的小诗而罹难。在那个时期的集体图式中,“车轮”“野羊”几乎不可能被作为一种客体来看待,而被视为一种逐渐固化起来的观念象征,现象世界的描述没有作为个人感知被阐释,而是作为确定无疑的观念符号被看待。在那个时期,“车轮”被置于“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集体图式中,“腐朽”的车轮就成为一种攻击;那么同样,相互格杀的野羊也就成为对阶级斗争或社会环境的讽喻。在“革命象征主义”的集体图式框架内,修辞发生了转义。这是年轻诗人始料未及的事情,事实上也真是冤枉了他,直到诗人的晚期作品,昌耀至死都是他诗中自嘲的“暧昧的”社会主义者。
昌耀的个人际遇表明修辞活动中的一种普遍状况:集体图式的固化取消了个人感知,进而是观念取代了体验,符号遮蔽了真实经验,一切真实的个人感知或个人体验被取消,一切真实经验、切身感受与经验语境都被从人的意识活动及其符号创造与交流活动中清空了,它意味着真实的意义生成被清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社会交流被阻滞了。我们知道,无论是在东方还是西方的历史过程中,源自宗教的集体象征图示基本上支配了某一历史时期的语言修辞活动乃至整个文化艺术的符号创造。只有在这种支配性的集体象征图示衰落之际,基于诗人或艺术家个人感受力的修辞活动才能有力地突破集体图式的固化,并有效地转换集体象征图示使之成为人们可以共享的意义资源与符号表现。
就昌耀所置身其中的修辞活动与意义实践而言,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现代汉语中支配性的集体图式渐渐地弱化甚至消解了,至少在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某些领域里,尤其在诗人创造性的话语活动中,这一集体图式不再对个人经验产生真实的解释作用,也不能赋予个人经验以充分的意义感。在一个短暂的过渡期,集体图式及其象征成为反讽修辞的对象,如这一时期的诗歌对“太阳”及其与“向日葵”象征含义的讽喻式表达。作为一种意义参照框架的集体图式过了价值的保质期。因此,昌耀在整个八十年代的诗歌写作中,他一反“伤痕”式的修辞,有效地将个人的社会感知转换为“慈航”或“苦修”式的宗教修辞,使个人经验发生了普遍性的转义,并受到了较为广泛的认同。但当昌耀在上世纪90 年代经济社会逐渐兴起的历史语境中,当他遭遇到女友跟了一位药材商这倍感羞辱的体验时,当他在诗歌中把这种个人苦痛的感知描述成资本家或食利者“对美的亵渎”和“对美的蹂躏”时,读者或许会发出一丝苦笑,转义难以被普遍认知,修辞变成了反身指向诗人自身的讽喻。这意味着,昌耀企图将个人苦痛再次神圣化的企图遭遇了反讽,当他将个人经验上升为阶级经验或赋予受苦者的阶级属性时遭遇了暂时不问“姓资姓社”语境的反讽。事实上,直到他去世前的最后一部主要作品《一个中国诗人在俄罗斯》,他一直都坚持着这种在他人看来或许是幻觉式的“历史视野”,不肯放弃某种意义上源自上一历史时期的集体图式,在这首长诗中诗人不会说他在莫斯科看到了“乞讨的老妇”,这对他的修辞或意义阐释都远远不足,他使用的修辞是“工人巴别尔的母亲”在挨饿。就作为诗人的昌耀而言,他的经验与修辞之间一直充满张力,也充满了意图的悖谬:他最初的话语企图使用个人感知时遭遇了集体图式的悲剧性强制,他晚期的话语使用集体图式时遭遇到经验语境的喜剧性反讽。作为诗人的昌耀在其一生的写作中,提供了修辞与意义实践的悖论形式,他个人的命运最醒目地彰显了集体象征图示与个人感知之间的戏剧性冲突。
与之同时,在某些历史时段内,一种非强制性的集体图式也在赋予个人的话语活动以意义的参照框架,它既提供意义资源、符号表现,也携带着约束性的机制。当集体图式彻底排除个人感知而不是与个人感知进行互动时,这个模式也就失去了自身的活力,失去了意义参照框架或提供意义资源的功能,变成了一种纯粹的强制体系。
二
什么力量支配着意义实践?在上面所说的一种情境中,语言同生产资料一样被收归集体所有,修辞与意义实践活动如同经济活动一样被垄断,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图式支配着一切话语活动。事实上,在不同的人类社会形态和历史阶段,语言总是某个共同体的语言,修辞活动与意义实践也总是置身于某种共同的意义参照系统之中。然而,就整个现代社会的历史趋向而言,随着源自宗教背景的集体象征图示的衰落,随着语言与观念中的摩尼教式的二元对立的消解,随着符号系统的碎片化,修辞活动的意义参照体系也开始变得模糊不清起来。
这一状况现在变得愈加混杂,正像经济领域一样,修辞与意义实践呈现出某种多元性,在诗学领域几乎显现出一种极端多元性。即使过往的集体图式并不甘愿退出它的支配地位,它也仅仅能在极其有限的语境而非意义语境中起作用,况且还不是出于自发性的认同而是出于各种权宜之计。就今天的历史语境而言,或许并没有单一的意志能够支配意义实践,没有稳定或固化的集体图式能够永久地支配着修辞与话语阐释方式,结构总是受到历时性的冲击并缓慢地变形。在社会话语领域,一切言辞都相等,一切话语都在失去其意义的状态正在出现,作为一种意义实践的参照框架的集体图式变得不甚清晰了。痛苦、磨难或不幸仍然存在,但人们无法赋予其共同认知的意义,不能给予恰当地命名,这种状况或许应该称之为语义实践的中性状态,类似于疲惫或者抑郁。
一位年轻诗人包慧怡《关于抑郁症的治疗》一诗这样描述了上述状况:
现在,我只需把胸中的钝痛精细分辨
命名、加注、锁入正确的屉格:哪些眼泪是为
受苦的父亲而流,哪些为了染霜的爱,又有哪些
仅仅出于战栗,为这永恒广漠、无动于衷的星星监狱里
我们所有人的处境。假如每种精微的裂痛
都能像烦恼于唯识宗,找到自己不偏不倚的位置
像罪业于但丁的漏斗,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每种我不屑、不愿、不能倾诉的苦痛
都将郁结成棕色、橄榄色、水银色的香料
在时光的圣水瓶里酝酿一种奇迹。修辞术在受难的心前
隐遁无踪,言语尽是轻浮,假如不是为了自救
铺陈不可饶恕。假如可以带粉笔进入迷宫,以纯蓝
标记每一处通往灾祸的岔口:“我到过这儿
必将永不再受诱”,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包慧怡在这首诗里提供了一种治疗方案,那就是对苦痛——一个人往往“不屑、不愿、不能倾诉的苦痛”进行“精细地分辨”,分类,命名,加注,这是把苦痛彻底知识化的意图;哪些苦痛是家常的,而哪些苦痛是命定的;哪些苦痛是个人的体验,哪些通向所有人的普遍处境。但在诗人看来,似乎这一方案很难实现,无论是近乎木然的“钝痛”还是“精微的裂痛”,即使你能够指出它们发生在身体的具体部位,却难以在宗教的象征图示即一种意义图示中找到它的位置,就像唯识宗处理“烦恼”,或者像但丁在他的基督教的象征图式中安置人的各种罪业。诗人说,那样的话,苦痛将变得“可以承受”。对象征主义的世界观而言,人们并不承诺会彻底消除苦痛,而是寻找每一种痛苦的“名称”,即苦痛经验在一种有效的宗教象征主义话语体系中“不偏不倚的位置”,它意味着需要赋予苦痛以意义从而使痛苦变得“可以承受”,甚至可以让苦痛“在时光的圣水瓶里酝酿一种奇迹”。革命与宗教的集体图式都曾经渴望在特殊的修辞方式或符号系统中完成这一对人类苦难的意义转化。就像对于唯识宗或但丁的宗教象征来说,这些都是可能的。治愈是可能的。这不仅是因为个人的苦痛在一种信仰集体中被分摊了,也是因为苦痛找到了集体图式所承诺的意义参照,及其与意义相关的修辞确认。
一个社会文化系统——以及承载着它的象征符号——凝聚的意义所遭遇的分崩离析,使得个人的生活实践无法继续保持必要的参照而产生莫名的焦虑。意义模式或文化的象征图式的解体,注定了要由社会与个人承担其不良后果。“修辞术在受难的心前/ 隐遁无踪”,这里隐含着诗人对修辞的一种矛盾态度,修辞是无用的,又是我们必须求助的隐秘意义资源。痛苦没有名字或失去了有意义的名称,然而又只能通过修辞、通过隐喻与转喻间接地、索引式地指向它的名称,否则就无法摆脱苦痛的“匿名性”。对研究过中世纪羊皮纸书的诗人包慧怡来说,其中或许隐含着对一种中古时期的语言、对一种意义较为明晰的集体象征图示的期待,或者是对一种与“圣言”相关的意义参照体系的渴望,对一种能够被普遍分享的意义实践的推许。这首诗的结尾似乎暗示了语义炼金术式的救治方案。
假如我尝到的每种汞与砷
能使你免于读懂这首诗
—它们将变得可以承受,
小病号。
在对痛苦的转化方案中,修辞术与炼金术关联了起来,这是诗中隐含着的等式。诗人所感受的各种不同的没有命名的苦痛也与炼金术者所品尝的“每种汞与砷”画上了隐喻式的等式。“汞与砷”这样的一些“化学”元素,恰恰意味着每一种人类的苦痛经验都等待着被“转化”,事实上,不仅是苦痛经验,每一种人类经验、每一种存在物都期待着转化的时刻,就像诗歌中的每个词语都将在它的隐喻结构中发生意义的转化。因此可以说,经验的转化才是治愈的最终方案。在前现代社会之前,“治疗”或“治愈”不仅是狭义的医学的事情,一切对身体的规训方式、对主体的呵护方式、乃至一切对感觉、感受、情绪的管理方式,都属于广义的或根本意义上的治愈。在柏拉图的对话中,我们能够看到苏格拉底的说法,那就是“修辞学与医学是一回事”的断言。而今医学是一门愈来愈世俗化的宗教- 巫术,而宗教是一种神秘化或升华了的广义的医学,也是一种被高度祛魅化了的救赎方案。对身体的疗救自始至终关乎灵魂的救赎,关乎情感与情绪的管理与转换。它们最终关乎苦痛、肉体的有限性与死亡。起源论的思想资源或许不会耗尽其全部能量,起源时刻的每一点滴都会融进此刻的思想与感受之流,即使只剩下极微弱的含量,也类似于溶剂的作用。宗教一直就是医学的一个广义的名称。宗教植根于人类的苦痛、疾病与死亡。宗教寻求着救赎之路。就是科学与革命也时常暗中扮演这一救赎者-治疗者的角色。然而这一切拯救或治愈,与其说它们发生在事实领域,不如说发生在意义与价值领域,发生在修辞方式之中。在革命象征图示之后,在“圣言的无力”之后,诗歌的修辞活动已经成为这一意义实践的合法领域。
然而,在现代社会,诗人或许还有精
神分析学家,不得不面对一个明晰的意义
体系的消解,一种稳定的集体图式的消失。
他们必须在衰落的集体象征图示与个人感
知的张力中重构一种话语实践。
三
什么样的集体图式能够为个人修辞学提供自由而有效的阐释?或者反过来,什么样的个人感知能够成为可以被分享的意义实践或共享的意义参照框架?什么样的个人感知及其修辞能够为集体图式注入活力或提供新的自由阐释?
或许已经出现的情况是,在修辞活动中对个人体验或社会经验语境的呈现,正在替代某种固化的象征图示,以个人经验与社会语境的呈现替代稳固的集体图式,即意义参照框架。
阿米亥《开·闭·开》“精确的痛苦,模糊的欢乐:渴望的迹象无所不在”第十六节如此写道:
精确的痛苦,模糊的欢乐。我在想,
人们在医生面前描述自己的痛苦是多少精确。
即使不曾学会读写的人也是精确的:
“这儿是抽痛,哪儿是绞痛,
这儿是挤痛,哪儿是烧痛,这是刺痛,
那个—噢,是隐隐作痛。这儿,就在这儿,
对对。”欢乐总是模糊的。我听到有些人
在成夜的寻欢作乐之后说:“真是太棒了,
我开心得快升上天了。”即使抓着宇宙飞船
飞到太空的宇航员,也只会说:“太好了,
妙极了,我没话可说了。”
模糊的欢乐,精确的痛苦—我想用精确的刺痛,描述幸福和模糊的欢乐。我在痛苦中学会了说话。痛苦果真如此精确?除了身体的病痛之外,痛苦的可交流性未必是确然的。要说清楚苦痛与其原因并非一件不需要发展其体验与表达的事。对生活在动荡不安历史中的诗人阿米亥来说,个体只会表达疼痛,表达那些与抑郁、焦虑或者愤怒情感关联的具体化的身体状况,在病人所处的社会群体和象征图示中,也许暗含着一种理解:这些身体不适同时传达着精神的和社会化身体的含义。
无论在昌耀那里,还是在包慧怡或阿米亥那里,一种不可忽略的情形是,激情、道德感受乃至社会伦理情感,也同样在悄无声息地滑入了边际模糊的疾病领域。那些被社会和个人所压抑的激情与社会伦理感情,没有正当的、合法的和受到鼓励的释放空间,进入了纯粹个人的感受范畴,成为一种负面体验,诸如内疚、挫折与失败感。一个人无法长期承受这些负面体验从而难以抗拒地转入躯体化的病痛状态。
即使在强制性的集体象征图示衰竭之后,在人类社会中组织和控制生活的各种支配性的力量渗透了我们的心理-身体状况,它隐秘地建构了一个身体-社会系统,因此,疾病与苦痛的感受不仅仅属于身体,就像在包慧怡的《关于抑郁症的治疗》和阿米亥的诗歌长卷《开·闭·开》中所揭示的,苦痛的感受也属于社会文化的一个表征。合法的和理性的支配力量被人们顺从地在理性的范围内接纳了,而那些令人感到丧失尊严、令人羞辱与苦痛的控制也在更加剧烈地不适应的感受中被人们内在化了,后者造成了更深的和更普遍的伤害。
语言、修辞与表达,承载着或管理着情绪、感受、体验与认知,修辞形式就是一种能量形式,当这一能量受到阻碍,无法进入自由交流与交换,就不仅只是制造了个人的和躯体化的苦痛,也造成了难以言说的社会磨难。在诗学中,我想也在精神分析学中,存在着一种持续发展着的体验能力,这一体验伴随着修辞与意义实践的过程,伴随着感受力、感知力和想象力的发展。这一意义实践有一个进入合法性的名称,即诗学与艺术。通过个人感知及其修辞活动生成含义的能力被审慎地界定在审美领域。而对诗学与艺术带来诸多启迪的精神分析及其对话无疑也属于这一领域。
个体表达了苦痛的躯体化层面,医患双方都关注着疾病或病痛的这一具体化的身体状况,精神分析则专注着疾病与病痛的心理学含义,就像诗人和读者专注于个人体验在独特的修辞活动中转义的发生。事实上,在医学之外,在革命象征图示与宗教的话语实践之后,关于个人的痛苦有着更为广义上的关注,各种话语实践诸如哲学,社会学,伦理学,还有诗学,以各自的修辞方式描述着人的各种隐秘的苦痛,它们关注的既非单纯的疾病亦非只是身体的病痛,而是关于痛苦和人世间应对苦痛的一种文化实践。诗歌不是一种消除了专有神名的宗教吗?它像医学的案卷,记录着内在的苦痛,寻求着慰藉的方式,或许,诗学在今天就是一种广义的医学,即一种对个人或人类苦痛的命名和救赎。
阿米亥想说的或许并不是我们真的能够轻易地说出痛苦,而是在痛苦中生成修辞及其意义实践的那种困难的努力。宗教话语或圣言,曾经是一种语言共同体所共享的修辞方式与意义参照体系,现在,除非是在一种极端主义的语境之内,这一集体图式或圣言早已变得软弱无力了,而诗人仍然能够将一种个人感知及其修辞融入其中,与之构成一种基于经验世界的对话关系,从而更新这一疲惫不堪的语言:
现在就用这疲倦的语言说吧。
一门被从圣经的睡梦中撕裂的语言,眩晕着,
从一张嘴晃到另一张嘴里。用这曾经描绘过
神迹与上帝的语言,来说出汽车、炸弹、上帝。
……
无论是我们称为圣言的无力还是阿米亥所说的“疲倦的语言”,都意指着某种集体象征图示或集体符号,它们曾经凝结着某个共同体的记忆与感受,但现在,集体象征图示或符号不再是毫无疑义的真理系统,不再是某种统一的、固化的集体图式,也不是将一种“社会方言”上升至强制性的真理语言,但在诗人在个人的现实感知中使用这“疲倦的语言”之时,他就在改变一种语言固有的或固化的象征图示,就是在将先前的象征图示置于某种流动的经验语境之中,正是这一经验语境中存在着差异而又可以交流的体验,彼此不同而又可以共享的情感,一种基于多元话语实践和充分交流所形成的情感的共通感,将成为个人体验与修辞活动的意义参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