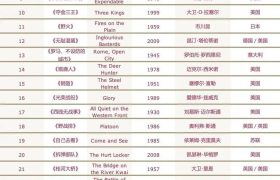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妈妈和七天的时间》讲了重庆的一个小山村里,
已经生下三个女儿的妈妈,
第四个女儿即将临盆,
她将因为这一次分娩而死去。

外婆和妈妈
影片用疏离而冷静的眼光审视了她生命中的最后七天,
一次次步行,一次次吃饭、一次次告别,
贫穷闭塞的山村,长年在外务工的男人,
虔诚追求儿子的女人,
相依为命长大的女儿们……
影片入围威尼斯电影节和釜山电影节,
在今年10月的平遥影展上获“费穆荣誉最佳影片”,
法国《电影手册》主编盛赞此片不仅是“中国乡村编年史”,
而且片子“对纯粹和极简的追求”,极具“启示性”。

主人公小咸(右)和两个妹妹
11月,我们在深圳采访了此片导演李冬梅,
这部片子高度复原了她本人的真实经历,
12岁时母亲因为生育突然去世,
27年后她才从打击中稍稍复原,
“这不止是一部电影,
我终于和母亲好好做了个告别。”
自述 李冬梅
撰文 宋远程 责编 石鸣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用134分钟耐心地讲述了一个村庄里的七天。七天里面,发生了三次死亡,两次出生。人们每吃一顿饭,每走一段路,都被如实反映在真实的电影时间里。
片中的女主角叫小咸,是家里的大姐,12岁左右,二妹8岁,三妹3岁多到4岁。小咸的爸爸在外打工,常年不在家,妈妈为了生儿子,又怀了孕。
影片开始时,家里的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妈妈无暇顾及女儿们,三姐妹相依为命,小咸除了自己上学,在年幼的妹妹面前,也会无意识地承担一些母亲的角色。


主人公小咸
片子从住校的小咸周日回家开始,一家人平平常常一起吃饭,吃完饭后,妈妈大着肚子把她送到回学校的路上。
然后时光一天一天流逝。小咸在学校里,妈妈在家里。第五天,临产日到了,没想到这一胎妈妈却难产了。
村里人抬着病危的妈妈走过漫长的山路,终于抵达镇上的医院,医生宣布抢救无效死亡,人们只好又抬着产妇的遗体原路返回。
等小咸回到家里,妈妈已经变成了一具不会说话的冰冷尸体,旁边多了一个哇哇啼哭的四妹。

平遥影展上,《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拿下了藏龙单元的最高奖“费穆荣誉最佳影片”。授奖词说,这部片子“有一种沉静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时间的沉淀,来自细节的真实,来自纯粹的影像。这种力量看似不经意,却非常地难能可贵。”
导演李冬梅是重庆人,影片取材于她本人的真实经历。她考出家乡的小山村后,到澳洲读了电影。《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是她的第一部长片,也是她来之不易、甚至有可能是唯一的一次拍片机会。


小咸的二妹、三妹
获奖后,她马不停蹄地赶赴深圳,去那边一个影像工作坊担任导师。我们在深圳见到了她。尽管已经接受了许多采访,但在被问到“为什么《妈妈》这个故事非讲不可”的时候,她依然有些哽咽。
母亲的去世是她多年来不敢面对的创伤,27年后,电影让她终于与12岁的自己达成和解。

以下是李冬梅的自述:
《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有一点半自传的性质。片中的小咸,母亲去世的时候是12岁,我的母亲去世时,我也是12岁。
母亲去世那天是1992年农历八月二十九。电影几乎再现了我的记忆:我和母亲最后一次吃饭,我们吃了什么菜,大概说了些什么话,走的时候她送我,然后我把妹妹带到学校去。

小咸与妈妈的最后一顿饭
“七天”这个概念也是真实的。我不是说要去追求一个宗教的七天,而是事实上我对我母亲去世的记忆是从星期天开始的。我们那个时候读中学是住读,每个周五回去,周六待一天,星期天就要从家里回到学校去。
等到我五天之后回家,妈妈已经不在了。我和妹妹放学回来,五天前刚见过的母亲已经变成一具尸体,躺在房子的角落里。几个小时前医生宣布了她的死亡,我和妹妹跪在地上就哭了起来,不敢相信这是事实。

妈妈的葬礼
这个事情对我影响非常大。好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过要把它拍成电影,写了好多剧本都没有写过这一段,可能情感太过强烈。很多年来我不愿意谈论死亡,不愿意去想起我的母亲,听到哀乐我就会难过。每次去母亲坟上祭拜,走在那段路上我都会发抖。
直到有一天,我在公园里散步,我想,我好像到了这个年纪,去触碰一些以前不敢面对的回忆。
我想让观众切身感受生而为人的艰辛
电影是在我的家乡拍摄的,重庆巫山的一个小村子。我在那里生活到12岁,上中学后离开,但每年还是会回去,因为那里还有一些家人。电影里拍到的那些石头房子,二十几年来那些人一直都住在里面。

我的家乡最大的特点就是山多。我们每次不管去哪里,都要爬过一座一座山,公路也要在很陡的半山腰去凿出一条路来。雾也多,夏天多雾多雨。
电影里孩子们上学走的那些路,也是我当时上小学要走的路。那条路我走了6年,单程步行要两个半小时。

孩子们的上学路
村子里面的时光是非常安静的,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我记忆当中,吃饭就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电影里拍了很多吃饭的场景。
每一次吃饭几乎都是一次离别。每一次坐在同一张饭桌边的那些人,吃完这顿饭,再没有机会相聚过。
我的电影里拍了很多睡觉,很多吃饭,很多走路,用固定的长镜头。因为我希望观众跟着电影中的人物一起去经历这些物理上的时间和空间。

有的时候,摄影师也会和我有分歧,比如为什么不拍中景、近景,为什么镜头不移动。其实我不是为了去模仿谁,这个片子从头到尾我都是在凭着本能去拍,听我的身体、我的直觉的指挥。
像妈妈难产后生命垂危的那场戏,村子里的人为了救她,把她送去医院。因为山路太难走了,只能慢慢抬过去。其实这条路,就是我母亲当年走过的最后的路。
你看着他们这样走着,就会更清晰地感知到,人活着就是这样子,生命一点一滴地这样流逝,这是生而为人的艰辛。

村里人抬着病危的母亲
电影里面的演员全部是素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从小到大都是在那个村子里长大的,有一两个是镇上或者村子周边的。
我的一个叔叔是这个电影的外联制片,他带我去串门,跟这些人聊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发消息说我们在招演员。让我们很惊喜的是,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大家参与的热情都很高,两天之内我们就面试了两三百个人。

片中小咸一家
找演员的时候,其实我没有太注重演员的外在形象。但是可能潜意识里就会去找和我的家人比较像的演员。比如外婆,她是小小的个子,爷爷比较瘦,看起来比较老实。
我和小演员的童年还是很相似的,所以我们之间沟通都比较容易。我也需要小演员们理解我为什么要拍这个电影,为什么要这么拍。所以有些故事我跟他们从头到尾分享了一遍又一遍。有一次拍了一天的重场戏,孩子们都哭累了,一般的专业演员都哭不到那个样子。他们是真的把自己的悲伤哭了出来。

对于我自己来说,拍这个片子最大的困难还是情感上的。写剧本的时候就很艰难,写着写着觉得写不下去。勘景的时候,回到当年的那些场景里,我常常控制不住自己,泪流满面。拍电影的过程,我又接受了一遍情感的煎熬。
这么多年以来,我的生理年龄在长,现在已经三十几岁了,但我的心理年龄一直还停留在12岁。母亲的去世让我感到极为无力又惶恐不安,好像瞬间被整个世界抛弃。

我做了很多事情,去跟这个12岁的小女孩建立联系。电影学院毕业时,我拍了个短片《阳光照在草上》,也是回到老家,回到《妈妈和七天的时间》的同一个地方,拍了同一所房子,故事讲的是村子里一个老人的去世。
这次拍完《妈妈和七天的时间》,我觉得我终于长大了。我心中那个小女孩的声音已经被听到,她已经被看到。从此我不会再纠结于12岁的那一个星期给我带来的伤痛,现在我是一个更加有力量的人。

这部片子是从一份15万5千块的平安保险保单开始的
我小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什么书。有一次,我捡到了一本书,没有封面,我看了很多遍,还做了很多读书笔记。好多年之后,我才知道那本书是《安娜·卡列尼娜》。
一个贫穷的农家女孩子,对于文学和艺术的启蒙,对于女性意识的觉醒,可能就是从那本书开始。片中我拍了一场戏是小咸在床上看书,看的也是《安娜·卡列尼娜》。

我是我们村子的第一个大学生,考上了四川外国语学院,选专业时选了英美文学。文学和故事有关。小时候我喜欢听故事,老人们讲的故事特别生动,长大以后我也喜欢讲故事。
因为小时候妈妈去世得早,爸爸常年不在家,我被很多老师照顾过,所以大学毕业就想当老师。我很喜欢我们村子里的那种气氛,所以就回到离我们村最近的一个中学去当英语老师。

李冬梅导演在澳洲
几年之后,我还是感到一种不满足。那个时候离开家乡去深圳创业。挣了一点钱之后,我想再读点书,学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就去了澳大利亚。有人说我拍照片拍得不错,建议我学摄影,我还是希望自己能讲故事,所以学了电影。
决定做电影时,我已经31岁了。考电影学院之前,我对电影一无所知,看片量不超过50部。我就先读了一个一年的基础班,第二年再开始读本科。

有一天,我走进一家空荡荡的电影院,里面正在放映一部关于一个伊朗女孩日常生活的电影。那是一个女性的很私密的故事,女孩的爸爸很想要一个男孩,当时我很有共鸣,原来这个世界上不只我一个人有这样的困境。
2015年12月,我从墨尔本大学毕业,毕业之后就真正的失业了。独立创作者完全没有钱,直到有一天,有人说可以帮我找投资来拍一个东西。我想如果我只有一次机会拍电影,那就只能是《妈妈和七天的时间》。

李冬梅导演在片场
片子开拍后,所有的剧组成员都到片场了,但是说给我投资的人没有兑现承诺。我纠结是不是要解散剧组。我四妹说,姐姐你不要担心,她把她之前买的一份平安保险的保单拿去做了抵押,贷了15万5千块钱。
所以这个片子就是从这笔钱开始的,一边拍一边借钱。

《妈妈与七天的时间》拍摄现场
2018年的8月1号开拍,拍到9月初,花了三十几天拍完。剧组的团队都是凑的,摄影、美术,三十几个人,大多以前都没有合作过,一边拍一边磨合。
在澳洲学电影的时候,老师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一定要保留你自己的声音。拍这个片子,我从头到尾都在努力坚持自我。
母亲难产去世,对于我自己来说,是一种个人的生命体验,在这种体验之下是关于生死的探讨。

长明灯
二十几岁的时候,我觉得死亡是一件特别悲哀的事。但是现在我对生死的感悟,随着年纪增长,变得不一样了。
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昙花一现的事情。一条河流的声音都比人要永恒。甚至是一棵树,它都可以比你活得更久。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我之所以选择用了这么多16mm的镜头,是因为从人类或者世界的角度出发,每个个体的存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我们的悲喜、我们的生死,是不是也没那么重要?

片子最后,小咸和妹妹为妈妈点亮了两盏长明灯。这是我们那里延续到现在的习俗。我们的文化里面相信人是有投胎转世的,会有第二次生命。在转世的过程中,会走过一段长长的黑暗之路,所以要送这盏灯给这个灵魂。
我在片中安排了这样的对白:
妹妹问小咸说:灯会熄吗?
小咸回答:我不知道,也许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