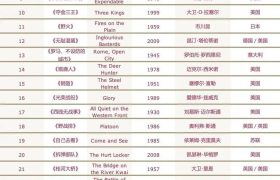1997到1998年期间,在日本北九州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恐怖连环杀人事件。凶手通过拷问、精神控制和电击虐待等方式,促使被囚禁的一家人自相残杀,其中包括两个不到10岁的孩子。
几个月后,直到一人逃出,事件才被曝光,最终有6人在这起事件中死亡。到底凶手使用了什么手段,才使原本相识的一家人互相残杀?而又通过什么手段不断掩盖罪行?仅仅这宗离奇但又真实的案件本身就令人困惑与着迷。

如果交给一位普通导演来诠释这个故事,对方极有可能采取改编或者半纪录片的方式,亦真亦假的去呈现这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以此一窥幽暗的人性阴影。但落到了日本邪典片大师园子温手里一切就变得复杂和鬼魅了起来。
他将这场离奇的事件作为故事核心,拍摄出《在无爱之森呐喊》,并且得到了奈飞支持,走上了流媒体的发行之路。众所周知,园子温的影片因为尺度太大。并且,园子温总在挖掘深刻的主题,但同时也没有抛弃诗人般的浪漫主义情怀。在他的影片中有时候死亡会和美好的画面、甜美的音乐一同出现,更显示出现实的残酷与无奈。

虽然能得到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的荣誉,但显然园子温的影片并非主流院线的香饽饽,而且经常激起卫道士的抗议,令众多发行商头条不已。这一次,《在无爱之森呐喊》同样以超越常规限制级的程度示人。
但所有的血腥和夸张只是表面,“糖衣”溶解后,故事的内核才是恐怖的源头,观众猛然发现原来“戏非戏,假亦真”,所有影片中出现过的场面都来自现实,最生猛的、最让人匪夷所思的绝非虚构,而是现实本身。

故事讲述了一群混乱的滥情男女,借拍电影之名,企图搅乱现实与虚拟世界,期间穿插着两位女主角的伤痛往事、森林里的连环杀人案、父权压迫的原生家庭和利用自身魅力控制他人的变态等支线。
影片以初来乍到的阿信作为切入点。从乡下来到东京的他,对大城市的未来充满期待,他意外结识了两个怀揣着电影梦想的年轻人。

三人一拍即合准备拍一部作品参加电影节完成自己的梦想。三人找到颓废女子妙子,而妙子想到了自己的同学和好友美津子。妙子和美津子都因为见证了好友的意外死亡而遭受了精神重创,久久不能脱离深渊,反而越陷越深。妙子反叛一切,靠滥交压抑伤痛;而美津子闭门不出,靠意淫宣泄欲望。三个大男孩的拍片请求并没有打动两人,妙子也无法拯救自己和她的朋友。
眼看又是一场泡影,可神秘男子村田丈的意外介入,却让事件发生了转机。村田丈大肆追求美津子,但妙子知道村田丈的恐怖过往,于是邀约阿信三人跟踪他,拍摄下他的丑闻,想揭露其罪行,让沉迷情爱,不能自拔的美津子醒悟。

阿信想要拍摄一个离奇的故事,妙子想要拯救自己的朋友,但所有人真正聚合到一起后,事情却朝着无法预料的方向,以急加速的方式冲向了地狱深渊……
《在无爱之森呐喊》是园子温的自我致敬之作。151分钟的观影过程就是一场大型的“园子温旧作观光巡礼”,那些熟悉的元素接连出现,仿佛看了两个半小时的园式混剪。虽然人物和线索众多,但在表达方式上还是园子温的套路cult特性爆棚。
但无论是第一次看他影片的新人,还是熟悉他恶趣味的老咖,其实要的就是这种“不变”,永远生猛,永远反叛,堕落到底。《在无爱之森呐喊》用了“戏中戏”的方式来表现荒诞,不断模糊现实与虚构的界限。

一开始阿信三人认为拍电影是自由的,能够在电影中完成现实中无法完成的夙愿,比如杀人、尽情的施展暴力,宣泄欲望。但当村田丈以精神控制的方法,成为他们的偶像,教会他们使用暴力,进而让他们自相残杀,掩盖罪行后。

阿信的朋友猛然发现,原来不是电影解放了现实,而是现实从来都是高于电影,电影不过是低配版的现实而已。一行人在电影之中拍电影,推倒现实的壁垒,他们无不渴望人生如戏,却往往亡于人生成戏。

不光是阿信三人因戏成魔,两位女主角也有一段因戏结缘的过往。美津子对女性好友产生欲望,陷入了《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情景中,由此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和心理依赖。但她发现妙子占有了对方,而对方最终惨死车轮下后,她的现实欲望与戏剧欲望冲垮了她对真实与虚构的理性区分。美津子沉迷在《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戏剧想象世界中,逐渐与现实世界隔离,活在了自我的欲望和虚构的想象中。

因为与现实脱节,她成为了第一个被村田丈控制的女子,进而不断引发了妙子、阿信,以及长期以父权控制美津子的父母。村田丈用拍电影对他们进行洗脑,让发生于现实中的北九州恐怖连环杀人案在银幕上得到了“逼真”呈现。
园子温曾说过,“残忍即美好”,这句话也点穿了他的创作宗旨。摧毁美好的事物,是残忍的,但这个过程同样可以是美好的。因为在电影里,一切都是自由的,真实的。园子温电影中所有重口味的一面都是为了让人看到包裹在破碎人生当中的爱和救赎的力量。
任凭欲望流淌,正是cult电影的邪典精髓。而自由的表达,往往籍由“不自由”, “不自由”来自电影本身的边界,所有的离经叛道和怪力乱神,都仅限于镜头之下,银幕之上。

所有的血腥、荒诞、残酷与暴力都是为了褪去人性虚伪,隐藏自我的面具,待伪装被揭露,我们才能直视其灵魂,看到了事件背后的真相,触及琢磨不透的人性。

这就是园子温电影实验主义者的创作本质,他希望借助电影颠覆一切,实现自由,抵达真相。而在他的影片中,实现颠覆的切入口,那些符号化的隐喻,常常落脚到了人物服饰身上,比如学生时代的水手服。
在《在无爱之森呐喊》中,高中时的记忆不断闪回,水手服意味着青春的美好,同时也带有同伴意外死去的悲伤,意味着刚刚喷薄而出的爱欲无处停摆,是梦魇,是一辈子走不出的伤痛。园子温多次在影片中以学生水手服表现颠覆,赋予人物全新的心理状态,作为人物弧光的转折点。

先清纯,再毁灭,直到让水手服被鲜血浸透,一遍又一遍地将美好的事物揉碎给观众看,让水手服承载起更多主题和所指。

水手服带来的是一个身份设定,它意味着少女、学校、课桌,可当她们错位出现在灯红酒绿的风俗街,或是床上时,带来一种打破预设的刺激,情色意味也将加倍。

作为校服的水手服,那么长时间里,作为清纯的象征,可崩塌却只在几个瞬间,并且从此不可逆,这便是人类的真实想法和欲望。

园子温所做的,就是将欲望影像化,将其放大罢了。与此同时,在其上增加更多重的含义,除了“情色与清纯”,还可以是女性意识,是自由渴望,是圣教,是对抗父权,是青春创伤。
在《在无爱之森呐喊》里,水手服同样有着以上所有的赋意过程。无论是墙上的水手服海报,亦或企图反抗、相约赴死的同学,还是最后临死前的回忆,作为园子温最复杂的象征性符号,水手服成为其植入伤痕累累的往事、日本青年的精神异变、权欲交织的当代生活等议题的通道。

园子温以变态到极端的方式去书写纯情、用夸张到令人胆寒的方法去刻画真实,这份纯情与真实,正是园子温对电影的热爱,是他献给电影、自己过往作品的一封的情书,也是企图揭露真相,鞭笞社会的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