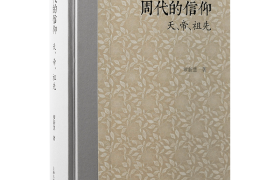一
《五石之瓠》是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上册)中的一篇课文,文章选自《庄子·逍遥游》,内容如下:
惠子谓庄子曰:“魏王贻我大瓠之种,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世世以洴澼絖为事。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
这段文字反映出了庄子怎样的思想?或者更直白地说:庄子与惠子到底在争论些什么?——这是一个在备课过程中让人颇费踌躇的问题。

庄子与惠子的争论
在课文后面,附有教材编者撰写的一段“学习提示”,对这段文字的意旨做了如下说明:
“庄子善于从常人认为没有价值的事物中发现价值。在《五石之瓠》中,惠子仅从日常使用的层面上考虑大葫芦的功用,庄子则超越了世俗经验的束缚,指出了大葫芦的独特价值。”
从教材所节选的《五石之瓠》这段文字来看,这样的解释并不算错——庄子与惠子所争辩的确实就是如何使用“五石之瓠”,或者说是如何为“五石之瓠”赋予意义与价值的问题。 但如果我们把这段文字带回到《庄子》原文中去,就会发现这种仅从字面出发所作的解释是与整篇文章的主旨——“逍遥游”——扞格不入的。
什么是“逍遥游”?按照庄子的意思,就是“无待”。“有待”与“无待”的问题也正是《逍遥游》这篇文章所讨论的核心问题。
通览全文,文章开篇处写到的大鹏,虽然可以“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却并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逍遥”,因为它的飞腾仍离不开风力的托举,它仍然是有待的——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而后乃今将图南。”
与大鹏相比,蜩、学鸠、斥鷃等“小虫”反倒像是完全“无待”的了——你看,它们可以“决起而飞,抢榆枋而止,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或是“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间”,不是逍遥自在的很吗? 可惜,它们的这种“无待”并不是真正的无待,而是一种虚幻的、末人式的自由,一种浅薄不学、栖身于孤岛之上的独立。就像海德格尔所说的那样:
“小人物之所以‘小’,恰恰因为他自以为是不依赖任何人的。而伟大的思想家之所以大,是因为他能够从其他伟人的著作中听出他们最伟大的东西,并且能够以一种原始的方式改变这种最伟大的东西。”(海德格尔《尼采》第6节)

大鹏鸟
真正的无待并不是像这样不自由地陷入了自由,或者说是自由地选择了不自由。在“寄旨鹏鷃”,明“小大之辩”(明“小大之辩”也终究是为阐明有待、无待这个问题服务的)之后,接下来的一段文字就是庄子对“无待”问题的正面阐述。这,也是《逍遥游》一文的核心语段,值得我们认真玩味: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而宋荣子犹然笑之。且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依照钟泰老先生《庄子发微》里的说法,“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三句是“全篇之要旨”,也是对“无待”问题的进一步剖释与阐发。这以后的文字都是在以“寓言”的形式说明这三句话的道理——“尧让天下于许由”一段讲的是“圣人无名”;“肩吾问于连叔”一段是在说“神人无功”;而庄子与惠子的问答,也就是课文中所节选的“五石之瓠”和后面的“吾有大树,人谓之樗”两段,则是在阐明“至人无己”的道理。
《逍遥游》结尾的这几段文字是不是完全能与“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一一对应?我们不敢断言。 但依照通常的行文逻辑,连同“五石之瓠”在内的这几段寓言,总不该脱离了全文所要揭示的“无待”这一主旨,宕开一笔,去另谈什么“从常人认为没有价值的事物中发现价值”的问题。
所以我们认为,五石之瓠也好,不材之木也罢,“无论是说大树还是大瓠,庄子说的都是大人,有一个大心的人。”(王博《庄子哲学》第七章) 易言之,庄子与惠子真正关心的不是物,而是人;文章中的“夫子固拙于用大矣”所要讨论的,从根本上说,不是一个认识论或者价值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存在论的问题;不是一个大瓠、大树到底是有用还是无用的问题,而是人生所要追求的是有待还是无待的问题;不是一个如何发现并赋予外物以独特价值的问题,而是一个如何让自己活出理想的生命意义的问题。
而其中的“用”字大约也有着双重含义,一面是指向对客体的使用、利用之用;一面又是指向主体的如“潜龙勿用”式的施用之用——这种理解,相较于教材中“学习提示”,似乎更能合乎庄生的本意。
二
《五石之瓠》中庄子与惠子所争论的话题既然不是“物”的有用无用,而是“人”的有待无待,那么我们接下来就需要探讨:什么是有待?什么是无待?——这其实也是庄子研究中一个热门话题,相关的论述文章可谓汗牛充栋。在这里,笔者也想将自己的浅见贡献出来,请大家批评指正。
我认为,在《五石之瓠》中,庄、惠之间的分歧就是20世纪德国大哲海德格尔提出的“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或者叫做对存在的“本真”理解与“非本真”理解——的中国式的表达。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说:
“此在(人)的‘所是’或‘本质’在于它的生存,此在(人)的各种性质都不是它的现成属性,而是它去存在的种种可能方式。因此‘此在’这个名称并不像‘桌子’或‘树’这样的名称,‘此在’并不表达这个存在者是什么,而是表达它怎样去是,表达其存在。此在就是它的可能性,它作为它的可能性存在……所以此在可以选择自己,获得自己,也可能失去自己。只因为此在(人)有可能去是它自己,它才可能失去自己,或者还没有获得自己。此在(人)立足于自己本身生存,我们称之为‘本真生存’(Eigentlichkeit),反之就是非本真生存(Uneigentlichkeit)。非本真存在并不意味着较少存在或较低存在。非本真状态反而在忙碌、激动、嗜好中规定此在(人)。”(参见《存在与时间》§9。后文引用此书只标注节号。因原文晦涩难懂,为了方便阅读,本文中的相关引文全部出自陈嘉映先生译写的《〈存在与时间〉读本》)
海德格尔认为,“本真”的存在方式指的是一个人“立足于自己本身生存”,拥有自己、获得自己的存在样式;“非本真”的存在方式则是指一个人失去自己,或者从未获得自己的存在样式。
一个人怎么会有“失去自己”或者“还未获得自己”的情况呢?这里的“失去自己”近乎一种隐喻。我们试想:一个人沉沦于世间,埋头于所从事的事务,把自己的身份或者自己所做的事情当作了最原本、最真实的自己——譬如,我们常常会说:我是个工人,我是个农民,我是个教书的,我是个做生意的——总之,是“从操劳所及的‘世界’来领会自己”(§53),从那个彼此指向的、意蕴关联的网络中来理解自己,把自己当作了这个意义网络中的一个“结点”,忘记自己本来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个体。这,难道不是对生命存在的一种错失吗? 孔夫子说:“君子不器。”非本真的存在者就是要把自己当作“器”——日复一日的东跑西颠、左右逢源、忙忙碌碌、到处张望,把自己当作商品,当作货物,当作一件可以用来做点什么的工具,或者用海德格尔的话说,当作了一个“现成的存在者”,成为一个平均化的、循规蹈矩、按部就班、可有可无的“常人”,时时迎合着“公众”“大家”“别人”等尺子的比较与衡量,直到临近告别这个世界的那一天,才发现自己似乎并没有真正地活过。
我们看《逍遥游》里的“五石之瓠”或是那棵“立之涂,匠人不顾”的樗树,似乎就包含着这样一种人生隐喻——“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无论是大瓠还是大树,你总得“作为什么”而存在吧;你总得通过自己“能做什么用”来彰显“自己是谁”吧;你总要“有待”于这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寻找自己的位置和意义吧!所谓“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大宗师》)——这大约就是在这则寓言中惠子对于存在问题的基本认识。
而本真的存在则近乎“无待”,指的是一个人“立足于自己本身生存”,对自身的拥有。人是可以对自己的存在做出选择的——选择不消散于世界之间,不消散于对外物的运用操劳、与他人的周旋操持之中。杜牧说自己“在群众欢笑之中,常如登高四望,但见莽苍大野,荒墟废垄,怅坐寂默,不能自解。”(《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启》)正是这样的一种被称作“畏”的情绪,“把此在(人)开展为个别化的存在”,“使此在(人)不能再从‘世界’以及从公众讲法方面来理解自身”,“使此在个别化为其最本己的在世,使它从最本己处领会自理解自身,从本质上向各种可能性筹划自身” (§40),从日常的、沉沦的非本真的存在走向本真的存在。
人何以能做出这种本真存在的选择呢?在海德格尔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永远藏身于“万人如海”之中,不可能永远藏身于众说纷纭之中,不可能永远藏身于世俗的荣辱得失之中。 总有一件“大事”或远或近地在前面等待着他,要他去独自面对——那就是死亡。于是,我们不妨先行到死,站在我们即将离开人世前的那一刹那,回看自己的一生,决定自己当下的取舍行藏,“看清楚了丧失在常人之中的日常存在,不再沉陷于操劳和操持,而是立足于自己的生存筹划种种生存的可能性,面对由畏敞开的威胁而确知它自己,因负重而激起热情,解脱了常人的幻想而更加实际,在向死存在中获得自由。”(§53)
《逍遥游》里说宋荣子“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宋荣子也罢,庄子也罢,虽不曾有这样“先行到死”的决断,却也通过自己独有的路径抵达了本真存在的境界: 我们要关心自己的存在本身,无待于这个充满了庸常意义的世界,回归自己作为个体的生命中来——这与“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的境界得毋有些相似之处呢?
如果觉得这两则寓言所表达的寓意还不够鲜明,我们不妨再读读《逍遥游》中的另一则故事——
“尧让天下于许由,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许由洗耳
“鹪鹩巢于深林,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天下对于许由而言是“无所用”的,他不需要通过“天下”、通过“世界”、通过“他人”来获得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而是“在众不失其寡,处言愈见其默”(颜延之《陶征士诔》),通过回到自己的自身性与个别性中去,回到自己本真的存在方式中去,进而建构一个属于自己的意义世界。——这大概可以算是对“无待”问题的另一种形象化的说明。
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由此认为,本真存在是一种好的、正确的存在方式,非本真存在是一种坏的或者是错误的存在方式?话还不能这么讲。 在海德格尔看来,本真与非本真只是就人与自身存在的关系而言的(是敞开的还是遮蔽的),并不具有一种伦理学上的意义。用更直白的话说,这二者之间只有主从之分(人首先是属于自己的,才存在失去自己的可能性),却没有对错之别——会有一种虚假的、错误的本真性,也会存在一种真正的非本真性。这体现在《逍遥游》中就是在“有待”“无待”维度之外的“小大之辩”——蜩与学鸠所自以为的自由自在、无所依傍就是一种典型的错误的本真性;而庄生笔下“海运注则将徙于南冥”的大鹏则是真正的非本真性的代表。
实际上,一个人活在尘世间总会不由自主地、不可避免地以非本真的方式存在着——“此在(人)首先和通常正是以非本真的方式存在着”(§41),因为人就是依寓世界而存在的,人的存在就是“在世界中存在”。在世界中存在是“此在(人)的基本建构,此在一向经历着自己的在世。”(§13)所以,人总是要从世界获取意义的——“本真生存不是脱离世界的生存,自由总是沉浸在某种事业中的自由。”(§40)
古人向往“飘飘乎遗世而独立”的境界,殊不知这个“世”是任何人都“遗”不了的——“世界就是此在(人)作为存在者向来已曾在其中的‘何所在’,是此在(人)无论怎样转身而去,但纵到天涯海角也还不过是向之归来的‘何所向’”(§15)。孔夫子说:“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我们可以把这个话改一改:“吾非斯世之寓而何寓?”—— 你要做“成实五石”、“瓠落无所容”的大瓠,总要有“江湖”可以漂浮;你要做“絜之百围,其高临山”的大树,总要有“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可以矗立。人终究是有待的。绝对的脱离世界的本真存在,永不可得。我想这大约也是“无待”这个词自始至终没有直接出现在《庄子》一书中的原因之所在吧?
由此可见,在《五石之瓠》里,庄子与惠子之争不是一个简单的对错是非之争,而是从不同侧面揭示了人的存在方式的不同可能性,使我们能够对人的整个生命存在有更丰富、更深刻的认识。
据说,庄子在惠子死后,经过他的墓地时说:“自夫子之死也,吾无以为质矣,吾无与言之矣!”(《庄子·徐无鬼》)——把这句话用在他们二人围绕着有待、无待,或者说是本真存在与非本真存在问题所展开的争论上,倒真是再恰切不过了。
三
黑格尔说,真理总是一个体系。
把庄生的“有待”“无待”与海德格尔的“本真存在”“非本真存在”进行这样“思想切片”式的比较,从学术层面看,实在太嫌粗糙,也免不了会引起种种质疑——
“在《逍遥游》中,庄子认为无待的状态是‘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既然是本真存在是让一个人回到自己的自身性与个别性中去,怎么还会存在一个‘乘天地’‘御六气’的问题呢?”(这其实是庄子研究中的一个老问题:“御六气之辩”和列子的“御风而行”到底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
“如果无待指的就是本真存在,那庄子所谓的‘至人无己’四个字又该做怎样的解释呢?”
……
这些质疑其实已经涉及到了庄子与海德格尔整个思想体系的异同问题。要把这些问题说清楚,恐怕非得写一篇大文章,对二人极为丰富深刻的哲学思想加以系统性的阐释与比较不可。而这一方面实在不是笔者的学力所能及,另一方面也离我们围绕《五石之瓠》这篇课文所进行的探讨实在太远了些。
不过笔者还是想在这里——仅就自己非常肤浅的理解——对庄、海两位大哲关于此在存在问题的根本分歧做一点解读。目的旨在于说明,正是由于这一根本分歧,使得他们虽然都抵达了人的本真存在这样一重境界,但是对于“什么是本真存在”的理解却截然不同,当然这也就使得他们各开境界,对于本真存在的具体样貌有着完全迥异的描绘。
庄子与海德格尔关于此在存在问题的分歧在哪里呢?一言以蔽之,海德格尔是“向前看”的,而庄子则是“向后看”的。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
所谓“向前看”,指的是:海德格尔认为人作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者是能够对自己的存在有所领会、有所作为的,是能够通过“去存在”来界定自己“是什么”的——
“此在(人)是什么,这依赖于它怎样去是,怎样去是它自己,依赖于它将是什么。就是说,它是什么,必须从它怎样去是来理解。怎样去是,先于是什么。如果使用传统存在论的术语,就可以说。存在(existentia)先于本质(essentia)。……因而我们永远不可以把此在(人)理解为某种现成存在者族类中的一员。对现成存在者来说,它怎样存在无关紧要。更确切说,它怎样存在对它来说既不可能有关紧要要又不可能无关紧要。”(§9)
庄子当然不会对人的存在问题做这样专题化的讨论,但我们从他神龙变化、汪洋恣肆的文字中或许能捕捉到一种“向后看”的倾向: 人是和万物一样,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被决定的存在者,是一种被造物,被抛物。对此最为形象化的描述便是《大宗师》中的——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今之大冶铸全,金踊跃曰‘我且必为镆铘’,大冶必以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为大炉,以造化为大冶,恶乎往而不可哉!”

《庄子·大宗师》
而庄子所认为的“本真存在”(无待)则不仅仅是超拔自身于庸常世界之上,于沉沦状态之外,还要通过“无己”、通过“丧我”、通过“坐忘”、通过“以(已)明”,剥离开由人的主体性而产生的种种情感、思虑、言语、行为,顺应自己的天命之性、自然之性,回归到自己的最源始的被造性中去,“审乎无假(待)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德充符》)进而通达万物,达到“与造物者游”的境界。
对于庄子的这种思想倾向,看的最透彻便是荀卿,他说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正是这样一个意思——这里的“天”是“自然之别称”(《齐物论》成疏)—— 庄子是蔽于自然赋予人的现成性与被造性,不知(或者说是否定了)人所具有的可能性与未完成性。所谓“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眇乎小哉,所以属于人也!謷乎大哉,独成其天!”(《德充符》)
庄子《齐物论》中有一则非常有名的关于“天籁”的寓言——
子綦曰:“夫大块噫气,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呺。而独不闻之翏翏乎?山陵之畏隹,大木百围之窍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謞者,叱者,吸者,叫者,譹者,宎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乎?”
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敢问天籁。”
子綦曰:“夫天籁者,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
对于这段文字,冯友兰先生的解读是:“《齐物论》用一种形象化的方式,说明自然界中有各种不同的现象。归结它说:‘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耶?’在这里并不是提出这个问题寻求回答,而是要取消这个问题,认为无需回答。……‘自己’和‘自取’都表示不需要另外一个发动者。”(转引自陈鼓应《庄子今注今译》)——这其实也是自郭象以来对这篇寓言的主流看法。
我的理解恰恰与此相反:如果说“怒者其谁邪”是一个应该被取消的问题,目的只是为了说明万物在“自己”和“自取”之外“不需要另外一个发动者”,庄生又何必花这样多的笔墨来描绘地籁,强调“泠风则小和,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的道理呢?人籁、地籁、天籁三者的相似性表现在哪里呢?南郭子綦用“自己”和“自取”来为“吾丧我”做注脚,到底是增加了思维的繁复还是减少了思维的繁复呢?
“怒者其谁邪?”这一问,恐怕不是要取消这个问题,而是像佛家“以手指月示人”那样,将不可言说的、并非具体存在者的造物主引入到读者的视野之中——如果说“人籁”指的是人的气息使笙管笛箫演奏出各不相同的乐音,“地籁”指的是狂风怒号使山陵之畏隹、大木之窍穴呈现出的撼天震地的和鸣(地籁),那么在这个表面看上去“咸其自取”世界的背后呢?就没有一个怒者、没有一个造物者、没有一个“非彼无我,非我无所取”的真宰在决定着千差万别的具体存在者之所是吗?—— “天籁”,就是整个世界。天下万物,禀生不同,受形各异,看上去千差万别,但作为被造者、被决定者是毫无二致的,在“是”我们之所是的层面上是彼此齐同的。所以,当我们“以道观之”、以造物观之的时候,才会发现“物无贵贱”——都是它们自身。
而庄子所主张的“本真存在”正是要我们感知这个“是”、回到这个“是”、安于这个“是”,然后“坠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庄子·大宗师》)——通过对自身的被造性的体悟,寻找与其他被造者之间的共通性,最终“旁礴万物以为一”。
如果我们可以接受对庄子思想的这样一种解读,再回过头来看《逍遥游》中的“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似乎就容易理解了——
“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郭象注)
回归自我生命,通过适自身之性,达到顺万物之性,大约就是庄子所设想的个体与世界相通达的方案吧?
作者简介

张聪,贵阳海嘉学校学术校长,猫奴一枚。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董京尘 谢琰
责任编辑:花蕊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