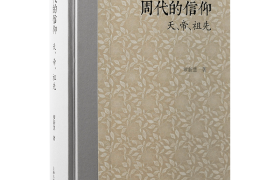内容提要:“以诗为谏”是周代谏说制度的重要形式之一,它酝酿于礼乐昌明时代的《雅》《颂》正声之中,是周代诗乐与政治言说良性互动的一种话语方式。这一讽谏机制的有效运行,并不必然催生出直陈王阙的政治讽谏诗,相反,正是西周后期礼崩乐坏,正常的谏说制度遭到破坏,诗人藉借礼乐歌唱所积淀的“谲谏”传统以寻求谏说的突破,这才有《二雅》讽谏诗的兴作。在创制机制上,讽谏诗分“公卿至于列士献诗”和“瞽献曲”两个步骤,其中瞽工不仅参与入乐歌唱之事,更促成了诗文本的最终整合、定型,如讽谏诗中的重章叠咏、“乱辞”的加入,都出自瞽工之手;在入乐机制上,讽谏诗主要在“无算乐”中歌唱,在尽欢的乐用情境中最大程度地实现“谲谏”的效果。
关键词:讽谏诗;献诗;献曲;入乐;无算乐
《二雅》中的政治讽谏诗本为公卿大夫的忧愤之作,它们通过一定的“献诗”和“献曲”渠道,在特定的典礼仪式中合乐歌唱,从而实现其政治讽谏功能。这些诗与“因礼作乐,因乐作诗”的《雅》《颂》正声不同,其内容、主题皆是感于时政,缘事而作,如孔颖达所说:“其诗皆王道衰乃作,非制礼所用。”[1]可以说,讽谏诗在创制和入乐上已形成一套新的诗乐机制。 那么,为了适应西周后期政治、礼制的变化,这一新的诗乐机制具体是如何展开的呢?是如何依托并接续了其前所积淀的诗乐传统?又注入了哪些新的礼乐精神和时代关怀?本文试论之。
一、讽谏传统与讽谏诗的兴起
谏作为一种政治言说,古已有之。《诗经·思齐》:“不闻亦式,不谏亦入。”青铜铭文《大盂鼎》:“敏朝夕入谏。”又曰:“敏谏罚讼。”《逨盘》:“(匡)谏谏克。”又曰:“谏辪(乂)四方。”《番生簋》:“用谏四方。”《作册封鬲》:“谏辥四国。”《大克鼎》:“谏辪王家。”清华简《周公之琴舞》:“咨尔多子,笃其谏劭。”又,《周礼·保氏》“掌谏王恶”,《司谏》“掌纠万民之德而劝之朋友”[2],《大戴礼记·保傅》“有进膳之旍,有诽谤之木,有敢谏之鼓,鼓夜诵诗,工诵正谏,士传民语”[3],都是有关周代谏说制度的记述。再如《国语·周语上》中召穆公劝谏厉王弭谤时所说:
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矇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4]
这说明西周王朝存在完整的谏说制度,谏说行为贯彻于整个贵族官僚系统的各个职官,且各职官结合自身职事有不同的进谏方式。类似的记载,还见于《左传·襄公十四年》:“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5]又,《国语·楚语上》载左史倚相言:“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6] 可知,周代官制设置中实即暗含着进谏制度,连虞人、旅贲、亵御等小臣也有进谏的职责,更遑论在朝的公卿大夫了。

所不同的是,一般的百工多结合其职事、就近取譬地进谏,而公卿大夫则结合自身的文化修养,以及对政事的参与和深度理解, 在进谏时更专注于言语上的功夫,谏言也因此更富含政教内涵和修辞色彩。如《国语·周语上》中祭公谋父、召穆公、芮良夫、虢文公、仲山甫对周王的进谏,就常引据历史典故、格言古训,以训诫天子,补察时弊。其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祭公谋父谏穆王征犬戎,其文曰:
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故周文公之《颂》曰:“载戢干戈,载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 [7]
祭公谋父以《周颂·时迈》所颂周武王灭商后聚敛干戈,韬藏弓矢,常求美德,保有天下,来陈说“先王耀德不观兵”之义。其后又陈说“先王之于民”“先王之德”“先王之制”“先王之训”等义,以谏穆王。与之相类似,《周语上》载芮良夫谏周厉王,亦引《周颂·思文》“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尔极”、《大雅·文王》“陈锡载周”,陈述后稷、文王能“布利”,以劝诫厉王勿“专利”。 以上二例,一方面说明周贵族接受了良好的“《诗》教”,这对其政治品格和言说方式的形成起到了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也说明作为颂美先王嘉言懿行的《雅》《颂》正声,其本身即内置了劝善谏恶的功能。故《国语·楚语上》说:“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8]又,《周礼·大司乐》提到“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即是培养国子更好地掌握《诗》语,以用于政治言说。其中的“道”,郑注:“道,读曰导。导者,言古以剀今也。”贾公彦疏:“若《诗》陈古以刺幽王、厉王之辈皆是。”[9]上文祭公谋父、芮良夫诵《诗》以谏,即属于“道”的乐语之用。再如“语”,指语说《诗》旨,阐发其中有益于时政的意义。孙诒让《周礼正义》曰:
凡宾客飨射旅酬之后,则有语,故《乡射记》云“古者于旅也语”。《文王世子》云:“凡祭与养老乞言合语之礼,皆小乐正诏之于东序。”又云“语说命乞言,皆大乐正授数”。又记养三老五更云:“既歌而语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合德音之致,礼之大者也。”注云:“语,谈说也。”《乐记》子贡论古乐云:“君子于是语。”《国语·周语》云:“晋羊舌肸聘于周,单靖公享之,语说《昊天有成命》。”皆所谓乐语也。[10]
“合语”“语说”《诗经》,是周贵族在政治典礼中十分重要的言说活动。“合语”时,自然会涉及历史、伦理、道德等方面的教诲、规谏,诚如《礼记·乐记》所言:“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孙希旦解释说:“语,谓乐终合语也。道古者,合语之时,论说父子、君臣、长幼之道,并道古昔之事也。”[11]以上文献,可以看出周人受《诗经》浸溉之深,尤其“《诗》教”十分注重“乐语”资源的运用,使得诵《诗》以谏成为周贵族政治谏说的基本方式。

除了公卿大夫,掌管《诗》乐的瞽矇乐官也肩负着讽诵《诗》来进行劝谏的任务。《周礼·瞽矇》有“讽诵诗”之职,郑司农注:“讽诵诗,主诵诗以刺君过,故《国语》曰‘瞍赋矇诵’,谓诗也。”[12]《尚书·益稷》:“工以纳言,时而飏之。”《伪孔传》:“工,乐官,掌诵诗以纳谏,当是正其义而飏道之。”[13]《国语·楚语上》:“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皆是明证。 总之,《雅》《颂》正声中蕴藏着先王的政治智慧与道德典范,乐工歌唱它们,不论是正面地劝勉,还是隐晦地陈古讽今,其劝谏的功能都是诗乐内置的、应有的效用——更何况这些诗辞中本身就含有劝诫的内容。这种劝谏的方式,在政治与礼乐昌明的时代即已酝酿形成。就以《关雎》一诗为例,三家《诗》认为周康王晏朝,故大臣作《关雎》以刺之[14]。但实际上,三家《诗》所论乃是《关雎》用作讽谏的“乐语”之用而已,贺贻孙《诗触》对此有分析:
此诗所谓刺讽者,非讽文王、大姒,乃以讽夫不能为文王、大姒者也。如《女曰鸡鸣》而《序》曰“刺不悦德也”;“大车槛槛”,《序》曰:“刺周大夫也。”后世有不能法古者,则诗人陈古诗以讽之。故程大昌曰:“所谓‘周道阙而《关雎》作’者,盖以奏乐谓之作,犹‘始作翕如’之作。”周道既阙,后妃之教衰,故奏此诗以讽刺之。[15]
这一认识是符合《关雎》的原有义旨和功能的。与之相类,《鲁诗》将《鹿鸣》认作大臣刺“仁义凌迟”之诗[16],也是误将“乐语”之用认作诗的创作,如《鹿鸣》自身所示,“人之好我,示我周行”“我有嘉宾,德音孔昭,视民不恌,君子是则是效”,诗辞中本即隐含着正面的劝勉、训教。这说明,乐工唱诵“正诗”以作劝讽,不论是在诗乐功能的原初设定上,还是在实际的礼乐活动和政治言说中,都是完全合理且有效的。
综上可以说,歌诗与讽谏言说相结合,是周代礼乐与政治良性互动的应有之义,“以诗为谏”的谏说方式孕育于“正诗”之中,并不是要晚到西周后期讽刺诗兴起时才有。正如魏源所说,“平居既以导中和,节性情”,“有时于常乐而寓箴规之义”[17]。过常宝也说:“附着在燕饮礼仪上的献诗讽谏,由礼仪传统提供了合法性,周王难以阻止或责罚这种行为。其实,周公制礼作乐的实践,就包括了利用仪式或由宗教人员对王侯进行训诫的权利,因此,献诗讽谏受到这一传统的庇护,它是周公礼乐教化思想在晚周历史背景下的新发展。”[18]不过,“以(正)诗为谏”传统的形成和效用的实现也有其条件,它需要有相对清明的政治环境,需要有和谐文雅的典礼仪式为依托,更需要有礼乐文明所塑造的君臣上下共同的政治、道德、价值认同为先导。以上条件若能满足,“以诗为谏”的传统并不必然促成讽谏诗的创制和运用。相反,恰恰是礼乐的崩坏,既有的“正诗”已不足以劝善诫恶,这才催生出直揭时弊的讽谏诗。例如《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其诗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19]《祈招》还主要是从正面加以规诫、劝勉,但到西周后期,公卿大夫愤于时政的败坏,则更多是直陈王阙了,两者的兴作背景、内容和功能效果已发生明显转变。正如郑玄《六艺论》所说:
诗者,弦歌讽谕之声也。自书契之兴,朴略尚质,面称不为谄,目谏不为谤,君臣之接如朋友然,在于恳诚而已。斯道稍衰,奸伪以生,上下相犯。及其制礼,尊君卑臣,君道刚严,臣道柔顺,于是箴谏者希,情志不通,故作诗者以诵其美而讥其过。[20]
从歌诗一端来说,王朝政治德行的败坏,歌诗从颂美转向讥过,反映了歌诗内容与劝讽方式的转换;而从谏说一端来说,谏辞与诗乐相结合,则是西周后期谏说制度破坏,正常的进谏渠道闭塞的背景下,利用周初以来所积淀的礼乐传统另辟出的一种新的言说方式。
西周后期谏说制度的破坏,在诸多文献中都有反映。《国语·周语》记载了召穆公、芮良夫、仲山父、虢文公的谏言,而厉王、宣王、幽王皆拒而不听。尤其是厉王使卫巫监谤,严禁舆论,钳制民口,致使“国人不敢言,道路以目”,此时,召穆公所述古代明王所设的理想的进谏机制,已经完全失效。正如《国语·晋语六》所说:“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21]《二雅》中不少诗篇也反映了西周后期恶劣的谏说环境,主要体现在两方面:
一、周王不用老成忠信之士,不听《诗》《书》法度之言,而任用小人,听信谗言。《雨无正》“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郑笺》:“如何乎昊天!痛而诉之也。为陈法度之言不信之也。”[22]“昊天”指周王而言。《桑柔》言“听言则对,诵言则醉”,《郑笺》:“贪恶之人,见道听之言则应答之,见诵《诗》、《书》之言则冥卧如醉。”[23]《诗》《书》等法度之言完全不被听用。《小旻》亦言“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迩言是听,维迩言是争”,《郑笺》:“哀哉!今之君臣谋事,不用古人之法,不犹大道之常,而徒听顺近言之同者,争近言之异者。”[24]古人之法,弃之不用,其结果则是谗佞之言大行其道。即使如《荡》所云“虽无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听,大命以倾”,《抑》云“於乎小子,告尔旧止。听用我谋,庶无大诲”,诗人劝、谏并用,语带警告,周王也不以为意,无动于衷。《抑》又云“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郑笺》:“‘於乎’,伤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携掣之,亲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对面语之,亲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孰,不可启觉。”[25]诗人一片拳拳至诚之心,苦口婆心,感人至极,但实际效果则是“诲尔谆谆,听我藐藐。匪用为教,覆用为虐”,《郑笺》:“我教告王,口语谆谆,然王听聆之藐藐然忽略,不用我所言为政令,反谓之有妨害于事,不受忠言。”[26]《二雅》还揭露了君子信谗、谗人巧言谮人的丑状恶行。如《巧言》“盗言孔甘”“蛇蛇硕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颜之厚矣”,痛斥了谗谮之人的巧舌如簧,厚颜无耻。《正月》“好言自口,莠言自口”,《郑笺》:“善言从女口出,恶言亦从女口出。女口一耳,善也恶也同出其中,谓其可贱。”[27]揭露了小人的出尔反尔。《巷伯》“缉缉翩翩,谋欲谮人”,刻画了谗人相谋而谮人的丑恶嘴脸。《雨无正》“哿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处休”,孔疏:“若世之所谓能言者,以巧善为言,从顺于俗,如水之转流。理正辞顺,无所悖逆。小人之所不忌,使身得居安休休然。”[28]谗人得志安处,无由惩治,而君子则不幸遭谗,深受迫害。《十月之交》“无罪无辜,谗口嚣嚣”,《郑笺》:“时人非有辜罪,其被谗口见椓谮嚣嚣然。”[29]《正月》“民之讹言,亦孔之将”,《郑笺》:“人以伪言相陷,人使王行酷暴之刑,致此灾异,故言亦甚大也。”[30]都揭露了小人讹言流行,影响之恶劣。
二、因为周王昏聩,忠信之士进说无途,因言获罪成为西周后期政治生态中十分常见的现象,《二雅》深刻反映了这一时期人们心中萦绕的政治言说的焦虑。《雨无正》“凡百君子,莫肯用讯”,《郑笺》:“众在位者,无肯用此相告语者。言不忧王之事也。”[31]在位者避谈政事,噤言以明哲保身。《板》“天之方懠,无为夸毗。威仪卒迷,善人载尸”,《郑笺》:“王方行酷虐之威怒,女无夸毗以形体顺从之,君臣之威仪尽迷乱。贤人君子则如尸矣,不复言语。时厉王虐而弭谤。”[32]贤人君子如同祭典上的尸,饮食而已,不作言语,对时局沉默以对,噤若寒蝉。《诗》中还更多表达了郁积于胸、言说无由的苦闷。《雨无正》“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维躬是瘁”,《毛传》:“哀贤人不得言,不得出是舌也。”[33]《巷伯》“慎尔言也,谓尔不信”,《郑笺》:“女诚心而后言,王将谓女不信而不受。”[34]又,《桑柔》“匪言不能,胡斯畏忌”,《郑笺》:“贤者见此事之是非,非不能分别皂白言之于王也。然不言之,何也?此畏惧犯颜得罪罚。”[35]言辄得罪,成为当时卿大夫难以摆脱的普遍的言说困境。对此,一些忠诚亢直之士坚持自己的政治操守,矢志不渝,不平则鸣,努力从噤厉的局境中挺立出来,他们除了不满于谏说渠道的闭塞,还表达了寻求言说突破的激切诉求,如《板》“犹之未远,是用大谏”,明言讽谏之意。《民劳》“王欲玉女,是用大谏”,则是一边给周王“戴高帽”,一边表达劝谏。《桑柔》“虽曰匪予,既作尔歌”,《郑笺》:“女虽觝距己言,此政非我所为。我已作女所行之歌,女当受之而改悔。”[36]既表达了讽谏之意,还毫不客气地对周王的自我逃遁予以揭露。
以上所举《二雅》讽谏诗,足以说明西周后期政治言说环境的禁锢程度,诗人执执于对这一言说困境及当时朝堂众生相的揭露,带有一种“自我指涉”的意味,愈发突显出这些讽谏诗突破困局的难能可贵。而这种突围之所以能够实现,实有赖于礼乐歌唱所积淀的传统,具体来说,仍是“以诗为谏”传统所提供的特殊的言说效应。前文论及,“以诗为谏”在礼乐繁盛时代的“正诗”唱诵中即有酝酿,其良好的讽谏效果的实现,除了歌诗自身颂美的内容可为典范之外,还有赖于整体的仪式歌唱情境的支持,即有别于一般性的言语直谏,合乐而歌的谏说方式更有细雨微风般的讽喻效果。《诗大序》曰:“主文而谲谏,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郑笺》:“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37]所谓“主文”即指合乐而歌,依托于声乐,重在婉陈,“依违而谏”,“不直言君之过失”。“谲谏”时,不仅谏者足以表明温柔敦厚的忠恕之心,被谏者也可以不失体面。这种“谲谏”方式最早也应是在“正诗”讽谏中发轫,它所具有的雅正得体又不失委婉蕴藉的言说效果,是在“乐主和同”的整体诗乐情境的熏染和影响下取得的,是歌诗乐用形态和政教功能的进一步拓展。流衍至西周后期,在言路闭塞的情况下,这种言者与闻者之间容有回旋空间的“谲谏”方式,正好可以为政治谏说提供一条突围的路径,避免了直谏所可能带来的君臣间的紧张、冲突,最大程度地实现“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的效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芮良夫作《桑柔》,据《潜夫论·遏利篇》记载:“昔周厉王好专利,芮良夫谏而不入,退赋《桑柔》之诗以讽。”[38]正是正常进谏渠道的受阻,才催生出“依违而谏”的《桑柔》之诗。从这一例子中,可以见出西周后期政治谏说所面临的普遍困境,以及卿大夫创制讽谏诗以寻求言说突破的一般情形。
于是,“谲谏”就从《诗》作为“乐语”资源、推广用于政治讽谏的一种语用方式,转变为一种能够促成讽谏诗创制、并保障其实现谏说功能的诗乐生发机制。《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四月》“君子作歌,维以告哀”,《桑柔》“虽曰匪予,既作尔歌”,都明确交待了讽谏言说与乐歌呈现的结合。这说明,虽然遭遇了西周后期政衰礼崩的困厄,但雅诗创作并未消歇,周初以来《雅》《颂》正声所蕴蓄的诗乐传统,仍发挥它的调适和新拓能力,在“谲谏”的庇护之下巧妙地将讽谏时政的内容纳入诗乐,从而开创出周代歌诗创制和歌唱的新机制。
二、从“献诗”到“献曲”:
讽谏诗的生成与歌唱
概而言之,《诗经》讽谏诗寄寓于仪式歌唱,来实现其言说目的,但公卿大夫在作诗之初,并不以合乐歌唱为第一要务, 因此《诗经》中所呈现出来的讽谏诗,作为可以“入乐”歌唱的文本,很可能已不是公卿列士“献诗”的原貌。《国语·周语上》“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韦昭注:“瞽,乐师。曲,乐曲。”[39]又《左传·襄公十四年》“瞽为诗”,孔颖达疏:“使瞽人为歌以风刺,非瞽人自为诗也”,并引《周语》韦昭注佚文曰:“公以下至上士,各献讽谏之诗,瞽陈乐曲献之于王。”[40]这说明,讽谏诗中诗人与歌者、诗歌创作与入乐歌唱已分属不同的行为主体:先是公卿列士作诗,献给瞽工乐师,再由乐师比于声律,谱成乐曲,最后在相应的典礼上被之管弦,施诸歌唱,以完成讽谏。也正是因为公卿列士与瞽工两重行为主体在讽谏诗创制、歌唱的前后参与,综合作用于诗文本,遂造成讽谏诗文本的复杂形态。
我们先来考察公卿列士所献原诗的创作情况和文本面貌。我们知道,《雅》《颂》仪式乐歌多是“因礼作乐,因乐作诗”,乐处于第一位的统摄地位,乐工甚至可以根据歌唱的需要做自主、即兴的发挥。而讽谏诗的创作则抽离仪式的范畴,不再以歌唱为首要的目的,多是感于时政之衰变而作,《史记·周本纪》曰:“王室遂衰,诗人作刺。”[41]《汉书·匈奴传》亦曰:“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42]诗之所言,多是个体生命在衰乱时局中的遭遇和感受,此时具有独立情感意志的“诗人”形象已突显出来。《雅》《颂》正声表达的主要是仪式中集体的情感意志,故诗人的身份往往不彰显,如孔颖达所言:“盖以正诗天下同心歌咏,故例不言耳。”[43] 但到变雅时代,一些诗的结尾已具明了诗人姓名,如《节南山》:“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巷伯》:“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崧高》:“吉甫作诵,其诗孔硕。”《烝民》:“吉甫作诵,穆如清风。”再据《诗序》,《民劳》《荡》为召穆公所作,《宾之初筵》《抑》为卫武公所作,《桑柔》为芮伯作,《板》《瞻卬》《召旻》为凡伯所作,等等。“诗人”独立身份的彰显,从根本上反映的是诗歌主体性的增强,以及诗、乐分途的趋势。陈世骧注意到公元前八、九世纪百年间雅诗中“诗”字的出现,认为这是诗歌“从舞蹈、歌永、诗辞之混合,渐到诗为言辞之独立观念”,“表示诗之为语言艺术之意识渐渐醒觉,它虽作来仍是歌的形式而可入乐,但已觉有超乎音乐的本身独立性”[44]。马银琴也认为:“‘诗’字的造字本义应为规正人行、使之有法度的言辞,也就是说,‘诗’字是在指代讽谏之辞的意义上产生出来的。”[45]文献中有关西周后期刺诗兴作的描述,突显的都是“诗”字本有的讽谏怨刺之义,从而将“诗”与“乐”“歌”“曲”等所指区别开来。前引《周语》“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诗”与“曲”相对而言,反映的正是讽谏诗中诗与乐的分疏。因此,《诗经》讽谏诗作为“入乐”的歌诗,实际上已是公卿列士“献诗”与瞽工“献曲”前后参与、交互作用的结果,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讽谏诗与相关平行文本的对比来加以认识。
就平行文本而言,我们固然找不到讽谏诗在“入乐”前的所谓“前文本”,不过,清华简《芮良夫毖》为芮良夫所作的训诫之辞,而《诗经·桑柔》一诗,亦为芮良夫刺厉王之作,二者的作者、主题、功能高度一致,但文本形式的差异也十分显著,比析二者之异同, 正可以见出一般性的讽谏之作演进为讽谏诗所需经过的“入乐”的基本工序。
学界对《芮良夫毖》属于《书》类文献抑或《诗》类文献,尚存争论。 笔者认为,从“毖”这一文体及《芮良夫毖》所呈现出的文本特征来看,仍当以《书》类文献为是。《尚书·酒诰》云“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王念孙《广雅疏证》以为毖“皆戒敕之意也”[46]。《酒诰》又云“汝典听朕毖”,此“毖”用作名词,指戒敕之辞。《芮良夫毖》言“芮良夫乃作毖再终”,可知其毖文与《酒诰》周公所作毖辞一样,都属于《书》类文献。而主《诗》类文献者,认为《芮良夫毖》毖文为韵文,当为诗语,甚而根据用韵情况给毖文做了分章[47],但实际上,典礼辞令用韵是不足为奇的。又“终”既可以是音乐术语,诗乐歌奏一次为一终,也可以用指一章有始有终的文本。如清华简《耆夜》中《乐乐旨酒》《乘》《赑赑》《蟋蟀》四诗皆称“作歌一终”,简文又曰“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可知“祝诵”之辞与“歌”一样都可以称作“终”,“终”并非是歌诗的特称。是故,《芮良夫毖》毖文称“再终”,并不意味着它就是《诗》类文献。而更大的证据还在于,与“入乐”的《桑柔》相比,《芮良夫毖》显示出更多非诗乐体式的特征。陈鹏宇《清华简〈芮良夫毖〉套语成分分析》一文对此有详细考察。陈文从套语理论的角度,考察得出《芮良夫毖》与《桑柔》中《诗》类套语成分所占比重分别为28.2%、45.5%,而《芮良夫毖》中的非《诗》类套语也占了24.7%,两下比照,说明《桑柔》的歌诗属性要远高于《芮良夫毖》。另外一个显著特征则是《桑柔》有歌诗常用的比兴手法,如“菀彼桑柔,其下侯旬”“四牡骙骙,旟旐有翩”“如彼溯风,亦孔之僾”“瞻彼中林,甡甡其鹿”“大风有隧,有空大谷”等,而《芮良夫毖》中没有起兴,通篇都是以直陈的方式论事说理。陈宇鹏因此认为:“《芮》没有用起兴,说明它的结构是事先构思好的,这是典型的文人作品。换句话说,《芮》是‘写’出来的,而不是‘歌’出来的。”又说:“《芮》或‘䛑’这种体裁确实像是散文化的诗——虽然持续用韵,却没有用比兴;虽然采用诗类套语,但非诗类套语也占相当大比重,如用‘譬只若’引起比喻,用‘必…以…’结构的条件复句等,都是典型的散文的特征。”最后得出结论:“《芮》可能是献诗制度下,芮良夫呈进的一篇规谏性质的作品,类似后世谏臣的表奏,这种体裁叫做‘䛑’。”[48]
笔者认同陈宇鹏对《芮良夫毖》文本性质、特征的分析,而需要补充的是,与其说《桑柔》与《芮良夫毖》的不同是芮良夫创作时就已经有清晰的文体区分, 毋宁说《桑柔》中的诗乐风貌是瞽工对芮良夫所献谏书进行“入乐”时赋予的。尤其是《桑柔》中的比兴手法和重章结构,它们是乐工为了便于组织诗章、强化乐歌属性和主题而有的惯用手法[49]。至于一般性的谏文,则更追求质直明切,发散性的起兴和繁复的叠咏反而不利于论题的集中和精准。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桑柔》并非是芮良夫所献原诗,其所进献的有可能仅是类于《芮良夫毖》或《逸周书·芮良夫解》一样的谏文,虽有韵语但尚不具备歌诗的体式,须得经过乐工做“入乐”加工,才最终成为我们所见到的《桑柔》文本。《大雅·民劳》亦可作如是观,其诗完全叠咏,且是赋的叠咏,这些乐章面貌都不应是召穆公所献原文所能有,而应是乐工蕃衍其文、反复咏唱的结果。此外,《荡》后七章均以“文王曰咨,咨汝殷商”起句,反复申说,我们也怀疑可能改编自一篇《书》类文献。
以上《芮良夫毖》与《桑柔》的比照,见出一般性谏文演进至入乐讽谏诗所可能出现的文本变异,反映了“公卿至于列士献诗”与“瞽献曲”两个环节之间错综互渗、叠加复合的情形。这其中,瞽工无疑是总持全局的关键人物,他们不仅承担谱曲和献唱之事,更促成了讽谏诗文本的最终整合、成型。
除了平行文本之间的对照,我们在讽谏诗内部也发现了乐工整合文本的痕迹,这主要体现在卒章的“乱辞”中。如《节南山》卒章:“家父作诵,以究王讻。式讹尔心,以蓄万邦。”《郑笺》:“大夫家父作此诗而为王诵也。”孔疏:“作诗刺王,而自称字者,……此家父尽忠竭诚,不惮诛罚,故自载字焉。”[50]郑、孔都认为是家父自己标明诗人身份。但实际上,诗的前九章都是第一人称“我”的视角,如“我瞻四方”“我王不宁”,但卒章则转为第三人称视角,点明作诗之人是“家父”。这一人称视角的转变,表明卒章很有可能并非原诗所有,而是乐工在歌诗结尾,跳出家父的第一人称口吻,以自身的立场从旁揭明《节南山》的作者及“以究王讻”的讽谏目的。同样,《巷伯》卒章“杨园之道,猗于亩丘。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凡百君子,敬而听之”,希望仪式在场的君子好好聆听寺人孟子之诗,其曲式结构、人称视角与前面的诗章不同,也应是乐工在原诗末尾加上的“乱辞”,总撮大义,交待原诗的作者和讽谏之义。而且,“杨园之道,猗于亩丘”两句,也是乐工惯用的兴辞,与原诗所用的赋法不同,也是出自乐工之手。又,《四月》末章“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维以告哀”,与前文“胡宁忍予”“我独何害”“我日构祸”“宁莫我有”的第一人称视角不同,也是乐工在原诗末尾加的“乱辞”。这种乐工跳脱出原诗人称和情境的“乱辞”,在《崧高》卒章“吉甫作诵,其诗孔硕。其风肆好,以赠申伯”、《烝民》卒章“吉甫作诵,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中也有见到。这些共同反映了西周后期讽谏诗所具有的“合成文本”的性质。可以说,在歌诗创作与入乐歌唱分离之后,乐工成为诗文本最终整合、定型的决定性人物。
了解了讽谏诗文本的生成过程之后,我们再来讨论它的歌唱问题, 即讽谏诗编排入乐后,是在怎样的仪式情境下付诸歌唱,又是如何籍借音乐的庇护来实现“谲谏”的效果的?
西周中期以来,仪式乐歌已粲然大备,并逐渐形成固定的“乐节”,仪式上的“正歌”也基本定型和经典化[51]。诸多未能进入“正歌”的诗乐,都被归入“无算乐”中歌唱,“无算乐”因此成为一个未限定的、开放的乐节,为这些诗乐提供“用武之地”,也因此促成新的诗乐得以继续创制。从实际的乐用效果来看,献酬正礼和“正歌”有繁复的程序、规定的次数、严格的等级、节制的饮乐,而“无算爵”时上下交亲,觥筹交错,和气融融,唯求醉饱,相应的,“无算乐”也没有次数、套数的限制,或间或合,或歌全诗,或歌某章,没有定数,是对“正歌”的有效补充和调剂。如何定生所说:“从上文‘燕’的轻松,与‘飨’紧张的强烈对比,我们才可以更充分的看出‘无算乐’的重要和意义来。……‘庶羞’和‘无算爵’,也正是个开怀的吃喝,而最顺理成章的,自然是‘无算乐’的成为这时娱乐的顶点了。”[52]在尽欢、娱宾的主题下,只要是可以酬兴助乐、应景切题的仪式乐歌,都可用于“无算乐”中。也就是说,“无算乐”本身作为礼乐歌唱繁盛的产物,其设立之初,本是用于安顿诸多未入“正歌”的仪式乐歌的,这些仪式乐歌与“无算乐”的尽欢主题也是相契合的。魏源《诗古微》:“以《仪礼》正歌言之,则不但变诗不得与,即正者亦有不得与,何者?周公时未有变风、变雅,而已有无算乐。则知凡乡乐自《樛木》、《甘棠》以下诸诗,《大雅》召康公诸诗,《周颂》成王诸诗,亦止为房中宾祭之散乐。”[53]这是礼乐繁盛时代“无算乐”的歌诗情形。
而当时过境迁,“无算乐”自由开放、不拘格套的优势,意外地为诗人所借重,为其抒发郁怀隐忧提供了合宜的空间。此时的“无算乐”脱离了最初的娱乐功能,诗人利用其自由、开放的乐用情境,将其演变为申诉个人意志的有利渠道,讽谏诗的创作和歌唱因此有了达成的可能。前代学者对此已有认识,孔颖达认为变雅“或无筭之节所用,或随事类而歌”[54]。魏源举证说:“卫献公宴孙蒯,使太师歌《巧言》之卒章;鲁宴庆封,使工为之诵《茅鸱》,其诗皆在变风、变雅,则又于燕享无算乐中而或有讽刺之事焉。”[55]尹继美也认为变诗“为燕饮无算爵之乐章,及瞽矇讽诵君侧之所用”[56]。顾颉刚分诗乐为“典礼中规定应用的”与“典礼中不规定应用的”,无算乐无疑属于“典礼中不规定应用的”诗乐,其中不妨有愁思和讽刺之作[57]。
那么,“无算乐”为讽谏诗的歌唱,提供了哪些便利呢?我们可以通过《小雅·宾之初筵》了解“无算乐”时歌唱讽谏诗的具体情境和效果。尹继美《诗管见》说:“此诗所陈皆无算爵时之事,此诗所用乃无算乐时之歌也。”[58]诗前两章赋写燕射初筵时主宾之肃敬,笾豆殽核旨酒之备,籥舞嘉乐之和奏,祖神之乐享,皆井然有序,湛乐融融。三章则着重写燕饮之事,其初尚能“温温其恭”,“威仪反反、抑抑”,而到无算爵时则“既醉”矣,主宾们变得“威仪幡幡、怭怭”,“舍其坐迁,屡舞仙仙、僛僛、傞傞”,“载号载呶”,手舞足蹈,喧闹耍疯,仪态尽失,狼籍一片了。《毛诗序》以此诗为“卫武公刺时”,是卫武公参加王朝的燕射礼,亲历了仪式前后秩序的巨大反差[59],当看到无算爵时主宾如此之醉态,卫武公愤慨地讥刺道:“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饮酒孔嘉,维其令仪。”末章的诗法从赋写转为议论:“凡此饮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监,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从谓,无俾大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语。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识,矧敢多又。”卫武公的讽谏之义于此最后揭出。秦氏《诗测》云:“玩‘既醉而出’四句,应是武公侍酒于王,见同列之人醉而失礼,故作此讽之。”[60]是也。卫武公身处仪式中,以当下情境入诗,遂有对燕射礼节、礼物的赋写;而到无算爵时,主宾的丑陋醉态引发他的激愤,遂又在“无算爵”“无算乐”时发出如上警语。总而言之,《宾之初筵》源于“无算爵”时所见,而又返于“无算乐”中歌唱,反映了西周后期讽谏诗创作与歌唱的真实情态。

至于“无算乐”中表达讽谏之意,其效果也十分突出。“无算乐”时君臣主宾上下情洽而无间,讽谏诗行乎其间,既可以在凝滞的正式进谏渠道之外获得言说的机会,同时,这种言说也可以在尽欢的气氛下缓解直谏的阻力。如《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庆封来奔,“叔孙穆子食庆封,庆封泛祀。穆子弗悦,使工为之诵《茅鸱》,亦不知”。按我们的理解,与其将庆封的“不知”理解成对《茅鸱》之诗不熟知,不如理解为庆封未能领会《茅鸱》“刺不敬”之义。之所以会如此,并非因为庆封不学无术,而是庆封在燕饮中唯求尽欢,以致于未能察觉歌唱中隐藏的讽谏义。这也从反面证明,在“无算乐”中歌唱讽谏诗可取得隐约迂回的表达效果。虽然其讽谏效果有所折扣,但讽谏诗正可利用这一难得的间隙,在西周后期恶劣的政治言说环境下取得突破,同时又能保证“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又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孙文子如戚,孙蒯入使。(卫献)公饮之酒,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大师辞,师曹请为之。初,公有嬖妾,使师曹诲之琴,师曹鞭之。公怒,鞭师曹三百。故师曹欲歌之,以怒孙子,以报公。公使歌之,遂诵之。”杜注:“恐孙蒯不解故。”竹添光鸿《左传会笺》:“歌有音节,故难骤晓,诵无音节,故易猝明。此诵之异于歌处。”[61]是师曹故意为了激怒孙蒯,改“歌”为“诵”,以不带乐节的诵读,来使《巧言》卒章的讽刺之义更简明显露。这是师曹反其道而行之,言下之意,在一般情况下讽谏诗合乐而歌,正可以取得隐晦的“谲谏”效果。
这里也有必要补充谈一下, 讽谏诗是否是被诸管弦的合乐而歌,抑或仅是略带腔调、抑扬顿挫的讽诵?文献对此的记述,似乎存在一定的模糊性,如《周礼·瞽矇》“讽诵诗,世奠系,鼓琴瑟”,郑注:“讽诵诗,谓暗读之,不依咏也。”[62]又,《左传·襄公十四年》“工诵箴谏”,《国语·周语上》“师箴,瞍赋,矇诵”,《国语·晋语六》“工诵谏于朝”,《国语·楚语上》“宴居有师工之诵”,《大戴礼记·保傅》“鼓史诵诗,工诵正谏”,都是以“诵”称谏,似有别于常规的合乐而歌。笔者认为,以上文献以“诵”称谏,多是散言之,与合乐弦歌并不矛盾,如《瞽矇》郑玄即注:“虽不歌,犹鼓琴瑟,以播其音,美之。”[63]《周语上》“矇诵”,韦昭注:“《周礼》,矇主弦歌讽诵。”[64]仍是认为“诵”与“弦歌”相通。再者,这些文献虽然称“诵”,但其所诵并不限于讽谏诗,若是一般的谏文,合有诵赋之用,正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孔疏所言:“诗辞自是箴谏,而箴谏之辞,或有非诗者,如《虞箴》之类,其文似诗而别。且谏者万端,非独诗箴而已。诗必播之于乐,余或直诵其言,与歌诵小别。”[65]若是讽谏诗,自然仍是播于乐,合乐而歌。上引《左传·襄公十四年》“使大师歌《巧言》之卒章”,就是明证,师曹改“歌”为“诵”,乃变通而用,实属反常。至于《诗经》作为“乐语”资源被“兴、道、讽、诵、言、语”,用以箴谏,实际上是《诗经》功能拓广之后的移用,且其行为主体也由瞽工转为周贵族,都不能反映讽谏诗最初“入乐”歌唱的情形。因此,我们认为,讽谏诗的乐用形态仍以《诗大序》“主文而谲谏”所述最为贴切,郑注:“主文,主与乐之宫商相应也。谲谏,咏歌依违,不直谏。”可为确解。

综上所论,在西周后期特殊的政治礼制背景下,讽谏诗逆势兴起,籍借礼乐歌唱的传统实现谏说的突破,讽谏诗创制与入乐机制的诸多新变,反映了周代礼乐所具有的自新和拓展能力,诗乐歌唱也因此得以实现新的转进和绵延。
向上滑动阅读注释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诗经》歌唱研究”(16CZW01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20]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43] [50] [54]孔颖达:《毛诗正义》,第548页,第5页,第732页,第1189页,第739页,第1174页,第1175页,第708页,第735页,第728页,第706页,第733页,第1148页,第734页,第769页,第1187页,第1192页,第13页,第696页,第706页,第54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2] [9] [12] [62] [63]贾公彦:《周礼注疏》,第352页、第355页,第575页,第616页,第616页,第617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第52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4] [6] [7] [8] [21] [39] [64]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1页、第12页,第501页,第1页、第2页,第485页,第387页,第11页,第11页,中华书局2002年版。
[5] [19] [40] [65]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第927页、第928页、第929页,第1307页、第1308页,第927页、第928页,第92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孙诒让:《周礼正义》卷四十二,,第1724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1]孙希旦:《礼记集解》卷三十八,第1014页,中华书局1989年版。
[13]孔颖达:《尚书正义》卷五,第16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14] [16]参见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第4页、第5页,第551页,中华书局1987年版。
[15] 贺贻孙:《诗触》卷一,《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咸丰二年敕书楼刻本影印,第61册,第493页、第494页,上海古籍出版1995年版。
[17] [53] [55]魏源:《诗古微》,第28页,第178页,第28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18]过常宝:《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第25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
[38]王符:《潜夫论》卷一,第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
[41]司马迁:《史记》卷四,第140页,中华书局1959年版。
[42]班固:《汉书》卷九十四上,第3744页,中华书局1962年版。
[44]陈世骧:《中国诗字之原始观念试论》,《陈世骧文存》,第22页、第12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45]马银琴:《周秦时代诗的传播史》,第222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
[46]王念孙:《广雅疏证》卷四下,第132页,中华书局2004年版。
[47]马楠:《〈芮良夫毖〉与文献相类文句分析及补释》,《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8]陈鹏宇:《清华简〈芮良夫毖〉套语成分分析》,《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2期。
[49]参李辉:《〈诗经〉重章叠调的兴起与乐歌功能新论》,《文学遗产》2017年第6期。
[51]参李辉:《周代典礼用乐“乐节”的形成——以〈诗经〉燕饮歌唱为中心》,《音乐研究》2022年5期。
[52]何定生:《诗经与乐歌的原始关系》,《定生论学集——诗经与孔学研究》,第82页,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
[56][58]尹继美:《诗管见》,《续修四库全书》据清咸丰十一年鼎吉堂木活字本影印,第74册,第20页,第7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57]顾颉刚:《论诗经所录全为乐歌》,《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十一,第340页,中华书局2011年版。
[59]孔颖达、欧阳修等皆以前二章为陈古,后三章为刺时,然诗中未有古今相对之明文,且诗从射礼写到初筵再到无算爵,节次分明,愈递进而醉态愈甚,应该就是卫武公现场亲历所见,缘事而作,藉此讽谏,并无陈古刺今之义。
[60]引自王礼卿《四家诗恉会归》,第145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61]竹添光鸿:《左传会笺》卷十五,第325页,辽海出版社2008年版。
作者简介

李辉,2003—2013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08年创立以雅昆曲社,现为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教授。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书目文献”
本文发表于《文学评论》2023年第3期,引用请以该刊为准。
特别鸣谢
敦和基金会
章黄国学
有深度的大众国学
有趣味的青春国学
有担当的时代国学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汉语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研究所
北京师范大学汉字研究与现代应用实验室
微信号:zhanghuangguoxue
文章原创|版权所有|转发请注出处
公众号主编:孟琢 董京尘 谢琰
责任编辑:刘桐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