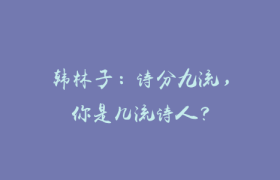儿时记忆的鲁迅是一个帅气满腔正义的男子汉,从手术台上到执笔之间的转换不仅仅是一个人职业的更新,而是他怀着对自己爱的深沉的这一片土地的交代。

那个年代多的是四肢健全身心麻木不堪的人,而鲁迅的文章又恰好是那个荒芜年代的一抹光辉。
对鲁迅的文章印象比较深刻的当然是《故乡》了,中年时期的他已经从儿时玩伴闰土的“哥儿”成长为“老爷”,依稀记得在瓜田里刺猹时身姿矫捷的闰土,雪地里陪着鲁迅一起捕鸟时单纯憨厚的闰土,许诺来年夏天时带鲁迅一起去海边拾贝时的闰土……
儿时的闰土在鲁迅的心里就是心里装着无穷无尽稀奇的事物,作为富家公子哥对于一切新事物的好奇都源自于闰土,这个家里长工的儿子。

要知道在那个社会里这种雇佣关系之间的阶级感直接拉满了,但是两个单纯天真的孩童之间是体会不到这种来自阶级之间的压迫感,他们在一起相处的日子都陪伴对方做了很多奇妙并且值得回忆的事情。
长大后,鲁迅也就变成了文章开头弃医从文的文学家,将自己对于当时社会的病态都写在了每本小说里,闰土也就成为了他儿时值得回忆的一个人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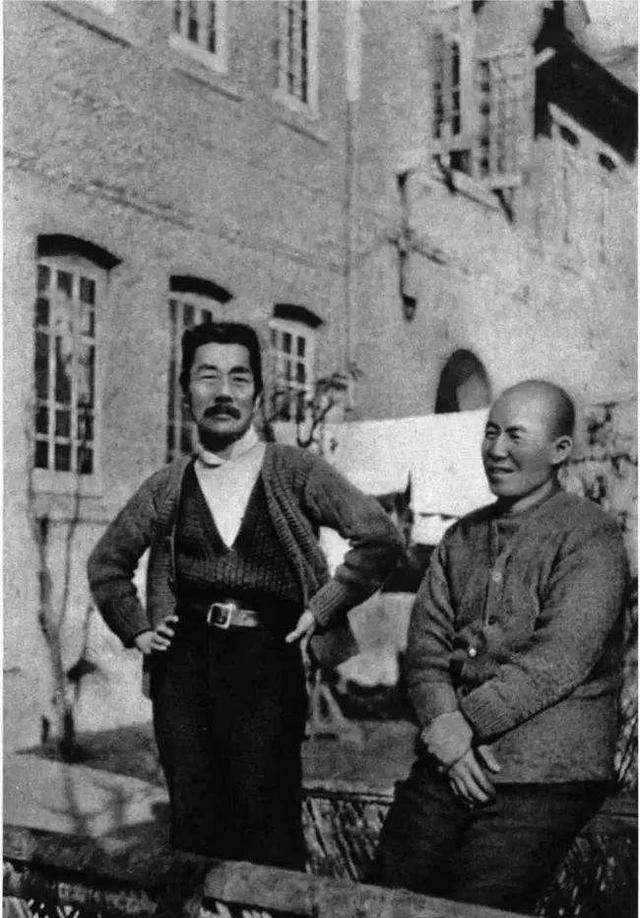
在几经颠簸之后他搬家再次遇到了这位故友,从小时候紫色的圆脸,戴着一顶小毡帽变成身材有些臃肿,面色由紫色变成了灰黄色,也多了很多皱纹。
头上依然顶着小毡帽不过是有些破旧,并且在寒冷的天气下穿着极其单薄的棉衣,在见到鲁迅的时候浑身冷地发颤,手里提着纸包和烟管。
纸包里包的是给鲁迅的青豆,手也不如以前那样灵活厚实,而是布满了冻裂的口子仿佛松树皮一般。

对于故友的外貌神态描写可以看出,年少时的好友已经不再是那个迅速灵敏会刺猹也会捕鸟喜欢拾贝的小男孩了,如今生活窘迫已为人父下面还有六个孩子要养活。
那么在《故乡》里面,鲁迅写到好几次在灰堆里掏出十多个碗碟,那么到底碗碟是闰土偷走的吗?
时隔多年见面,搬家的时候鲁迅的母亲也表示用不着的东西都可以给闰土留着用,毕竟那个年代给闰土的身上早已赋予了一种常人难以承受的压迫和劳累,生活方面的拮据也是可以想到的。

他也随着鲁迅母亲的话挑选了一些自己家里能够用得到的杂物,有两条长桌,四个椅子,祭祀用的香炉和烛台,一杆抬秤,并且也主动要了草灰,应该是运回家用来做沙地肥料的吧。
以他目前的处境来说,在鲁迅家里做长工出出进进的难免会接触到很多雇主家里的东西。

如果顺手拿走了一些无关紧要的物品来填补家用也是能够想到的,但是作为年少时期的玩伴来说,明明小时候短短几天的相处那样亲密无间而又纯真稚嫩。
岁月的流失带给这两个少年的是截然不同的处境,一面是生活拮据经济压力大的长工,另一方面是经济条件高出长工很多的雇主,谁都猜不到闰土中年时期再见鲁迅时那一瞬间相识的欣喜和紧接着一句冷冰冰的“老爷”称谓时的心情。
对于闰土是否真的拿了碗碟,其实还有更多的猜想,比如搬家时天天去鲁迅家“捡便宜”的豆腐西施杨二嫂。

在文章当中对于她的描述也是蛮有意思的,“凸颧骨,薄嘴唇,年龄在五十岁左右,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像一个细脚伶仃的圆规”。
这种人物描写一般都是反面人物的形象的,和闰土以及他的父亲的神情外貌描写截然相反,从鲁迅的笔下可以看出他对于这个记忆模糊的妇女是带着一点厌恶的。
自私自利、小市民心理并且爱占便宜的杨二嫂也完全有机会将鲁迅家的碗碟放在灰堆里面趁机拿走。

所以这十几个碗碟到底是谁拿走的已经不重要了,那么对于中年窘迫的闰土来说,从灰堆里发现的碗碟更是一种尊严上的侮辱和他儿时跟鲁迅之间情谊的践踏。
在鲁迅的眼中仿佛已经认定了这些碗碟是闰土拿地,在回家的船上回忆过去的种种,儿时跟闰土的情谊更像是他年轻时候对于故乡寄予美好的希冀。

现实生活中的闰土从伸手像他要击败神像用到的香炉和灶台的时候,鲁迅自己心中的美好希冀已经在慢慢崩塌。
从闰土让水生下跪喊鲁迅“老爷”时,希冀再次被瓦解了一部分,而最后灰堆里出现的碗碟以及“杨二嫂”这个人物的出现完全瓦解了鲁迅对于故乡所寄托的美好愿望。
他们在重重压迫下所表现出的麻木不仁和安于现状,对于当时一腔热血想要拯救家国的鲁迅来说完全就是两条平行线,是他最不愿看到的一面,却真真实实亲眼目睹了这一切。

其实反过来看,闰土和杨二嫂却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孩童时期和鲁迅要好的闰土因为祭祀事宜相识,到文章结尾拿走了香炉和灶台或许也是他在用自己的方式纪念自己和鲁迅的情谊。
作为知识分子的鲁迅认为被生活已经摧残至麻木的闰土将生活希望寄托在鬼神的身上,足以看出闰土是个重情义的人。
当时闰土在老家遭遇了大旱,颗粒无收还要养家糊口的情况下他选择卖掉了自己的家产给人当长工。

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为了自己的尊严,他没有选择向鲁迅或者他的家人伸援手,而是自己承担。
在鲁迅递来用纸包包住的礼品时,他也给了自己“家里晒干的青豆”,他没有像杨二嫂一样伸手去要,平白无故的要求别人承自己的情来获得满足自己的小恩小惠。
水生和宏儿或许在文章之外也会成为儿时的鲁迅和闰土的缩影,但是中年时期的闰土仍然在用自己力所能及的方法来维护自己的尊严。

即便是在饱读诗书经济阔绰的鲁迅眼里他已经饱受生活的折磨而麻木不堪,会将碗碟偷放在灰堆里面运走的人。
这是两个生活在同一时代背景下遭遇不同的人,站在鲁迅的立场来说闰土已经不是从前认识的那个闰土,而是会为了生活而去选择“偷”碗碟的人。
站在闰土的立场来说,本身这个碗碟偷或者没偷都是没有定论的,但是他却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来维系自己的尊严和儿时与鲁迅下地刺猹、雪地捕鸟,相约初夏拾贝的情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