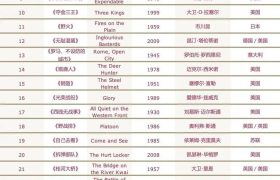还记得20年前的那个冬夜吗?我们一起看电影
“看着几位主角的特写在这么大的银幕上出现,回忆起当时点点滴滴,感觉很特别也很激动。”香港MCL cinemas的IMAX放映厅里,62岁的刘伟强坐在黑暗中,一帧帧光影映入他的瞳孔,闪过的都是二十年前的记忆。
2002年,凭借“古惑仔”系列和《风云雄霸天下》的大获成功,刘伟强组建了自己的工作室“基本映画”。为了打响新公司的名号,他到处寻找着一部合适的创业作品。恰好这时,麦兆辉拿给了他一张纸,上面写着一个故事大纲:黑社会派了一名卧底在警队,警队也派了一名卧底在黑社会。他觉得这个想法挺有意思,等到麦兆辉把剧本写完,他认定了这就是属于工作室的开山之作。只是对于片名,他还不太满意,专程去了趟泰国拜谒白龙王,终得赐名《无间道》,取佛经“无间地狱”之意。
戏拍了两个月,首场上映是在2002年12月12日的晚上9点。101分钟之后,戏院散场,陆续有人给刘伟强打来电话,他知道自己成功了。最终,《无间道》以5504万港元的成绩拿下当年的香港市场票房冠军,华纳兄弟还以175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翻拍权。次年,金像奖又将七座奖杯颁给这部电影,同时续集已经开机,年底之前第二部和第三部接连上映。

《无间道》海报。
白云苍狗,野马尘埃,时光恍然过去了匆匆二十载。这二十年中,《无间道》从未被遗忘过,无数影迷将其奉为神作,甚至它早已超越了一部电影的意义,像一记符号般刻印在历史的脉络之上,勾连着前前后后的许多时代掠影与况味。
就在一个月前,版权方寰亚电影放出了预告,全新修复的4K全景声版“无间道”系列将于12月12日在香港重映。刘伟强亲自担任了这一次修复的监制,有段时间,他每天都在后期公司看调色、听混音。对他而言,二十年前拍片好似生仔,如今则好似嫁女。去影院试片的时候,刘伟强经常一个人走来走去,到处坐坐,以确保无论哪一个位置都能获得最好的体验。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除了希望让之前看过的观众重新感受二十年前,也希望更多的未看过的年轻人看一下这部电影。”
抱团取暖的背水一战
二十年前,《无间道》是诞生在一个寒冬之中的。
自1970年代进入高速发展期,香港电影在1990年代初迎来了一个巅峰:1992年,港产影片仅在香港本地的票房就有12.76亿港元之多;1993年,影片年产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80部。但一片繁荣中,隐患也悄然埋下,导演许鞍华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的一次采访时就说过:“那个时候,人人都在乱拍电影,可是也没办法,非常无可奈何。”
在巨大的市场诱惑下,彼时的制作公司和从业者狂飙突进地踏上了一条“多快好省”的“捷径”,成功案例的既有套路和模式被大量复制,卖片花、七日鲜、飞纸仔乱花迷眼,明星轧戏更是传为一时美谈。大量质量粗糙、内容简陋的影片很快便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加上好莱坞大片的涌入、盗版影碟的泛滥、中国台湾、日、韩及东南亚市场的变化,香港电影逐渐呈现出了颓势。1996年,全年本土票房已跌至6.6亿港元,海外收入更是断崖式地下滑至4.35亿港元。与之同时,年产量下降到109部,市场占有率也随之落到了52%。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全面性的经济重创使得原本就已步履维艰的电影业更加雪上加霜。当年,香港影片的产量第一次回落到了百部以内。许多繁荣时期成长起来的头部电影人,不得不纷纷出走,试图在好莱坞等处另谋一条新的生路。而更多普通的从业者,只能守在原地,无能为力地等着开工,有的甚至要在下班以后去开出租车补贴家用。
彼时的香港电影圈,流传着一个悲情的故事:2001年底,圣诞节前的一个晚上,尖沙咀一家酒吧里,一位老导演过生日。老导演收了7个徒弟,酒过半巡时,其中5个各自端起一杯酒,跪在师傅面前哽咽着说:“我们对不起您,这一行实在没办法混了,我们要找别的生路。”
麦兆辉和庄文强也挣扎在这个局面里。1995年,他们在陈木胜的《欢乐时光》剧组相识,之后逐渐形成了一个庄文强编剧、麦兆辉导演的合作模式。2001年,两人联手创作出《愿望树》和《别恋》两部电影,结果票房一败涂地。麦兆辉陷入了无片可拍的境地,庄文强则在铜锣湾开起了酒吧。
但麦兆辉心里一直还装着一个念想。几年前,在看了杜琪峯的《暗花》《真心英雄》和吴宇森的《变脸》后,他便想写一个双雄的故事。因为父亲是一名警察,他从小生活在警察宿舍,见过父亲曾和一个黑社会打招呼,后来父亲告诉他,那个人是卧底。创作冲动与童年记忆就这样撞到了一起,他动笔写下大纲,取名《杀警》。
带着大纲,麦兆辉找过很多人,其中也包括杜琪峯和邹文怀,他们觉得故事不错,却都没有给出下文。麦兆辉不甘心放弃,他在心里发下一个誓言:如果这部戏不能开拍,自己就离开电影圈。幸运的是,刘伟强在这时出现了,他让麦兆辉赶快把剧本写出来。于是,麦兆辉拉上庄文强,花了三个月时间打磨出了完整的情节和台词。麦兆辉记得,刘伟强看完剧本立马打电话给自己,说这将是一部A级制作的电影,主角请梁朝伟和刘德华饰演。他吓了一跳,因为当时市场上的一部卧底片才创下新千年后的票房新低,自己的卧底故事如果做成A级片,一旦惨败,香港电影业将会一蹶不振。庄文强更为悲观,他觉得决定开拍已经“犯法”了,此前一年最安全的类型是喜剧、爱情小品。
刘伟强心里不是没有过类似的担忧,但之所以依然做出这一近乎赌博式的选择,是因为他埋藏着一个反叛心态:“一切香港电影出现的陋习,我们统统不做。我不想这部电影草草了事,当时美国片和韩国片就是凭着完善的创作把港产片抛离,我们要赢回观众就必须更加用心拍好这部电影。”为此,刘伟强也找了很多人,过程同样屡遭碰壁,直到敲开林建岳的门,2000万的投资才终于落袋。其时林建岳刚刚入股寰亚,心气正高,他觉得只有有人做出承担风险的投资,才能引来效法,市道才会兴旺。

刘伟强(左)与麦兆辉。图/IC
一定程度上,一片萧条之中出生的《无间道》其实恰恰得益于这股寒风。它是香港电影界在绝境里的一个希望寄托,是一众电影人抱团取暖的背水一战。正如刘伟强所说:“当时香港市道实在太差,大家都没有什么拍摄工作,当听到剧本好像不错,很多人都是一口答应。有天晚上开会,刘德华知道我们还欠点钱,他主动说暂不收片酬先开拍。”刘伟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当时我跟《无间道》的剧组工作人员都说,大家如果这次干不好,可能大家都要转行了。可能就是有了这个破釜沉舟的心态,每个工作人员都付出200%的努力,最终才能创出《无间道》这个奇迹。”
新的都市江湖
创作上,《无间道》也在许多地方留下了群策群力的痕迹。
警方卧底陈永仁在和上司黄志诚接头时,有一句台词,庄文强本来写作“当了十年的卧底”。梁朝伟在片场找到他,说这一句自己可不可以讲成“三年之后又三年”。庄文强想了想,突然发觉经此一改,陈永仁对自己命运无法掌控与挣扎的意味确实更为浓重。他同意了梁朝伟的建议,同时回过头去把剧本里的所有台词都重新琢磨了一遍。
另一场戏是黑社会大佬韩琛和泰国毒贩交易后被抓回了警局,因证据不足又被释放。初版剧本的设计里,韩琛挥手扫掉了桌上的盒饭,然后撂下狠话拂袖而去。刘伟强和麦兆辉觉得这样太过夸张,让庄文强再改一改。庄文强又写了三个方案,一个是韩琛带着一群手下在警察面前拜关公,一个是韩琛在羁留室里和黄志成下棋,还有一个则将焦点转移到了陈永仁和刘建明身上。最后一个方案立马被梁朝伟和刘德华一口回绝了,他们觉得两个人物在这里是不会说话的,否则便暴露了身份。前两个方案给到曾志伟,他一边看一边说不行,然后直接叫剧务去买60个小菜10个饭。庄文强知道他是要用初版,但刘伟强却不肯拍,僵持许久才不得已开机。当时只有梁朝伟一个人说这场戏好,但上映后这一幕却成了经典。
还有临近结尾处的那幕天台会面,原本安排的是两个卧底在电梯里决斗,动作指导林迪安甚至连动作都设计好了。还是梁朝伟,他觉得这样没意思,拉着庄文强一人一句碰出了“我以前没得选,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对不起,我是警察”那段对话。最终,陈永仁没有死在电梯里,他在电梯停靠的一瞬眉心中弹,倒在了开开合合的箱门之间,配乐响起,悲壮苍凉。
庄文强后来说,如果不是梁朝伟的坚持,这样的结尾在当时一定被人骂——香港警匪电影向来以动作场面著称,习惯了感官刺激、快意恩仇的观众不容易接受这般暗藏余韵的“温吞”落幕。不仅结尾,除了一场短促的警匪枪战,《无间道》整部电影都弱化了暴力桥段。据刘伟强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其实筹备阶段,发行公司提醒过他要多加枪战和动作戏份,但他未予理会。“最记得黄Sir堕楼那场,动作指导早已设计堕楼前在天台被盘问和殴打的动作,但我看过之后发现,这部电影应该不需要这些情节,而且直接堕楼才有戏剧性,所以我在现场临时决定不拍。”刘伟强说,开机之前两三个月他就在思考:“香港电影拍过很多卧底片,我就为自己定下规则,如果以前香港卧底电影出现过的画面,我就不拍。”
《无间道》对香港警匪电影的突破与改变,与香港社会的整体发展和变化有关。正如马家辉曾在采访中对《中国新闻周刊》所说:“为什么香港能够拍出那么精彩的《无间道》?因为香港曾是殖民地,是难民和移民的社会,所以有这种暧昧混沌的特点,黑中有白,白中有黑。”。
上海财经大学学者徐巍在《江湖伦理、宿命轮回与现代法制——40年来香港警匪片价值观念的演变》中指出:从《无间道》开始,“香港警匪片似乎失去了一种信心满满的制胜法则。在一个善恶难辨的世界里,左右人物的往往是一双双看不见的命运之手。” 这无疑是一种焦虑的外化,它源自个体在面对不确定的外部世界和未知前路时,自然而然生出的迷茫与挣扎。
与这份焦虑相伴随的,还有对自我身份的困惑与重新建构。无论是陈永仁一遍遍提醒着自己“我是警察”,还是刘建明始终萦绕心头的“我想做一个好人”,都是对于身份认同的一种寻找与确认。如果说第一部的故事里,两个人的身份在阵营分明的对峙中尚不构成重点,或者创作者并未有意着力于此,那么第三部中刘建明的精神分裂和自我幻想,已俨然成为推动叙事的关键;而在第二部中,当吴镇宇饰演的倪永孝倒在警察枪下,曾志伟饰演的韩琛崛起为新的大佬,一个历史的大变革也在完成,真实的时代躲在虚构的传奇背后,却无比明晰地呼之欲出。
或许正与这重意涵有关,刘伟强自己最喜欢的也是《无间道2》。“因为是我坚持要先拍这个故事,我和麦、庄都投放了很多心机。”他说。
创作这一部的剧本时,庄文强本来有过一段时间停滞不前。恰逢那时SARS肆虐,仍未完全从金融危机中恢复的香港正在呈现出空前的脆弱感,于是他和妻子去了泰国,一边散心一边找寻灵感。直到有一天收到张国荣离世的消息,他突然明白自己要写什么了。“在香港,张国荣象征着一种优雅,你看着他坠落,就像天使坠落。”那天晚上,他一口气完成了整个故事,用了二十多页纸,然后跟麦兆辉说:“下一个,肯定不会再比这个好了。”
“最后的荣光”
《无间道3》2003年上映的时候,刘伟强曾说自己用18个月拍完三部曲,完全是因为激情所致。“我们希望用自己的方式,和所有热爱华语电影的人共同争取华语电影的盛景和尊严。在我心中,自己要拍续集的标准就是要像《教父》那样的。”
不过,他并不否认“《无间道》最能带给香港电影的是信心,不论是对投资者、工作人员、甚至观众。《无间道》出现证明香港电影是可以回复有质素的行列,甚至能带给观众新感觉。”
在更广泛的评价里,“救市”同样被认为是“无间道”系列最首要的意义。麦兆辉便说过:”《无间道》成功后,多了投资者‘入市’观察。《无间道》不可能一手振兴电影业,但它无疑为我们的前景带来一些启示。”杜琪峯也说过,《无间道》的最大成功在于振兴了香港电影业。
然而二十年过去了,下一部《无间道》却没有再出现,香港电影终究没能挽回衰落的命运。即使是《无间道》上映的2002年,港产影片的本土票房也仅1.18亿港币,产量只有91部。而这两个数字,在之后的数年中还在持续下降。在这个意义上,《无间道》常常被称为港片“最后的荣光”,或许并不是一句虚言。
时代已经改变。就在当初香港电影届还在为《无间道》欢欣鼓舞时,一部《英雄》在内地狂揽了2.5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如果算上海外市场,这一数字则要增加到大约14亿元。尽管香港观众更多地把票根贡献给了《无间道》,但这显然只是局部的胜利,在更大的蓝海之上,巨轮已在悄然间驶离了维多利亚港,一路向北。
事实上从《无间道2》开始,刘伟强也在迈出“北上”的探索一步。不仅在演员阵容上,先后加入了胡军、陈道明、黄志忠三张内地面孔,第三部更是与内地的电影制片厂联合出品。也是那一年,香港和内地签订了CEPA合作,内地在包括文化娱乐在内的多个领域对香港服务及服务提供者开放和放宽市场准入的条件。自此,“北上”成为了香港电影人集体性的大势所趋。
其实对于香港电影而言,这并非全新的挑战。麦兆辉就曾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过:“香港这个地方是这样小,它的电影市场一直是外向型的,总会随着环境的变化改变自己。”2009年以来,他与庄文强联手,接连推出了“窃听风云”系列、《听风者》《非凡任务》《无双》等作品,一举打造出合拍片最成功的“麦庄模式”。
刘伟强也与内地公司和演职班底展开了更密集的合作,《游龙戏凤》《精武风云》《血滴子》等一系列电影由此诞生,近年来更是参与到主旋律项目中,先后执导了《建军大业》《中国机长》《中国医生》。面对《中国新闻周刊》,刘伟强说:“我经常都说自己是商业片的导演,当然希望市场大一点,拍戏也就是想多点观众看。内地市场这么大,肯定要来试试看。很多人说我来内地拍戏要讨好很多人,其实我在香港拍电影,也要讨好很多人呀。”
不过,他也承认“北上”并不是一条好走的路。“北上导演当然不好做,虽然我早期的电影都已经有来到内地取景,对内地有一点了解。但真正要拍全内地制作的电影,倒是两个世界。” 对于“北上者”,这大抵是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这不等于简单地调整航向,还时刻需要接受和适应能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不乏有人退回了,有人离开了,有人隐匿了,有人过时了。
当然,也有人选择了留守。采访中,刘伟强便谈到:“近年我看到香港很多新导演出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证明投资者肯给机会他们。而且我亦见香港观众近期非常支持香港电影,很多部作品都有不错的票房成绩。”这些“留守者”仍然坚持本土视角、本土题材,依靠本土资金和本土市场延续着纯港产片的血脉,形成了一个自循环的湖泊。只是比起从前,这个湖泊太小太小了,纵使还有倔强和骄傲,也卷不起往日的波涛。
一切就像《无间道2》中曾出现过那艘“珍宝海鲜舫”,如今已沉睡在了大海之中,时间的脚步不会因为任何眷恋与怀念而停止或倒回。也像《无间道3》中,陈道明饰演的沈澄说出的那句台词:“往往事情改变了人,人改变不了事情。”
记者:徐鹏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