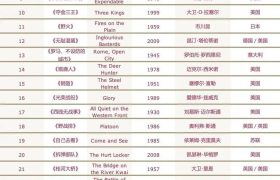未知生,焉知死
《海街日记》2015 / 是枝裕和
看完是枝裕和的《海街日记》,我突然想去拍摄火葬场上空的烟,那些灵魂。葬礼与祭仪、日常对亡灵的敬拜轻盈地贯穿整部电影,看了那么多死亡,你并不觉得压抑和悲伤,因为那些人“死得其所”,一如那些活着的人“活得其所”,你觉得静静地记录下这一切是值得的。
生和死,原来是可以这样的,电影,原来可以这样的,不需要勾心斗角,不需要戏剧化大逆转——本来那些角色设定,如果落在一个中国导演手上,估计得成一出闹剧:离家出走十五年的父亲突然死亡,留下一个异母妹妹,三姐妹如何接纳她;因为父亲出轨也离家的母亲回来参加外祖母的祭日,与身代母职的大姐姐多年的怨怼一触即发;大姐姐其实也爱上有妇之夫,饰演了当年拆散自己父母的女人相似的角色,最后又怎样了结?

无论是导演,还是角色,都以日本式的克制解决了这些有点狗血的纠缠。或者说这种克制原本就存在于日本的自然、电影中镰仓的山水草木中,人物只需要静听四时变化——就像姐妹们居住的老宅一角的梅树,它结子落子,被外祖母、四姐妹分别采摘酿成不同口味的梅酒,不同的口味呼应着姐妹们不同的性格,但在某些时候,她们又会交换手中那一杯,学习尝尝别人的人生滋味。
任运、顺变,这本来是中国传统最深厚的面对命运的态度,惜乎陶渊明“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之后,能领会如此境界的国人越来越少,最后还是被日本吸收发扬到无微不至。当文化日益走向极端世俗化,岌岌乎形而下的功名利禄或口腹床第之乐,无一刻消停去沉思死亡。不是说日本就没有这种极其世俗的计量,只是日本人不止于此,镰仓古宅里的四姐妹并非什么哲学家也不是禅宗大师,只是在一个人性温和的社会中,在川端康成所说的一种日本的美的包围中,自然而然地学会了这种无喜无惧。镰仓细海不停息的浪,樱花隧道混和与风、光、尘的那些花瓣,都在传递着这样的讯息。
未知生,焉知死,孔夫子这句话本来是提醒人们珍重当下而齐生死,不要只问鬼神。但在中国数千年的实用主义民间“生存智慧”中,渐渐演变成回避死亡、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犬儒,死亡在我们生活中只意味着恐惧和麻烦,死永远是他人的死,我们尚未学会把死亡归纳入自己的人生中,因此每一次面对死亡我们都惊慌失措,过后又浑浑噩噩活着,只要死的不是自己或者至亲,死亡变得毫无意义。
实际上,善终,无论在日本还是西方都已经成为一门由专业人士介入的学问,即使华人传统积习甚重的中国香港这些年都开始重视“善终”问题,我记得有一天在地铁站看到巨幅海报,分别印着新生儿和待死老人的照片,旁白:“来的时候万千宠爱,去的时候孑然一身。”——如此警句,让我和许多匆匆赶路的乘客都稍一驻足反思死亡。
饶有意味的是,《海街日记》里的大姐姐香田幸任职护士,被调到新成立的“善终病房”服务时,开始她并不是很乐意的,正如她那做儿科医生的情人所说:天天看着人死去,心情怎么会好,还不如我天天帮助新生命来到世间,更能体会积极的可能性。但当她一家的老朋友二宫姨突然身患绝症也入住善终病房之后,香田幸渐渐知道自己也可以成为她的一个同事那样:做陪伴老人最后一程的天使,度亡的重要性,不亚于接生。
理解死亡的同时,是枝裕和依旧不遗余力地赞美生命、赞美青春,异母妹妹浅野铃身上被寄托的,就是这种礼赞的光辉——有一个长镜头,铃坐在男同学的自行车后座穿越长长的樱花隧道,镜头不息地徘徊在她身上脸上的光影流转中,仿佛贪婪地吸取着青春的力量,又像在她的美姿容上向那些逝去的父母祖先招魂一样。其时我竟心生感慨:死在此刻也不错。生与死如此和解。
顺变,也顺其不变,被导演用近乎缱绻的慈爱镜头记录下来的这镰仓小镇和老屋、外祖母的浴衣、简单的烟花……它们都是旧的不变的,再放一千年也不必创新改造,相对于在发展至上主义的国度里那些光怪陆离的新事物,它们更加强大,因为它们令人安心。安心、安心、安心,重要的事说三遍。著有《住宅巡礼》《住宅读本》《意中的建筑》等作品的日本建筑家中村好文,曾提出“居心地”这个概念——“住宅不但是为肉体的居住而设,更是心灵的居所,即使是柴米油盐一锅一榻的陋室,也能拥有大教堂那样修心养性的能量”。你会发现在这部电影里,处处是居心地。
唯其如此,拥有居心之地的姐妹们,最终才能理解死者——缺席者的意义,理解了她们死去的父亲,他虽然在整部电影中未曾露面,也从二姐、三姐过于年幼的记忆中只有淡淡的印记,却存在于山顶远眺的海面波光或者一碗承载故乡之味的白饭鱼盖饭里。在女儿们体谅他的一刻,他也终于获得安魂了。这样的一部电影,固然还是治愈系,但它治愈的,已经不只是急于寻找治疗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