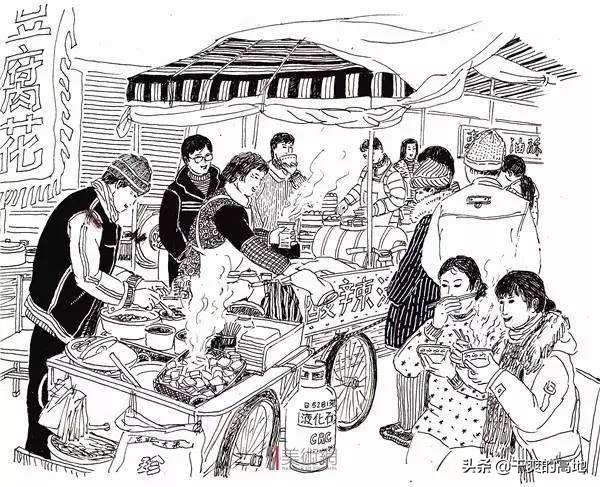
不散的老味道
文|姚君英
家的味道,是灰色的土豆饼的味道。小时候,深秋时节,我们最喜欢去地里捡冻土豆。那被风霜打过的三扁四不圆的软柿子一样发黑的土豆,小半天就能捡上一土篮,挎回家当猪饲料。为了奖赏我们,母亲会从中挑出一些来洗净,去皮剁碎,再加上花椒、大料、咸盐、味精、葱花等调料,烙土豆饼子给我们吃。记忆中,那烙熟的土豆饼子灰得透明发亮,香气扑鼻,特别筋道好吃,那种独特的口感和味道,竟使我误以为土豆饼子的原材料必须是从烂土豆里挑出来的,略带着些腐酵味儿的冻土豆不可。因为后来,再也没吃到过那么好吃的土豆饼子。
家的味道,是煎饼的味道。父母亲是地道的山东人,特别钟情煎饼。他们在一次回老家探亲时,千里迢迢地背回了一个煎饼鏊子和一盘小石磨。他们在院子里支起一个塑料棚,用红砖黄泥盘了一个炉灶,垒起半截火墙,再接上用铁皮做的烟囱。鏊子就常年嵌在炉灶上。
母亲做煎饼是极讲究的,她提前把黄豆泡好,用小石磨碾成浆液,盛在一个大铝盆里,掺上玉米面,搅拌成稀米糊状。母亲摊煎饼的工具基本都是自己动手做的,一个铁皮罐头的油盒,一支寸把宽的板刷,一个安了一尺来长把柄的长方形推板,一个像斧头一样带点弧度的刮板,两块用白纱布折叠起来缝制的软擦布,一只套在右手上的棉布手闷子,一把长柄饭勺,还有一把安了木柄的铜铲子。摊煎饼所用的柴火也有说道,不可以直接用柈子,也不可以用煤块。母亲说,用柈子或者是煤块儿,火太硬,煎饼会烙糊。母亲把晒干的稻草或者麦秆扎成一小束一小束的,码成一垛。摊煎饼的时候,先用木柴引火,把鏊子烧热,然后开始往灶堂里续麦秆或者稻草。通常我们兄弟姊妹会有一个人蹲守在灶门前,遵从母亲的吩咐烧火。母亲则扎上蓝围裙,坐在一侧的木椅上,先用擦布仔细擦一遍鏊子,然后用长把勺子从盆里舀一勺糊糊,举得高高的,慢慢倾斜着呈一条小细流倒在鏊子的中间,再上下晃动着空一下勺子。将勺子放回盆子里,拿起推板延顺时针方向推拉。从中间推起,随着冒着白气儿的“嗞啦”声,一圈儿一圈儿地向外延展,那一勺糊糊恰好能把鏊子覆满。放下推板,母亲戴上棉手闷子。拿起刮板一遍一遍地刮,刮得四下里都薄厚均匀,任何细小的漏洞都被刮板修补得天衣无缝。放下刮板和手套,母亲拿起那把小铜铲沿着鏊子的外沿儿把煎饼的边儿撬起一圈,放下铲子,分别用两只手的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煎饼的边儿,轻轻一揭一旋,那金灿灿的滚圆的煎饼就顺势被母亲不偏不倚地转移到盖帘上去了。煎饼的大小正好与圆圆的盖帘重合。鏊子上干干净净的,不粘得半点米面的痕迹。

母亲很会掌握火候,她烙的煎饼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薄薄的软软的,卷上大葱大酱或者土豆丝之类的炒菜,吃起来格外香软筋道,口齿生津。还有一种是薄薄的脆脆的,不可以卷东西,只能像饼干一样掰着吃,煎饼略带点甜丝丝的香味儿,留在唇齿之间,令人回味无穷。母亲说煎饼的软硬,全凭火候来控制。母亲每次烙完一大摞软煎饼后,都会再烙上几张脆煎饼,给我们当零食。
每次摊完煎饼,母亲都会用擦布擦一遍鏊子,然后用板刷蘸油刷一遍,再用另一块儿擦布擦一遍,最后罩上一块儿塑料布,压上一顶木锅盖。母亲说抹油是为了“养”鏊子,使鏊子更加平滑细腻。
家的味道,是水煎包的味道。母亲做的水煎包,在我的记忆中,这么多年来,是没有人可以超越的。母亲做水煎包的食材很简单,豆腐、粉条、白菜等拌馅,且从不放肉(那个年代平时也吃不到肉)。母亲把白白软软的豆腐焯一下,切成丁,粉条也要焯一下切碎,再细细地剁一遍,馅子拌得很清淡——回想起来,我常常觉得母亲做水煎包的秘诀就在蒸煎的过程。母亲有一个专门做水煎包的平底耳锅,母亲先用抹了豆油的擦布将平底锅擦一遍,待锅烧热时,用刷帚掸一点水,在“嗞啦啦”的白气中,母亲将包好的圆圆的包子疏密均匀地摆放在里面,盖上锅盖蒸几分钟。这时候的炉火是由母亲自己掌控的,她信不过我们任何人。中间,她会揭开锅盖再掸一遍水,出锅时,母亲用铲刀四下轻轻一铲,再沿着中间的缝隙处划两下,锅里的水煎包就分成了四份儿。母亲右手握铲子托起其中的一份儿,左手罩着,随着一声“闪开,别烫着”的嘱咐,迅速地将水煎包底儿朝上倒扣在饭桌上一个白瓷茶盘里,从上面看就是一整张金灿灿的饼。于是,右手食指已不知不觉抠在嘴角的我们,一下子从炉灶前又围到了圆桌边,探着小脑瓜盯盯地看着,像是蹲伏在起跑线上等待枪响发令,只待母亲一声“吃吧”,就开始狼吞虎咽。
母亲总会笑着说:“你们这帮小饿死鬼托生的,等会儿凉一凉再吃。”母亲不慌不忙地将锅里的水煎包都起完,再蒸上一锅,然后小心地将那连接在水煎包之间的,薄如蚕翼的,黄灿灿的脆嘎巴掰下来分给我们吃,再把水煎包分到每个人的碗里。水煎包上软下酥,外焦里嫩,每次我们都是先把水煎包上半部分几口吃掉,再从四周向中间吃饼一样细细咀嚼底部。吃完了,再眼巴巴地盼着下一锅出锅。

家的味道,是冬日里门后那散发着淡淡蔬菜清香的碎咸菜的味道。每当秋收后,母亲都会吩咐我们用大洗衣盆洗刷萝卜、芹菜、大头菜、豆角、香菜等各种蔬菜,然后该擦条儿的擦条儿,该切段儿的切段儿,该剁丁儿的剁丁儿。母亲把家里最大的那口缸里外刷净,铺一层菜,撒一层盐。五颜六色的碎咸菜,吃到第二年开春儿,脆生生的口感和鲜灵灵的色彩也不曾削弱半分。那可是我们兄妹冬日里就着带冰碴的窝窝头最下饭的美食呀!因为那些年母亲身体不好,冬天若不回老家,就得在医院里过冬。父亲工作又在外地,无法照顾我们。因此母亲每年回老家之前,都会为我们一家人储备上一冬的咸菜。
家的味道,是那黄褐色的油炒面的味道。油炒面,我们平时是吃不到的,那是只有在外地上学的孩子才有的待遇。记得上师范时,每次回家,吃过晚饭后,母亲就会用一口小铁锅,用炉子里的余火为我们炒面。她先把花生和芝麻炒好,用擀面杖在面板上擀碎,再用荤油把面炒好,将擀碎的花生芝麻拌进去,等晾凉了,再拌上几勺砂糖。我第一次吃到母亲做的炒面,就是在学校的宿舍里。舀一勺放在搪瓷缸子里,用开水沏成糊状。倒开水时要先小水流少倒一点,待将炒面湿透并搅拌均匀,再用滚烫的开水一沏。混合着芝麻花生的麦香味儿,便霸道地弥散在寝室的所有角落,室友们会都端着搪瓷缸子齐刷刷伸向我的面前:“嗨,咱妈做的炒面太馋人,给咱也分一勺妈妈的味道……”从此,同宿舍的人就管我从家带的炒面叫“妈妈的味道”。

家的味道,是逢年过节父亲做的熏兔的味道。那时家里鸡鸭鹅狗牛羊马兔都养。快过年时,父亲就会宰几只兔子,扒下的兔皮让母亲给我们做棉手套。父亲在炉子上架一口五印大铁锅,锅里放上拌了红糖的锯末子,把从竹框上掰下来的几根竹篾交叉着横担在上面,再把那剥得赤条条的,眼睛显得格外鼓大的,涂了油的兔子摆放在上面,盖上木锅盖,然后生火。不一会儿锅盖的四下里就翻滚出带着焦糊味道的浓烟来,父亲掀开锅盖把兔子拿开,用铲子将闪着火星子的锯末子翻炒一下,再把兔子翻个个儿放里,盖上盖子,但这时的火候就不可以那么大了。父亲蹲在灶前,用他那痛感神经极差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捏着铸铁炉门的门鼻子,一会儿打开,一会儿又关上。个把小时,那冒出的白烟里就飘出烤肉的香气了。这时父亲便不再加柴火了。再焖上一两个小时,打开锅盖,熏兔的香气就飘满了整个屋子。拿出兔子,那竹篾已变成了黑黑的竹炭了,锅底也糊着一层凸凹不平的硬硬的黑焦炭。父亲用他那不怕烫的手,从兔子的胸部撕扯下几块暗褐色的兔子肉递给我们,我们就蘸着父亲事先擀碎的盐面儿,和味精、花椒面等佐料拌好的一碟椒盐美美地吃起来。那种味道,啥时候想起来都会垂涎。
家的味道,是父亲做的青豆花生的味道。父母亲每次从山东老家回来,都会背回来小半袋青豆——那是一种比黄豆粒稍大,有些扁椭的青绿色的豆子。父亲会将煮熟的花生米和青豆,加少许萝卜丁,还有打过水焯的芹菜混合上一大盆,再煮上一锅加了各种调料的盐水,晾凉后倒在里面。每次吃饭时都盛上一碗,即便没有其他像样的饭菜,但那色彩极其舒服养眼的花生青豆萝卜丁清香爽口,也让我们吃得极其享受。
家的味道,是春节前母亲蒸的炸的各种小动物造型的面食的味道,是端午节父亲做的叉烧卤蛋的味道,是夏日里母亲酿制的黄酒的味道,是母亲用锅底灰标记后腌制的油黄咸鹅蛋的味道,是寒冷的冬日早晨父亲升好了炉子将我们冰坨子一样硬硬的棉裤一一翻过来拎着烘烤时的味道,是母亲栽种的满院子花花草草的错综纷杂的甜蜜味道,是母亲的手挤过老黄牛那鼓胀的乳房时泉水一样叮咚作响,流淌进铁皮桶里的洁白的乳香味道,是冬天厨房里鸡架下撒了炉灰也清晰可辨的热烘烘的鸡粪的味道……
原以为这些味道,会因那座小村庄向城镇迁并后,随着那消失的缕缕炊烟而渐渐弥散无痕,也会因2007年冬季的某一天和2015年底的某一天,伴着母亲和父亲的溘然长逝而再无迹可循。可是,谁能料到,那些味道竟都被多情的记忆,点滴不漏地搜集到潘多拉的魔盒里,魔盒的开关被一根细微的神经牵扯着。不经意地一次碰触,魔盒便倾倒得一地珍宝,所有的味道都像久困的魔障一样四散开来,无处不在,无孔不入,浓雾一样将我囚困在其中,无处可逃的我,被那些熟悉的味道一遍遍蹂躏。
原来,我与家的味道,只隔了这一层薄薄的透明的记忆呀!可泪流满面的我,却无比悲哀而清晰地意识到:我再也无法沿着这样熟悉的味道找到回家的路了!因为今生与父母亲走散了的我,已成了永远无家可归的浪子了……

姚君英,笔名舟儿,牙克石市作协常务副主席。著有散文集《放一叶轻舟》,诗集《午夜,做你窗外那帘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