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编按:诗人任评说,吾同树的诗写得极有水准,非一般诗人所能及,“我想,他会成为海子第二,一点也不为过。”吾同树已经走了13年,他的死曾经轰动了整个东莞诗歌圈。这位曾经被预言成为海子第二的诗人,是如何让房贷成为压住自己最后一根稻草的?让我们重新走近和回忆这位极具有天赋的年青诗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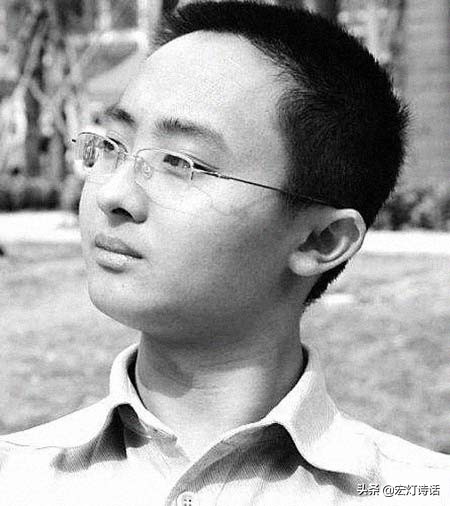
吾同树(1979年12月—2008年8月1日),本名曾桓开,生于广东梅县石坑镇长布村,中国当代诗人。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在《诗刊》《星星诗刊》《歌曲》《散文诗》《音乐周报》《南方都市报》《珠江晚报》等四十余家报刊发表诗文近400余件,获过十余项文学奖励。2005年7月,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职东莞一家房地产公司。2008年初,创业失败;7月28日,入职东莞一家报社;8月1日,在东莞家中自缢身亡,终年29岁。
远去的诗人,永恒的歌 ——追忆诗人吾同树
山海游客
吾同树(1979—2008),原名曾桓开,生于广东梅县,客家人。1995年开始诗歌创作。2001年入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先后在《诗刊》《星星》《北京文学》《诗选刊》《歌曲》《扬子江》《中国校园文学》等刊物上发表诗文400多篇(首)。曾获《人民文学》《天涯》《飞天》《诗潮》等刊征文奖十余次。入选《2003年大学生最佳诗歌》《敦煌2004年卷》等十余个选本。被《诗刊》评为“2007年度中国20位最具活力青年诗人”。身后出版有《吾同树》诗选……
说起来,我与诗人曾经有一段缘。这段缘始于2001年9月。当时诗人刚入暨南大学珠海学院学习,我刚好在此任教现代文学课,且兼任诗人所在班的班主任,课内课外与诗人的联系就较其他人多一些。我与诗人的直接交往时间虽然不长,但或许因为诗的缘故,我们的友谊却没有中辍,从那时起一直延续到他的遽然辞世止。
追溯起来,我与诗人的交往,大约算得上始于师生,终于朋友;起于职业,讫于友谊。2008年8月1日,诗人的突然离去,让我深深体会了生命的脆弱而造成的难以言说的痛楚,禁不住为一个已经显示卓越才华的年轻诗人的夭折而扼腕。
尽管我对诗歌创作可能并不在行,可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却经常被诗人洋溢于诗行的卓越才华所打动,并因此成为诗人作品的忠实读者。也可以说,正是诗人的诗作征服了我。
一
我与诗人的第一面是在2001年9月,开学后正式上课的第一个早晨。当时我挟着讲义走在通往教室的路上,桓开与我路遇,略显拘谨地主动与我打招呼,我方知是自己班里的学生。诗人给我的第一印象是,身体瘦小但不乏灵巧,面颊泛着南国骄阳曝晒后特有的黝黑,双眸透出精神,也许偶尔还闪烁着些许忧郁,脸上挂着大多广东孩子带有的真诚朴实神态。
同行的过程中随口问他,平常都读过哪些刊物,桓开不假思索地列举了包括《人民文学》《诗刊》在内的几种文学杂志。问其印象,他似乎有些冲动地脱口而出:“老师,许多作品还不如我写得好!”我内心咯噔一下。询其创作,他似乎又显得有些冲动:“几乎每天写一首诗”。我心里再次咯噔一下,不禁暗暗对眼前这个年青人所表现出的咄咄锐气感到称奇。
也许是感到自己说得有些冲动,或者担心我的误解,大约两天后,桓开拿着一本厚厚的笔记本来到我的寓所,请我过目他过往所写的文字。从这时开始,桓开的诗歌创作开始进入我的视野,给我带来一阵阵赏心悦目的审美冲击。老实说,桓开的文字具有很强的艺术魅力,我相信,稍微具备一点文学鉴赏力的人,阅读了桓开的文字,立刻就会感受到什么叫文学才华。几乎就在阅读这个笔记本的同时,桓开的文学笔触所展现的惊人才华就俘获了我。我毫不怀疑地认为,我遇到了一个诗歌天才。
实际上,因为个人专业的背景,在我眼中滑过的诗人诗作不在少数,而且因为职业的行为,我也免不了要通过评价诗人诗作——尤其是现当代的诗人诗作——而讨生活。但除了少数诗人的作品为诗歌留下了光荣的印记,大多数诗人诗作如过眼云烟,甚至带给我们的是对诗歌审美意识的磨损。质言之,诗人众多,但诗才可能并不多,而桓开无疑属于具有突出诗歌禀赋的人之一。从阅读桓开诗作的那一刻起,我有一种从沉沦于职业的麻木的诗歌经验中被唤醒的兴奋感和解放感。
如果一定要追问桓开诗歌的才华禀赋,我认为,在桓开诗作表面漫不经心的诗行里有一种对诗歌形式感的直觉把握,他的诗歌有一种整体的旋律感,渗透文字的艺术世界具有很高的想象成分,他的诗歌对文字的驾驭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训练而获得,毋宁说每一次创作都是一次激情与灵感的瞬间释放,他对文字非常敏感,而且对之具有很强的捕捉能力。在我看来,桓开的创作总是走在想象与现实的结合部,文字与精神的交汇处。
遭遇桓开的诗歌对我是一种全新的艺术体验,我有一种既被震撼又深受鼓舞的兴奋。不用说,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了这个年轻学子的诗作具有的不同凡响的艺术价值和蕴藏其中的超时间能量。说实话,我为这个发现而倍感振奋。于是从其中精心挑选了十五首诗歌,输入自己的电脑,作为永久的珍藏。
桓开的这些精美的诗歌陪伴了我很长时间,直到有一天——我已经来到宁波,电脑意外发生故障,这些诗歌令人惆怅地在我的珍藏中消失了,直到今天仍然无法弥补。在我的记忆中,诗人身后出版的《吾同树》诗选中,只有《第一笔稿费》是在我第一次阅读的桓开的诗歌篇目中,但按诗选后的时间标注,该诗写于2004年11月23日,我想这很可能是该诗经修改发表于某刊物的时间,而非首创的时间。
与诗人曾桓开的相逢,品读他的那些美好的诗歌,后来成为我对珠海学院的最美好记忆之一。甚至因此,我感到了自己短暂的南国之行具有了别一番意义。
二
2002年5月,我移居宁波,和桓开的联系也从直接转为间接。但因为诗歌的关系——作者和读者的关系,我们之间结下的友谊没有因为时空的转移而终止。闲暇之时,我会有意无意地留心一下关于桓开的零星消息。其实这样做并不是缘于教师这个职业,尽管身为教师,但我似乎一直缺乏职业的神圣感,但我确实发现,当一个人自己不再年轻时,目睹一个年轻人如雨后春禾般地拔节成长,无论如何都是一桩令人兴奋的事。后来,时任宁波大学校长严陆光院士在一次会议上提到,他曾经就高等教育向他的父亲——著名科学家严济慈——请益,这位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老教育家语重心长地说:高等学校教师的职责,一是传授知识,二是发现人才。想到与桓开的交往,我油然有感。其实我对桓开诗歌创作的成长并无多少贡献,但作为一个教师和读者,当我发现并确认他的诗歌才华时,我想我对得起自己的职责了。当然,如果这种发现和确认对他的诗歌创作有所激励那就再好不过了。
求学时的桓开,精力过人,文学交往非常频繁,创作也异常勤奋,这是让人称羡的——年轻就是好啊!如果说诗歌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文学体裁,那可能不会有太大问题,因为诗歌在本质上是抒情的,当然青春与诗歌同在。
离开广东以后,桓开每年初都会把上一年的诗歌新作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发给我浏览,每一次我都非常愉快地分享了他的新作。这种愉悦是难以言表的,它不仅给我带来耳目一新的感受,而且让我直接感受到了一个年轻人成长的旺盛脉搏。
大约是在2004年春节前夕,诗人将他前一年创作的诗歌的电子文本发给我。阅后,我对诗人在课余时间仍然保持勤奋的创作状态,感到由衷地赞佩。我去邮局给诗人汇去两百元钱,在留言处写道:“谨表示一个读者对作者的真诚敬意!”我说的是真心话。
历时地梳理桓开以后几年的诗歌,创作风格与题材的变化痕迹是明显的。清纯精致的个人化抒情似乎少了一些,乐观轻快的格调也降低了不少,激情中明显蕴含着愤世的尖锐倾向,但文字更加洒脱大气。个别篇章还使人明显感到了某种深刻的虚无主义情调——好像是《哲学课》,——原文我手头已找不到了,但那单纯、谐谑而深蕴惘然的意象却永远镌刻在我脑海里了。尤其是他辞世前两年的诗歌创作更是花费了很大的力气将视野投注到了家乡的生命背景中,营构了一种诗歌与生命同在的大境界,他似乎有意识地要将自己的生命托付给自己创造的宏大作品。虽然他还非常年轻,但似乎已经在进行探寻精神的回故乡之路。
毕业之后,桓开的职场生涯似乎比较顺利,这时了解桓开的信息已经非常方便,因为他在新浪网开了一个博客。他的博客更新的频率非常快,笔头依然洒脱生动,下笔成文。我是他博客的常客,也经常从他的博文中有所收获,并且我还把桓开的博客推荐给我的研究生们浏览。此时桓开的工作状态和精神面貌,都以其生机勃勃使人深受感染,我也希望我的研究生们从中汲取一个同龄人应有的生活热情。
从桓开身上,我突然产生一个联想,感到不论是外形还是气质,他都与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粤籍作家丘东平非常相似,激情如火,疾恶如仇,诚实清高而富有正义感,但有时也不免偏激。说起来,两人的故乡也相去不远,一个在梅州,一个在海丰。两人都才华过人,对文学都很虔诚,入世的意志也非常强烈,并且都在强烈的入世行动受挫中而自决。从个人行为上讲,都表现得非常刚烈。
丘东平,生于1910年,殁于1941年;曾桓开,生于1979年,殁于2008年。一个31岁,一个29岁……
三
凡是桓开的朋友,都会为诗人的遽然逝去而感伤。时至今日,关于“诗人之死”的话题其实已与诗人无关,因为他已经走在了天国的路上。而事实上我们每个人也将随着时日的推移,无可避免地陆续踏上死亡之旅。然而因为血缘亲情的原因,抑或因为诗歌的原因,诗人之死竟然成为萦绕生者心头挥之不去的伤痛。
2008年8月3日,在东莞参加完桓开的追悼会后,关于桓开生前的点点滴滴不断盘桓在我的脑海,很想写一点什么,但一时又不知说什么好。于是这个想法也就随着俗人俗世生活的繁忙而渐渐淡出脑海。09年珠海的容浩兄告知,将于5月16日在珠海学院举行一个桓开诗歌的朗诵与研讨会,诚邀我为桓开写点文字。于师于友,我都无法推托。这个活动对诗人和珠海学院的学生们都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诗人的主观死亡不能遮掩诗人伟大诗歌的现世价值。然而真要写点什么,我却深感踌躇,因为我知道我无法写出有力量的文字。容浩兄回复,只要情真即可。
既然如此,我不得不又一次发掘着久已微漠的记忆,蓦然间竟然发现,诗人生前实际上不止一次与死亡邂逅,据桓开自己讲,早在上大学之前他就曾经有过一次严重的轻生经历,原因不得其详,只知后来是在他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才帮他度过了那次生命危机。但后来的一次活动却使我在某种意义上亲自领略了发生于桓开身上的这一生命症候——
好像是2002年3月26日,——那是诗人海子的忌日,桓开吃力地捧着一箱矿泉水,邀请我和王香平教授、珠海的两位音乐人以及班里的十余位同学,到珠海海滨公园为海子举行了一个纯属民间自发的追思活动。我内心很是愕然,老实说还夹杂了一些世俗的念头。1989年3月26日海子在山海关卧轨自杀,这我是知道的。从那以后众多的关于“诗人之死”的文章,我也是耳闻的。但海子之死是否成就了他诗歌的伟大,我却是持有保留意见的——直到今天依然如此。但桓开对诗歌的虔诚却让我无法拒绝他的恳求。
但现在猜想,吾同树在发起这次纪念海子的行为中,除了诗的因素,是否也包含着“诗人之死”的因素呢?我想也是应该有的。
记得那一天阴雨连绵,冷风阵阵,空气阴冷,即使在珠海也算得上是一年少见的坏天气。在空旷凄凉的海滨公园的一个亭子里,大家围坐一圈,气氛稍显压抑肃穆。桓开说了一个开场白,然后我顺着时髦的“诗人之死”的观点作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即兴发言,凭着语言的惯性,我自己也好像被自己的言说感动了。然后众人都很投入地参与了这个话题的讨论。我相信这个事件对当事人或多或少都会有一些触动。实际上文化活动的人为性是显而易见的,价值认同对人的影响却由此产生。文化的本质大概就体现在精神对生命肉体的能动塑造过程中。
2007年10月4日,云南诗人、小说家余地自杀,桓开专门为此写了一篇充满同情与怜悯的诗歌《中心》。现在想来,余地的行为无疑在桓开的精神世界投下了一道浓重的阴影,因为在《中心》里,桓开把余地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请看这样的诗行:“1998年,我曾走在自杀的路上/因为压力和对未来的无望/母亲和一个远房的亲戚救了我/我‘活’了下来,却一直走在‘死亡’的归途/和那些爱我的人一起,和那些爱我的人一起/死,只有先后顺序区别/但一路上,有‘爱’,使得痛苦的旅程/充满了快乐、感激和幸福的眼泪。”
2008年8月1日发生在诗人身上的事情,想必大家都知道了。在我看来,桓开最后留下的那首悲观——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做达观——的《消失》,几乎就是对《中心》主题的践约:
一只鸟,在层云上飞
那疲倦的身躯、迷茫的眼神
只能被云朵的灰色遮蔽
或许云有多么脆弱,然而
他无法穿透,他的力气已将用完
内心的虚弱,更能感觉天空的缥缈
努力地扇动翅膀,依旧没能绕过
雷电潜伏在云的周围
他爱的人都在下边
大地上熙熙攘攘地过往
他们无法飞起,沉溺其中——
幸福和苦痛,在尘嚣中难分彼此
雨下了,寒凉的雨丝
没有零落的羽毛
再无孤独的影子
之后,天空像新鲜的蓝床单
而大地,继续像垃圾场
物质坚持物质的腐烂
梦在无形地蒸发,一切在缓慢地
消失,于相近或遥远的未来。
生或死?这确实是一个问题,而且对人类来说是永恒的问题。也许透过生死,我们隐约窥测到的是生命的未解之谜,然而我们却永远也无法解开这个谜底。
……
诗人已逝,终究无可挽回。但值得庆幸的是,诗人留下的诗歌却超越了死亡的羁绊。我深信,诗人留下的那些充满才华、扣人心扉的诗歌,是没有也不会随着诗人生命肉体的陨灭而消亡的。那些脍炙人口的优美诗篇仍然将以精神的方式播布时空,捕获她的知音,进而绵延诗人的生命。这是诗人优越于常人和俗人的地方,也是诗歌显示其高贵价值的本质标志。
2009年5月10日深夜
广东诗人吾同树在家自缢身亡 四次写遗书(图)
来源:新华网 作者: 时间:2008-08-04 17:04:05

“努力地扇动翅膀/依旧没能绕过/雷电潜伏在云的周围/他爱的人都在下边……”广东诗人吾同树在完成他最后一首诗《消失》后的第二天(8月1日)在其东莞家中自缢,令诗歌界扼腕叹息。还不到29岁的吾同树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在广东诗歌圈里,他是“一位才华横溢、具备广阔创作前景的诗人”,在朋友眼中,他是“一位热情忠厚、仗义的朋友”,他去年在东莞买了一套小户型,有一个体贴的女朋友,但为何还决然赴死?
诗坛新秀,死有预兆?
吾同树本名曾桓开,1979年12月生于广东梅县,2005年7月毕业于暨南大学中文系。他的诗歌曾在《诗刊》《星星》等刊物发表,入选《2003年大学生最佳诗歌》等十余个选本。记者不久前收到了广东诗人俱乐部编辑出版的《白诗歌》第三辑中还收录了他的两首诗歌,诗人任评说,吾同树的诗写得极有水准,非一般诗人所能及,“我想,他会成为海子第二,一点也不为过。”吾同树的朋友刘大程撰文透露,在自杀前一天,他们还在网上聊天,吾同树还劝他不要因为生病花光积蓄的事情伤心,“健康了,再挣回来”。
吾同树不想别人猜测自杀的原因,因为他早就写过一篇文章,说“死亡是不可解释的。尤其是自杀,能找出来的原因都不是最关键的原因。”他在这篇文章中谈到了海子、张国荣等人的自杀,他甚至在一次纪念柯特·柯本的酒会上大吼:“想死的今晚就去死吧,不要犹豫;想活的要坚强一点,留下来,不要悲伤!”这篇文章似乎为他如今的自杀做了注脚。
失业青年,几多抑郁
诗人罗西是吾同树好友,他2日告诉记者,吾同树是在8月1日上午9时左右自杀的。罗西说,吾同树显然是下定决心赴死,“他的遗书有六页,写了四次,第一次是6月17日写的,第二天他又做了补充,7月又写了两次,对身后事做了详细的交代。”
吾同树的好友赵原说:“小树的死,与诗歌无关,主要是因为在我看来不太严重的抑郁和生活的压力。”罗西也认为,生活的压力和抑郁可能让吾同树想不开,吾同树是农家子弟,家里经济条件并不好,父亲又早逝,和母亲、妹妹相依为命,他当年读大学的钱都是靠贷款。吾同树毕业之后相对比较顺利,今年年初,他和朋友到深圳合作开了一家文化公司,但这家公司并没有给他带来收益,反而让他亏了不少钱,两个多月前,吾同树回到东莞,成为一个失业青年。
窘迫房奴,压力过大?
朋友们猜测,导致吾同树自杀的可能是他的一次生病和供房压力,吾同树去年在买房后曾写过一篇关于房奴的文章,他在文中透露,向各方借钱凑够了首付10万元按揭买了一套房,他和女朋友需要在今后20年每月支付银行2000多元的按揭款。罗西说,吾同树买的房子并不大,而在失业之后,女友的工资仅够支付按揭,加上生了一次病,生活愈发显得窘迫,“他走的时候,身上只有200多元现金,卡上剩下的存款也不到3000元。”
据了解,在得知噩耗之后,很多诗人来到东莞,川籍打工诗人郑小琼也到他家帮忙处理后事,诗人们紧急凑集了1万多元让朋友走得体面一点。据赵原透露,3日上午将在东莞殡仪馆设灵堂吊唁吾同树,下午将火化遗体,由其母将骨灰带回梅州。(蒋庆乔雪阳)
29岁诗人吾同树在家中自缢身亡
2008年08月05日(来源:南方日报)
上周五,青年诗人吾同树在位于(广东)东莞的家中自缢身亡。4天前,他刚被东莞一家报社录用。诗友们在悼文中提到,吾同树生前觉得生活压力大并且感到厌倦,而吾同树在生前的一篇文中也写到,他面临着极大的房贷压力。

进报社仅4天自缢身亡
昨日上午,记者收到《文化周末》编辑部寄来的最新一期报纸,出版日期为8月1日。记者看到,这期报纸的封面上写着“最意网十大写手之一、青年作家李云龙青年诗人吾同树双双加盟本报”的字样,用的大号红色黑体和报宋字体。
据《文化周末》介绍,今年29岁的吾同树,原名曾桓开,1995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在《诗刊》、《星星》、《鸭绿江》、《北京文学》、《作品》等数十家全国性报刊发表文学作品500余篇(首),被《诗刊》评为“2007年度中国20位最具活力青年诗人”。
不过就在这期报纸出版的当天上午,吾同树在家中自缢身亡。《文化周末》负责人汪晟说,他回江西探访生病的母亲,周五上午打电话得知吾同树没有到办公室,于是又打吾同树的手机,却被告知关机,后来才知道他已经上吊身亡。
据汪晟介绍,上周一即7月28日,吾同树在朋友的介绍下到《文化周末》工作。他很勤奋,每天早早地来到办公室。上周四,汪晟跟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考虑到他文字功底不错,打算安排他做一些专题。在上一期的《文化周末》报纸上,记者看到了两篇署名“曾桓开”的稿,当时他是实习记者。这两篇稿件是关于莞产音乐剧《蝶》获韩国国际音乐剧最高奖和一家艺术馆开业的消息。
在汪晟的印象中,吾同树内向、儒雅、单纯,很有书生味,让他想起了以前的自己。
生前面临较大生活压力
从诗友写的悼文中可以看出,他面临着极大的生活压力并且感到厌倦。
据介绍,吾同树的家在梅州偏远农村,他自幼丧父,他和妹妹靠母亲拉扯大,家里很穷。2005年7月,吾同树从暨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入职金地集团东莞公司。东莞作家航亿苇在博客中说,吾同树“后来去了深圳,办了家文化传播公司。听说亏了。或许生存的压力让他最终做了这种绝望的选择。”另据介绍,吾同树生了一场病,在进《文化周末》之前失业半年。
曾经和吾同树有接触的一些人则认为,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不堪房贷压力。据介绍,吾同树去年和女友按揭买了一套复式房。后来吾同树应一家刊物之约写了一篇名为《同是房奴沦落人》的文章,叙述了他购房的心路历程。文中写到,他东借西凑,凑齐了10万元,支付首期房款、律师费、契税等费用。
吾同树在文中感叹:“从来没有这么花过钱,但花得很疲倦。”据介绍,他每个月要还2000多元的房贷,要供240个月。“供到那时候,差不多都有白胡子了吧。”他这样写道。
而这让诗友们很羡慕。刘大程说,吾同树毕业两三年就和女友买房了,“而我们这些在底层辗转滚打的家伙,来东莞这么多年仍两手空空,对买房连想都还没多想”。
不过有媒体透露,今年年初,吾同树从深圳回来后就失业了,靠女友的薪水维持生活,交完7月的房供后,他手中的现钱紧张了不少。关于这一说法,尚未得到证实。
诗友们反思生存之道
对于吾同树的死,汪晟很痛心。汪晟说,此前他还没有和吾同树谈待遇的问题,但是在《文化周末》的收入,足够他支付房贷,他准备从江西回来后再跟他谈待遇问题,没想到竟然成了永别。
对于吾同树的死,诗友们除了感到无比痛心外,也在思考这个社会的生存压力。他的朋友赵原说:“在我们的思想和内心中,在我们对这个时代和对这个世界的认知中,一个诗人的死亡,从来都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
刘大程在悼文中这样写道:“在这个生存压力逼人的时代,我们都过得不轻松,不快乐。”当看到吾同树和女友辛苦置下的房子,刘大程觉得悲伤而愤怒:“不就这么宽一点的复式结构的居所吗?一点也不敞亮,囚笼般压抑感扑面,竟就要那么几十万?一月月地掏钱供着,直供到渐趋年老?与其如此,我如挣到了生活资本,是宁愿回到僻远的乡下,住着几间瓦屋。”
吾同树在生前访谈中自述
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的命运比较坎坷,少年失父,失去了精神支柱和经济支柱,接下三年失去人生导师外公和疼爱我的祖母。这三位亲人的离世,使我的心境受到了磨洗,深切感触到生命的脆弱、岁月的无情和人生的悲凉。另外,求学路上的坎坷,勤工俭学经历的况味,也给我的精神世界很大冲击。一次次变故,让我从一个单纯、骄傲的,享受着亲人、师长恩宠的少年,渐渐转长成一个独立、勤奋,有点悲悯、忧伤的情怀的青年。我是向善的,但也常有恶念。在对恶念的克制的过程中,我变得复杂起来。
可以说,我的作品笼统地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我在异乡的惆怅,包括对往事的回首,对异乡孤独的描述,对一个罪恶的忧伤的灵魂的自我救赎;另一类作品就是写底层——时髦的说法是“草根”,我写我在号称“浪漫之城”的珠海、在“花城”的广州、在“东方底特律”东莞看到打工者的生活状态、遭遇,对他们寄寓着我深深的祝福,同时我又是他们当中的一分子。除了你点到的那两首,还有《冬天的九个瞬间》《民工》《台风过后》等几首我自己比较满意的。“苦难”,对我而言,是怀念之苦,切肤之痛,是岁月的碾痕,是我每天看到乡村、城市里那些底层人民生活中难于摆脱的阴影。
我在同情着这个世界熙熙攘攘的人们。我们都是艰难地生活着,有人忍受着内心的痛苦,有人背负着物质的重担,更多的人是在双重的包袱的压迫下,踽踽独行。我从未同情过自己,其实,我一直把这些降临于身的“苦难”当作命运的安排。我从未讳认:我是一个宿命主义者。悲情成为了我诗歌抒情的基调。我渴望在文字里除了流露悲观外,能注入多一点对尘世的宽容,对命运的敬畏感。
诗人辛泊平说:“吾同树的诗,既没有学院诗人的高蹈和艰涩,又没有当下口语诗人的油滑和轻飘,而是把各种元素拿捏得恰到好处,让人不仅读着舒服,也愿意长时间玩味。”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首吾同树的诗,纪念逝去的年轻生命。
独自莫凭栏
吾同树
眺望那些远远的山脉,薄暮的边缘
不适合怀念、望乡以及任何的愁赋
因为你只是一个人
在异乡,你寂寞得没有声音
乡音便隐藏了起来
你寂寞得没有回忆
那些有趣的事说与谁听
你寂寞得——
仿佛随时可以把自己忽略
可以丢失,可以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