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荒谬,命运荒诞,生活荒凉,一场落荒而逃的出走与归来。
这是皮兰德娄的《已故的帕斯卡尔》这本书的主线。主角帕斯卡尔是一个小镇上的图书管理员,生活郁郁寡欢,像蝼蚁一般匍匐于命运的翻云覆雨手中。如果不是一场赌场上不讲武德式的大杀四方和一场意外的被宣告死亡,或许生活依旧在平铺直叙中划上一个扭扭曲曲的句点。这其实就是芸芸众生中大多数人的命运,而帕斯卡尔幸运又不幸地走上了一条与众不同的人生之途,在被篡改的命运面前,最终比别人多活一场,尽管“死去”的帕斯卡尔将自己第二次命运的剧情设计地精彩绝伦,但最终却发现依旧是一地鸡毛,螺蛳壳中做道场的结果不过是大梦一场而已,一切似乎未曾更改过,“死去活来”之际,并非是王者过来,自己命运的青铜底色从来就不曾有一丝一毫的改变。

皮兰德娄
这是一场没来由的悲从中来,一开始出场就带有一种宿命的悲剧。
开宗明义的“我的名字是马提亚·帕斯卡尔”,这样的一个点睛之句其实包含着一种大彻大悟后的淡定与落寞,对自己的过往和家族只字不提的背后,是一种痛彻心扉的自我诀别,也是一种身不由己的欲罢不能。这场离奇的故事剧情终将落幕之际,主人翁只能以“我想,我应该是已故的帕斯卡尔!”这种略带自嘲的语气,呼应一开始的独自寂寥的出场。
这场匪夷所思鬼使神差的人生荒诞剧中,已故的帕斯卡尔和冒名重生并最后决定“自杀”的阿德里亚诺·梅伊斯,一人分饰二角,一刀不能两断,最终在一边竭尽全力地追寻自我中一边重复上演着命中注定的失败剧目,寻找是一个错误,重复是一个错误,醒来时却发现没有退路,一度只得在命运面前不甘心地放下武器缴械投降。

或许,这一切正像帕斯卡尔在第一次“死亡”之后,面对“重生”之后无所适从的一团糟的状况,一语成谶为自己的未来写下了一个伏笔式的断言:“归根结底,我最大的问题就是——生活!”诚哉斯言,他之后的一切遭遇都是为这样的断言写下的一个个蹩脚的注释,无论是他作为梅伊斯所面临的无法承受的纯美爱情,还是面对不公平的待遇之后无法光明正大地与人决斗来了结事端,还是他回到他原来的农场时他的妻子早就另嫁他人……
可是,生活到底是什么?
在皮兰德娄的笔下没有所谓循规蹈矩的真相。帕斯卡尔的奇遇更像是一次剑走偏锋的虚张声势,这样一个充满着偶然和不确定性的人生奇遇,在通常意义上说由于显得过于伪饰而失去了普遍意义上揭示人生真相的力度。这样的处理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继承了以意大利民间文学的传统,对故事性或者说戏剧性的偏爱可以看成是一种青出于蓝的扬弃,看似荒诞不经的表象之下,其实无意间打开了一扇现代主义的大门。正是这样夸张的变形的看似不合常理的外在表现形式,却蕴含着锐利而坚硬的现代主义的内核,这样的一种表达方式也为皮兰德娄的戏剧创作开启了先声,从而使他的戏剧创作在更深层次上抵达了浮夸的现实所遮蔽的真正内核,他的开创性的戏剧也因此享有经久不息的盛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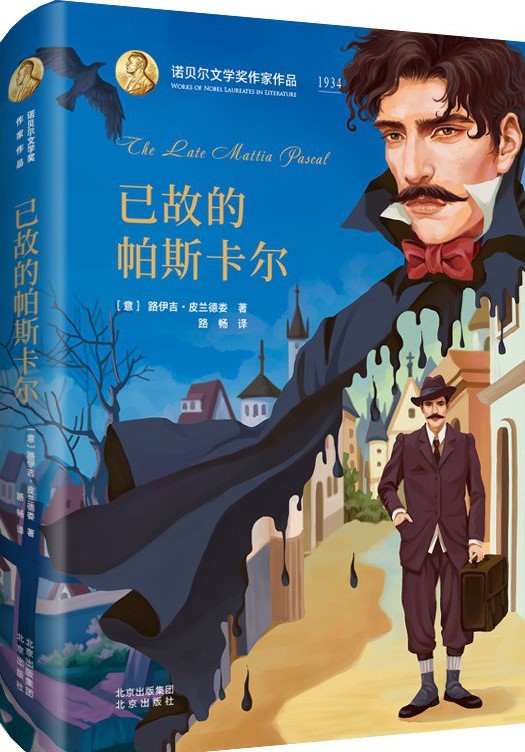
皮兰德娄的创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个性特点。他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致辞中这样说道:“对于我写到的一切,我都会用无限的关心和深刻的真诚去对待,并对其中揭示的人性的真实进行思考:热爱和敬仰生命,免不了要经历痛苦的涅槃、难过的过往、恐怖的伤痛和所有带给我经验和教训的错误。”在这本《已故的帕斯卡尔》中也可以看出这样的思考轨迹,卡斯帕尔的一切遭遇,历经千帆之后,最终还是回归于对生活真诚的相信,这何尝不是皮兰德娄本身的写作和生活态度的一种委婉的自我表达。

所谓“借他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皮兰德娄在这本书中,总是隐约闪现着自己生活的某种不足为外人道也的滋味。皮兰德娄的少年和青年时期的家庭生活十分优渥,祖父腰缠万贯,父亲年轻时从军后来经商开矿赚得盆满钵满。这样一个“有矿”的家庭出生使他从小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并且遵从自己的兴趣投身于文学创作,在结婚之后在妻子的财力支持下更是生活的优哉游哉,但好景不长,后来家族的矿产生意由于洪水和塌方而完全被毁,皮兰德娄的生活一落万丈,而他的妻子也因此患上了精神分裂症。这样的悲惨的人生剧变使皮兰德娄接触并进一步深入了解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潜移默化中促进了他文学创作主题的转变,而《已故的帕斯卡尔》正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之作,书中带有悲剧性质的黑色幽默的荒诞变形的现实元素的融入,使他的作品在诠释现实生活与自我追求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和无法突破的困境方面别出机枢,皮兰德娄也成为“受弗洛伊德影响的第一代人,开始重新估价现代环境中的个性之谜的一代人”(美国戏剧评论家诺斯·霍顿之语)的杰出代表。

从弗洛伊德的理论出发,皮兰德娄在这本书中不自觉地触及到了现代社会中的“自由的困境”,就像书中帕斯卡尔念叨的那样:“一开始,我以为我获得的是无尽的自由,后来我才发现,这种自由其实受到了各种各样的限制,……为了得到这种自由,我需要付出超乎想象的代价。虽然我获得了自由,却也伴随着这自由陷入了孤寂,我处于完全的孤立之中。”但皮兰德娄笔下人物却又不是完全被动坐以待毙地去接受这样的命运审判,这或许也是他自己坚定的信条,就如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中提到的那样:“幸福在他想象的世界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可是生命的尊严还完全有余地周旋。”帕斯卡尔的诡异的人生遭遇就生动而鲜明地印证着这样的观点。

为了追求并找回这种“生命的尊严”,书中的帕斯卡尔在一次次的纠结之后,终于下定决心突破那种作茧自缚的自我禁锢,这样的寻找最终实现了一定程度的自我救赎和和解。
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帕斯卡尔对自己逝去身份的重新构建尽管不能使自己完全回到过去,但以“已故的帕斯卡尔”的身份重新在广袤无限的生活中一点点地拓展出一小片周旋的余地。这样的“重生”带有某种哲学意味的自我重塑,尽管残缺,“因为我没有恢复到法律的范畴,也没有回归正常生活”,不过当生活这个最大的问题已经不再成了他肩上的枷锁之时,不再幻想着彻底决绝的逃离,而是忠于窘迫但真实的现实,正视那种情理之中的失败,最后,他终于有限地找回了内心一度被遮蔽尘封的真实自我,在荒诞不经的生活日常中重塑那曾经一度破败不堪的个体生命的尊严感。
这,或许才是皮兰德娄的《已故的帕斯卡尔》带给我们最大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