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郭学祥,1940年出生,浙江诸暨人。1959年毕业于湘湖师范学校,1961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
讲述 郭学祥
主笔 牛牛
01 豆腐拿斧头劈,猪肉拿锯子锯
加格达奇,在鄂伦春语中,意为“有樟子松的地方”。
如果没有成为一名光荣的铁道兵,我可能永远不会去这个地方。
1964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三、六、九师进军会战大兴安岭。

1965年10月,我从铁道兵学校(四川绵阳)毕业,回老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三师)报到。
我们四个学员从四川出发,坐火车到北京,再到齐齐哈尔。到齐齐哈尔后,还要坐一天一夜的火车,才能到加格达奇。
祖国的北方已经白雪皑皑。
车窗的玻璃上,结着一层厚厚的冰花,冷气不断从外面透进来。
我穿着一件棉袄,外面再裹一件棉大衣。
衣服是军校里发的,在四川过冬肯定够了。但在这里,似乎和穿一件单衣没什么区别,还是冻得直打哆嗦,牙齿咯咯作响。
四个人挤在一起,互相取暖。

第二天早晨,太阳从樟子松的间隙中照射过来。
列车缓缓驶入加格达奇。
走出火车站,外面是一条黄褐色的土路,土块已经冻得硬邦邦了。
道路两旁,是一排排军绿色的帐篷。整个城市,只能见到零星的几座“建筑”。
店里卖的是冻梨、冻柿,豆腐是拿斧头劈的,猪肉是拿锯子锯的。

生活用水,靠冰块化
几个人来到师部招待所,在这里休息一晚。
说是“招待所”,其实也是帐篷,左右两排通铺,一共能住八个人。工作人员帮忙点了煤炉,给我们取暖。
厕所是露天的,铺两块木板,中间挖个坑。
排泄物已经冻成宝塔形了,越到上面越尖,边上还摆着一根钢钎。下一个人方便前,要先拿钢钎把“宝塔”敲掉。
在招待所住了一夜,我们四个人到机械营营部报到。
营部边上,刚好有一个连队在搭帐篷。
看我们没什么事,他们就说:“你们来帮一下忙吧,刚到这里,先熟悉熟悉。”
我们四个便去帮忙了。
我戴着一双绒手套,钢管拿在手里,像握着一根冰棍。
手暴露在空气中,不到五分钟,就冻麻了。
我赶紧把手塞进棉衣里,放在咯吱窝下面捂一会。等手恢复知觉了,再拿出来。干一会儿,再捂一会儿,周而复始。

铁道兵搭帐篷
干了两个小时,帐篷终于搭完了。
回到室内,脱掉手套,手已经没有血色了。
四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感觉心里凉了半截。
我们满腔热情回到老部队,没想到,才来两天,这里恶劣的环境,就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不知道还有什么困难等着我们。
02 一根毛竹打在下巴上,牙齿掉了4颗
我老家是诸暨浣东新东村的。
我们家五个兄弟姐妹,我是家里的老幺,上面还有一个哥哥,三个姐姐。
父亲是中医,每个月都要去诸暨店口坐诊,一个月回来一次。
每次父亲回家,都有不少人来家里找父亲看病。
遇到条件困难的,父亲也不收钱,开个药方子,让他们自己去县城抓药。
母亲走到哪都把我带着,她教育我说:只有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有出路。
1956年,我考上湘湖师范学校。
本来读3年的,但“大炼钢铁”开始,我提前毕业,进了萧山钢铁厂当化验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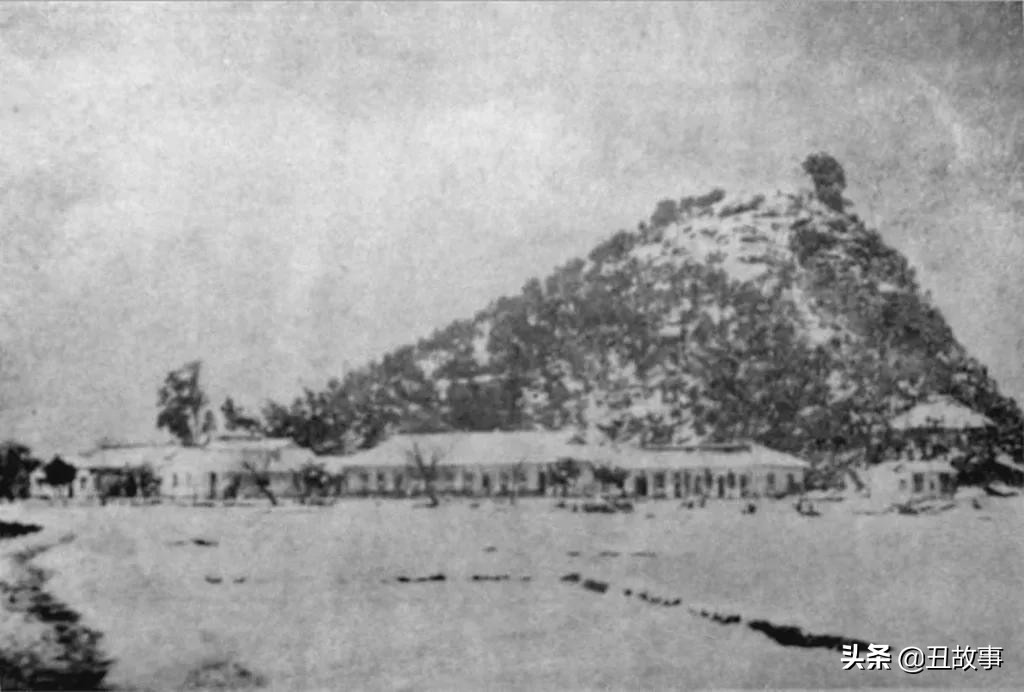
湘湖师范
厂里来动员参军,我去报名登记,体检也通过了。
等通知书发下来,我才回诸暨和家里说。父母有些生气,觉得没和他们商量就去当兵了,但也没阻拦。
母亲只是说,出门在外,你自己各方面注意。
1961年7月,我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第三师11团1营3连。

部队驻扎在江西南昌县。
刚到部队两个星期,连队就接到任务,去三江口背毛竹。
一人背一根,到目的地后,走在我前面的战士,把毛竹往地上一丢。
没想到,这根毛竹弹性很好,丢在地上,又弹了起来。
刚好打在我下巴上。
顿时鲜血直流,牙齿被打掉四颗。
我被送到江西九江171医院,进行救治,镶上了四颗假牙。
到部队两个星期就负伤了,对我是个不小的打击。
1962年6月,我考上石家庄铁道兵学院,学习“铁道工程技术”。
后来,这个专业划到了四川绵阳的铁道兵学校,我又去四川继续学习。

和铁道兵学校的同学
03 刚到工地,就听说山体塌下来了
1964年,我和铁道兵学校的同学们去“成昆铁路”实习。津贴每人每月6元。
四川的山是绵延不断的,几乎找不到一处平坦的地方。
我们坐车从成都青龙场出发,前往乐山范店镇。
部队的运输车,绕着盘山公路一圈圈地往上爬。好多学员都晕车,在车上吐了。
来到“大石板隧道”施工现场。
工地在半山腰上,一边是崇山峻岭,一边是陡峭的山壁,往下一两百米就是大渡河。
大渡河河水浑浊,波涛汹涌。

大渡河
刚到工地我们就听说,前段时间,成昆铁路上出事了。
靠近云南的一个隧道在施工的时候,山体塌下来了,牺牲了很多战士。
上级要求我们,必须戴好安全帽,保证绝对安全。
我的工作是打风枪。前面一个战士主要操作,我在后面辅助他。
隧道里灰尘很大,我们没有口罩,只能拿一根水管接在风枪上,一边打,一边往洞里灌水。
这样打出来的灰尘就变成泥水了,风枪也不会发烫。
每天工作完走出隧道,一个个都是“泥人”了。
这里的山体都是石头,我们在隧道截面上,用风枪打出二三十个洞,再把炸药塞进洞里,进行爆破,把隧道一点点炸出来。
打孔的位置,和炸药的用量,都有严格的讲究,专门有人负责计算。
炸药放多了,山就炸塌了,炸药放少了,石头又炸不开。
我们一天至少炸两次,能推进一米,已经非常不错了。
一千多米的隧道,就这样一天天往前推。
当时,毛主席有一句话:“铁路修不好,我睡不好觉,没有钱,把我的工资拿出来,没有路,骑毛驴去,没有铁轨,把沿海铁路拆下来,一定要把成昆铁路打通。”
我们的口号是:一定要把成昆铁路修好,让毛主席老人家睡好觉。

我们还要进行“社会主义教育”。
住在当地的老百姓家里,和他们一起下地种田,给他们挑粪,帮助他们提高生产,宣传社会主义。
在老百姓家吃饭,要给伙食费,一天三毛钱。
老百姓吃的都是红薯和稀粥,粥稀到什么程度呢,就是一碗开水,加了几颗米。
吃了一个礼拜,学员们就没力气干活了,一个个饿的面黄肌瘦。
我们在“大石板隧道”实习了几个月,隧道里风枪声音很响,一天到晚“突突突”。
实习回来后,我耳朵不行了,别人说话听不清楚。过了几个月,才恢复听力。
1965年10月,我从铁道兵学校毕业,回老部队三师。
此时,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三、六、九师已经进军大兴安岭。
三师师部,就在大兴安岭的加格达奇。

04 连长踢踢我们,问有没有活着的
到加格达奇的第四天,我被分配到3师机械营1连,当技术员。同行的三个学员,也都去了各自的连队。
1968年开春,连队接到任务,开往“西林吉”(现在漠河市的位置)
我和三十多个战友,作为先头部队,提前去“西林吉”搭建营地。
天蒙蒙亮,我们就集合出发了。
运输车行驶在林间公路上,凛冽的寒风呼啸而过。两旁是高大的樟子松,偶尔还能见到几只狍子和四不像,在林间停留。
这一路走了七八个小时。
赶到目的地,太阳已经下山了。
大家把东西一点点搬下车。
大兴安岭的晚上,因为有北极光,就算没有月亮,也不会很黑,抬头还能看到白云。
东西搬完,我们用行军锅,煮了点高粱米吃。
连长说:“今天太迟了,大家先休息吧,明天我们再搭帐篷。”
此时的气温,已经零下四十多度了,我们要在雪地里露天过夜。
我们找了一块树木不多的地方,简单清理了下,把帐篷布平铺在雪地上,再把各自的毛毡和垫被盖在上面。
大家一个紧挨着一个,躺在垫被上。再找来所有能当被子的东西,盖在身上,最上面用一层帐篷布罩住。
头上戴着大头帽,只留眼睛和鼻子在外面,其他都缩在被子里。
也许是太累了吧,躺进去没多久,我就睡着了。
再醒来,天已经亮了。
连长走到我边上,用脚踢踢我,说:“还好,这个还活着。”
我搓了搓眼睛,醒了。
连长扯着嗓子喊:“你们有没有冻死的啊,冻死的,起来说句话啊!”
大家躲在被子里,一起喊:“都冻死了。”
从被子里钻出来,眉毛和睫毛上都挂着一层白霜。盖在最上面的帐篷布,也铺着一层厚厚的白霜,像下过小雪一样。
大兴安岭的早晨,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松针的味道。
大家干得热火朝天,有的操作机器,平整场地,有的搭帐篷,拧螺丝。忙活了一天,一个小型的营地就建成了。
第二天,大部队抵达后,顺利驻扎下来。

05 挖下去,全是枯枝败叶
修公路是我们机械连的主要任务之一。
大兴安岭的铁路,都是公路修到哪里,铁路修到哪里。只有把公路修好了,铁轨才能运进去。
大兴安岭土质比较特殊,挖下去全是“腐殖土”。
所谓“腐殖土”,是树木的枯枝残叶经过长时期腐烂发酵后而形成。
这种土受力强度不够,直接在上面修路,车开上去就塌陷了。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操作机械,把腐殖土清理干净,再从取土场,运来比较干燥的土铺在上面,平整压实。
但大兴安岭是原始森林,腐殖土实在太厚了,有些地方甚至超过一米。
为了按时完成任务,我们就地取材,把木头并铺在路上,再往上面盖土,这样就增加受力面积了。
部队有规定,不能乱砍乱伐。
我们都找一些林业公司砍下来,堆在那里没用的,或者一些半死不活的树木。
每修好一段,我们就要进行验收,驾驶汽车在上面来回开。
有一次,我们修“嫩林线”(嫩江到林海),到马尾山这个地方。
马尾山一边是甘河,一边是山脉。
大兴安岭的山不高,都是小丘陵,但土质松软,下面都是沙土,挖不了隧道。
我们只能从上往下,在山上挖了一道两三百米长,三十多米深的口子。
我们管这种方法叫“大拉沟”,也叫“路堑”。
我们机械连操作推土机、铲运机,挖了几个月,才把“马尾山大拉沟”的轮廓挖出来。后面交给线路连,由他们继续施工。

还有一次,我们在“古莲”修公路。施工的时候,正好是大兴安岭的夏天。
夏天最怕的是蚊虫,大兴安岭的蚊虫特别厉害,从早到晚都要戴防蚊帽。
太阳出来前,都是“蠓”。
蠓比蚊子要小,像一颗黑芝麻,也是吸血的。被蠓咬到,奇痒无比,还会起水泡。
太阳一出来,蠓就躲起来了,接下来是牛虻登场了。像轰炸机一样,嗡嗡嗡地在空中盘旋。
等到下午,天气凉快了,蚊子又出来上班。黑压压的一片,随手在空中抓一下,都能抓到四五只。
我们开玩笑说,大兴安岭的虫子是“三班倒”的,但铁路兵战士是不休息的。

06 两次命悬一线,死里逃生
1973年,营部需要土木工程师,就把我从连队调过去了。
营部就不用睡帐篷了,是住在房屋里的,屋里还有“地火龙”。
“地火龙”是大兴安岭的铁道兵发明的。
用砖和泥垒起的烟道,在床铺下面绕行,烟道一头连着火炉,另一头连到屋外,作为烟囱排烟。
火炉烧起来后,整个通道就像一条火龙,均匀、持久地散发着热量。外面天寒地冻,屋内能达到20多度。

这里叫龙头山,离加格达奇18公里,身后的房子就是营部
我住的这幢房子里,有五个小房间,我们五个技术人员住在这里。
有一天早上,起床号响了,战士们都出早操了。
我们技术人员,也要和大家一起出早操。我听到起床号声音,但感觉浑身没力,怎么都起不来,很想睡。
迷迷糊糊又睡着了。
通讯班班长很奇怪,今天技术组的人,怎么还没出来?
他跑过来敲门,敲了很久没人开。
一脚就把门踹开了。冲进来一看,里面全是烟,我们五个人都瘫在床上,一动不动,怎么叫我们都没有反应。
班长赶紧又叫来几个战士,把我们抬了出去。
五个人被抬到广场上,裤子都湿了,小便失禁了。
营部马上向师部汇报情况。一个小时不到,医疗队就赶来了,给我们检查身体。
医疗队的医生说,要是再晚十分钟,这五个人就没了。
医生让我们在操场上走路,绕圈圈,呼吸新鲜空气。围着操场走了一个上午,我们几个才算缓过来。
后来知道,是地火龙的烟囱堵住了,烟排不出去,就渗到房间里来了。
多亏通讯班班长当机立断,不然五个人就没了。
还有一次,我和几位技术人员,去连队指导工作。
连队驻扎在额木尔河边。连队的战士告诉我们说,部队在上游捕鱼。
额木尔河有一种细鳞鱼,在满清时是上供的,慈禧太后称其为“龙凤之肉”。

额木尔河
在大兴安岭,我们顿顿吃土豆和大白菜,一天两顿高粱米,星期日才有大米饭,更不要说猪肉和鱼肉了。
他这么一说,大家口水都下来了。
跑到额木尔河边,河面已经冻上了,冰层下水还在流动。我跑到河中央,拿铁锹在冰面上凿开一个窟窿。
就看见鱼一条接着一条,从冰层下飘过来,场面非常壮观。
这种鱼木木的,有人在上面也不怕。过来一条,我捞一条,很快就捡了一箩筐。
看差不多了,我就想回岸边了。
没想到,刚走几步路,“咔嚓”一声,冰层裂开了。
我一下子掉进了冰水里。
冰水从我棉裤的裤腿里,一点点往上钻,很快就钻到了我的胸口。不到几秒,全身都被冰水浸透了。
我双手扒着冰面,但衣服太重了,根本爬不上去。
岸边的战友,看到我落水了,马上拿着树枝把我救了上来。
我脱掉湿透的衣服,战友们又一人脱下一件,给我穿上。
中午,我们在连队吃饭,炊事班烧了一大盆红烧鱼块,都是早上捞来的。看着锅里鱼,我有点哭笑不得。

07 车子发生了侧翻,朝战友身上压去
1975年1月20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营部断粮了。
营部的管理员戴荣舫,和驾驶员一起去买粮食。
营部在龙头山,离加格达奇18公里。买粮食的地方,在大杨树方向,开车来回得一天时间。
大清早,他们就开着“嘎斯车”出发了。
但不到两个小时,车子就回来了。
驾驶员停好车,跑下来说:“出事了,出事了。”
我们跑过去一看,戴荣舫瘫在副驾驶座上,一动不动。
驾驶员说,他们开出30多公里,到了一个下坡。没想到前几日雪下得太大,把路都堵上了,他连忙紧急刹车。
结果车子打滑,发生了侧翻。
车上没有安全带,戴荣舫当场被甩了出去,侧翻的车子刚好砸在戴荣舫身上。
战友们把戴荣舫抬下车,平放在办公室的桌子上。
我摸了摸他的手,还是有温度的,但人已经没气了。
师部的卫生队赶来了,抢救了一个多小时,还是没能救回来。
戴荣舫为人不错,工作负责。他是管理员,营部的吃喝拉撒,他都很劳心的,不管是打扫卫生,还是组织会议,他都冲在最前面。
这么热心的人,一下子就没了,大家都挺难过的。
出事的第三天,戴荣舫的家人来了。他们从湖北出发,坐火车赶到加格达奇。
遗体还躺在办公室里,部队的领导也赶来了。
房间里气氛很沉重,戴荣舫爱人,还有他的三个孩子,大儿子8岁,二女儿6岁,小女儿才2岁。
他爱人抱着三个孩子,哭成了泪人。
戴荣舫的岳父也来了,他是个老革命,站在一边安慰女儿说:“他是为革命牺牲的,不要伤心了,部队里总会有牺牲的。”
戴荣舫被安葬在加格达奇北山的烈士陵园。
我和王卫生员一起,送戴荣舫的家属回老家,湖北天门岳口镇。
看着车窗外的景色,从一望无际的白色,变得色彩丰富起来。到了武汉,我们坐轮船过汉江,江水波光闪烁,奔流不息。
我和王卫生员在湖北住了一个月,帮戴荣舫办好了烈士证和抚恤金,还给他爱人安排好工作。
临别的时候,戴荣舫的爱人,带着三个孩子来送我们。
我心情很复杂,只能反复说:保重,有困难找政府,有困难找政府。
大概七年前吧,我在“铁道兵吧”上看到,戴荣舫的女儿戴红梅,在网上发帖。
戴红梅说,想找到爸爸当年的老同事,了解一下爸爸的事情。她列了几个名字,其中一个是“郭工程师”,就是我。
我给她留言:我就是你要找的郭工,当年我送你们一家人回湖北,你还是个小孩子……你们现在还好吗?
消息发出去,可惜一直没有回应。
08 一个解不开的结
1977年4月,加格达奇依旧寒风凛冽。
我即将离开加格达奇,从部队复员。在部队生活了17年,过惯了集体生活,有太多的舍不得,放不下。
战友们把我送到加格达奇火车站。
列车驶出加格达奇,窗外的风景一幕幕闪过,眼睛不自觉湿润了。
回到杭州,老单位萧山钢铁厂已经没有了,我进了杭发厂,在二车间当一名工人。后来又当车间副书记,书记。
1991年,我去了杭发技工学校,当校长,支部书记。一直干到2000年,在杭发厂光荣退休。

和车间的同事
爱人在萧山胶木厂工作,后来又调到钟表机械厂。
我和爱人1968年结婚,那时我还是铁道兵,她是一名小学老师。

女儿出生了
我们一年只能见一次面,就是我的探亲假,20天。
我们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
孩子出生后,一直由我爱人照顾,她非常不容易,将两个孩子拉扯大。

我们一家四口
2019年,女儿和几个朋友去东北玩,去加格达奇,想带我一起去。
离开这么多年了,我非常想念那里,可惜因身体原因,最后未能成行。
女儿到加格达奇后,拍了许多照片发给我。
加格达奇变化很大,帐篷没有了,街道比以前宽敞了,高楼大厦都建起来了。

加格达奇火车站
加格达奇北山上,“铁道兵纪念碑”耸立在万绿丛中。碑前还有一只马鹿雕塑。
马鹿是大兴安岭林区特有的动物种类,置于主碑前面,象征着大兴安岭地区各族人民对铁道兵部队开发大兴安岭时的大力援助。
主碑是两根放大的钢轨,中间镶嵌着铁道兵兵徽,像一个解不开的结。

铁道兵纪念碑碑文记载:
1964年,遵照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三、六、九师8万官兵进军会战大兴安岭。
广大指战员在举世罕见的“高寒禁区”爬冰卧雪、宿露餐风、英勇开拓、顽强拼搏,在林区各族人民支援下,到1983年底,共修建铁路792公里,桥梁124座,隧道14座,为开发林区,建设边疆做出了重大贡献。
为铭记他们的光辉业绩,缅怀英勇献身的烈士,特立此碑。

牛牛说:铁道兵精神永存
一个夏日的早晨,我坐地铁来到萧山潘水站。

走进小区,沿着树荫一直往里走,一幢独栋的楼房,上到三楼。郭叔已经侧着身子,在门边等待了。
郭叔说,你就是牛牛吧,欢迎欢迎。
郭叔的爱人出门了,家里只有郭叔一人。
我注意到,房间里摆着不少荣誉证明,其中就包括郭叔和他爱人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郭叔说,这是前段时间发下来的。
茶几上,还有一张白纸,白纸上摆着许多老照片。原来是,郭叔知道我今天要来采访,已经把照片找出来了。
我问郭叔,平时有什么兴趣爱好?
郭叔说,他最近在学习强国,学习很努力,已经达到支部的第三名了。说完,郭叔拿出手机,向我展示了“积分排行榜”。

郭叔今年已经81岁,但说话中气很足,还时不时来几句诸暨话。
郭叔说,他从部队回来,已经在萧山生活了四十多年了,还是改不了老家口音。
回忆起铁道兵往事。
郭叔说,离开部队多年,再没见过老战友,但心里一直挂念着部队,希望通过讲故事这种方式,向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致敬,向老部队和老战友表示怀念。
讲到挖隧道时,郭叔说,他们当年是靠打风枪,放炸药,一点点往前推的,一天最多挖一两米,不像现在有盾构机,一个月挖几百米。
听到这个数字,我有些震惊。
一千多米长的隧道,就靠铁道兵们一天一米地前推,硬生生凿出一条通路。
当年的艰辛,可想而知。
铁道兵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解放战争时期。
1945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东北组建了一支武装护路队伍,后改为东北民主联军护路军。
1953年9月9日,中央军委决定组建铁道兵领导机关,铁道兵正式作为一个兵种进入人民解放军序列。
1954年3月5日,铁道兵司令部正式在北京成立,最多时铁道兵总兵力达40余万人。
先后修建了鹰厦铁路、成昆铁路、贵昆铁路、襄渝铁路、东北林区铁路、新疆南疆铁路、青藏铁路和北京地铁工程等大型铁路,立下了汗马功劳。
直到1982年4月9日,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通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铁道兵建制,把铁道兵并入铁道部。”
12月6日,国务院、中央军委正式下达了关于铁道兵并入铁道部的决定。
铁道兵在解放军序列中消失,但铁道兵的功绩,却永远留在解放军的史册上。
如今,中国已拥有世界上最现代化的铁路网和最发达的高铁网。正是这些先辈们的无私奉献,才换来了今天的繁荣昌盛。
向中国铁道兵致敬,铁道兵精神永存!
愿山河锦绣,国泰民安。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