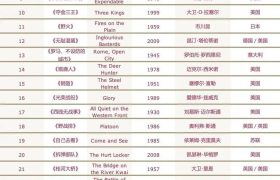关于“性”,中国人一向讳莫如深。
对于“肉体之欢”,我们的文化里有很多婉转隐晦的说法。最引人浮想联翩的,莫过于“云雨之欢”。
这简单的四个字,却隐藏着农耕文明中对于生育、对于“传宗接代”的殷勤期盼:云化作雨水,滋养万物,带来收获;正如夫妻之间的性爱,生儿育女,传宗接代。

清代著名作家李宝嘉在小说《官场现形记》中,借着别人之口,道出了古老文化中的婚姻观:
“自己辛苦一辈子,挣了这份家私,死了又没有个传宗接代的人,不知当初留着这些钱有何用。”
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时代,婚姻的社会原则被无限放大,“传宗接代”被视为婚姻的最重要的目的,所以”七出之条“中,才有“无子去”这一条款。
至于精神和肉体,通常处于从属地位,往往被无视,甚至遭到压迫。古有陆游和唐婉这样恩爱有加的夫妻,因妻子的不能生育,被迫离异;今天仍有不少女性,因为生育问题被离弃。

“精神和肉体”到底在婚姻中占据什么地位?婚姻里,爱、性与生育之间,到底何为贵?三者如果不能并存,又该如何取舍?
所幸的是有这么一部电影《砚床》,它用优美舒缓的叙事格调,给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性、爱和生育的冲突中,情与欲交织的故事。吴家少爷和妻子玉莲,在这种矛盾中苦苦挣扎,终究是一步走错,空留余恨。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花落空折枝:有爱无性婚姻中,一对委屈的男女,诉说着难言的悲剧
江南小镇,丝雨纷纷,滋养出玉莲这样娇嫩的美人花。走在小巷中的她,眉蹙春山,眼颦秋水。高门大户家的吴少爷,只瞥了那么一眼,便深深沦陷。
一对正好年华的璧人,男才女貌,天作之合。提亲拜堂,一气呵成,俩人就这么结为夫妻。
吴少爷是个才子型的人物,他会玩,懂得玩,玩得高雅,玩得有情趣。
他给玉莲画眉,教她跳舞;他让玉莲在家中一张巨大的砚床上,摆出各种诱人的姿势。妻子的娇美和青春,都被丈夫画进了画里。

他给玉莲讲关于这张砚床的故事:皇帝和皇后当初也在这张砚床上两情缱眷;玉莲却对皇帝和皇后有没有在这张砚床上有过“同房”更感兴趣。
一提到这个关键问题,吴少爷就闷闷不乐。
这对夫妻精神高度契合,拥有理想中的爱情。但肉体之痛,成了这对夫妇难以启齿的隐晦。
玉莲年轻的肉体,需要情欲的释放和异性的爱抚。但每次玉莲的求欢,都被丈夫拒绝。
玉莲使出一切手段,撩拨丈夫。吴少爷拥着玉莲躺在那张砚床上,面对妻子渴求的眼神,他偏过头去,只能对她说一声“算了,我们还是睡吧”,来掩盖自己的无能。

这又能怪谁呢?正是那张凉气渗骨的砚床,他贪图凉爽,在上面渡过无数时光。寒毒侵体,造成了吴少爷的男性障碍。
玉莲不得不压制自己的欲望。从没尝过“肉体之欢”的她,对丈夫爱得深沉又专一。
若不是家族”传宗接代“的逼迫,玉莲怎会知道,原来”性爱“竟然是这般滋味:它如水,滋养得她圆润丰满;它又如火,烧毁了她的大好年华。
“借精生子”引起一场情欲的大火
树欲静而风不止。玉莲和丈夫想要“一生一世”的愿望,被吴家老爷太太无情地撕碎了。
他们对这对闲散夫妻发出最后通牒:如果再不能生下后代,他们便没有继承吴家产业的机会;不但如此,吴少爷还要纳妾生子。
玉莲选择了不辩解。为了生育,她给丈夫煲了无数的汤药,问了无数次的神,许了无数次的愿。

希望一次次落空,吴少爷想出了一个馊主意:让玉莲和下人阿根同房生下后代:“只要你做了母亲,谁还能怀疑我不是孩子的父亲呢?”
面对丈夫“借精生子”的要求,玉莲反抗过,但最终选择服从。她那么爱他,情愿替他背负“不能生育”的黑锅。
但玉莲的爱,却无法撼动吴少爷心中的男权思想。他想要掌控一切,安排一切,他要用牺牲妻子的办法,来掩盖自己的生理缺陷。
仆人阿根,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卷入这对夫妻间的纠葛。他的出现,本是作为一个生育的工具,提供一个“精子”的牲口而已。
在丈夫的安排下,玉莲第一次和阿根有了云雨之欢。没想到竟是这般神奇。
事后阿莲看着镜子中的自己,脸蛋红润,容光焕发,在这个深宅大院的阴郁氛围下,她如一朵带露含珠的玉莲花,绽放出最光彩的瞬间。

吴少爷一生高高在上,这件事成了比“不能生育”更大的耻辱。
面对娇艳的妻子,丈夫第一次对玉莲发了少爷脾气。玉莲端来的药,被少爷斥责为“不干净,端回去重做。”
玉莲心中又悲有苦,还有说不出的委屈。一方面她要对抗心中被点燃的情欲,一方面还要在丈夫面前委屈周全,照顾他那可怜的自尊心。
欲望不是说放就放,说收就收的。

欲望是火,它一经点燃,便如烈火燎原,除非烧个一干二净,否则不会休止;这把大火,它烧死了两个人,还有一个半死不活,苟延残喘着余下的生命。
更高级的欲望,脱离了“传宗接代”的初衷,只为享受“肉体之欢”
有了第一次,就会有地二次。玉莲开始背着丈夫找阿根。
影片对阿根这个下人描述不多,这正暗合了阿根的定位:他只是一个符号,一个真实又健康男人的化身,他不需要用药罐子来维持生命力。
玉莲第一次感觉,和一个健康正常的男人在一起,是多么的美好!他们的肌肤之亲,如水交融。玉莲享受其中,超脱了“传宗接代”这个最原始的欲望。

尤其是和阿根的最后一次同房。那时玉莲已经被大夫诊断为没有怀孕。吴少爷又失望又屈辱,他打发阿根离开吴家。
趁着丈夫不在家,阿莲找到阿根,送给了他一块珍贵的磨条。玉莲对阿根的感觉,已经由肉体之欢,发展到依恋之情。

隐藏在身体里的欲望开始作祟,玉莲关上门窗,躺在了砚床上。阿根懂她的意思,于是在砚床上,他们有了最后一次肌肤接触。
这一幕,被提前回家的丈夫看在眼中。明明妻子已知道和阿根无孕,还主动求欢,对一个丈夫来说,这无疑是背叛。

对于一个失去性能力男人来说,又怎会理解一个女人对性的渴求呢?在他眼里妻子的“背叛”,实际上,只是她内心欲望的释放,是一个女人正常的诉求,无关精神契合,无关传宗接代。
就是在那一刻,吴少爷痛下杀机。最终,阿根被痛打一顿,然后被残忍地活埋在砚床之下。
那张砚床,是玉莲的快乐,她在上面和丈夫有过琴瑟和谐的过往,和仆人阿根享受过肉体之欢;而如今,那张砚床,它埋葬了一个鲜活的肉体,任由他化成了一具森森白骨,在这座阴森潮湿的古宅里游荡。

晚年的玉莲,一直在自问:“我不明白,要是我害了阿根,那谁害了我呢?”
是啊!欲望是无罪的,是更高级的快乐,它超越了”生育“的桎梏,让玉莲活得像个女人。
执拗于“传宗接代”的丈夫,送掉了年轻的性命;自赎和和解,让玉莲获得最后的幸福
吴少爷死了,死在30岁。家族和乡邻都说他是被砚床害死的,只有玉莲知道,他是被那些汤汤药药害死的。
即使灌下无数的苦水,即使把妻子送到别的男人身边,吴少爷也没能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他不但搭上了自己的性命,还搭上了妻子一生的幸福。他们当初明明有那么美好的精神之爱。
自卑让他拒绝了玉莲当初提出的“抱养一个孩子”的建议,嫉妒让他背叛了当初“让阿根离开吴家”的诺言,玉莲也被他桎梏在这桩婚姻里,变成了一个“活死人”。
晚年的玉莲,变成了一个面目丑陋的妇人。她无子也无夫,身体有疾,偏瘫严重;性格偏执又古怪,活成了一个令人讨厌的女疯子。

一个走南闯北收古董的老头,就这样走进了玉莲的生活。他对玉莲的这座砚床爱不释手,执意要收购。
这个见多识广的老头,给玉莲带来远方的消息,带来上海、广东这些遥远之地的风土人情,还给她带来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古董商人看着古宅中玉莲和丈夫年轻时的照片,随口说了一句:“他看起来还挺面善的。”
玉莲意味深长地回了一句:“面善……”
天人一别,生死两隔。吴少爷让她又爱又恨,他成全了她,又毁了她;他给了她极致的精神之爱,又毁了她极致的肉体之爱欢。
玉莲半生无法解脱,她守着埋葬阿根白骨的砚床,渡过了后半生。这是愧疚,又是赎罪。可一个人的欲望哪有罪呢?
所幸的是,古董商人成了玉莲晚年生活的唯一疗慰。他给她做了一个轮椅,推着她走出古宅,去看身边的风景;他推着轮椅,带玉莲去探望丈夫的坟墓。

古董商一走几个月,玉莲又急又担心。她自己摇着轮椅去外面探看消息,轮椅滑到,玉莲跌倒在地上——这最后要了她的命。
她至死也没等到再见古董商一面,不过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她最终和自己和解,完成了救赎,走出了心霾。
临终前知道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个人,一直在牵挂她,这难道不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最大的幸福?

这份幸福,是在岁月绝了她关于性、爱以及生育的幻想后,玉莲才领悟到的。
人一死,万事都变得不那么紧要了。吴家早已败落,也没有后代继承香火;什么名声、财富、地位,都成了过眼云烟。
一直照顾玉莲的侄媳妇,卖掉了这座砚床。这些都跟玉莲和吴少爷没有关系了。
他们曾经那么执着于一些事情、一些感情。也许直到死亡的那一刻才明白,在短暂的一生里,就应该遵从内心的欲望,享受该拥有的,不要强求没有的。

结语
这部改编自著名作家李平易的电影,不但在国内收获了“金鸡奖”两项提名,还成了新中国第一部被好莱坞购买的电影,在国际上也露了一把脸。
好的文艺作品总是切中人性,引起共鸣和深思。著名作家周国平说:
性是肉体生活,遵循快乐原则;
爱情是精神生活,遵循理想原则;
婚姻是社会生活,遵循现实原则。
在遵循现实原则的婚姻里,就包含了“传宗接代”这样的宗法观念。问题是,当性、爱和“传宗接代”的宗法观念发生冲突时,如何妥当安放这三者。
婚姻中最难的就是,如何在一个异性身上,把这三者完美地结合起来。如果发生了冲突,又该如何取舍?
《砚床》中的吴少爷和玉莲,他们拥有过完美的爱情,却没有性,导致了无法完成“生育”这一难题。

任何把这三者单独剥离出来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因为爱而有了性,因为性使爱得到了升华;而生育和繁衍,也就是所谓的“传宗接代”,只是爱和性完美结合的衍生物,是一种水到渠成的收获。
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你又期望从婚姻中获得什么呢?何为先,何为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