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论契诃夫
文丨纳博科夫
在安东·契诃夫所创造的生活的灰暗色调里,渗透着一种从容的、微妙的幽默感。在富于哲理的或关心社会的俄国批评家看来,他是独一无二的俄罗斯典型性格的独一无二的阐述者。要我来说明这种典型过去或现在究竟是什么,是一件相当困难的事,因为它和十九世纪俄罗斯总的心理与社会的历史联系得十分紧密。有人说契诃夫总爱写一些可爱而一事无成的人物,这种说法不够准确,倒是这样的说法更确切些:他笔下的男女正是因为一事无成才显得可爱。对一个俄国读者真正具有吸引力的是,他从契诃夫笔下的人物身上认出了俄罗斯知识分子、俄罗斯理想主义者的典型——一个古怪而哀婉动人的生灵——它对于外国人来说,完全是陌生的,而且在苏维埃时代,这种人即使在俄罗斯本土也不能生存。契诃夫笔下的知识分子是兼有两种特性的人:他具有人所能达到的、最深刻的尊严感,但是在实践他的理想和原则方面却无能得几乎令人发笑;他笃信道德上的美,忠于祖国人民以及全人类的福利,但是在私生活方面却连一件有益的事都做不成;他把偏狭的生活浪费在乌托邦的梦幻烟雾里;他明知什么是善,什么是有价值的生活目标,然而他却在无聊的生活泥塘里越陷越深,恋爱只会带来不幸,什么事情都休想干得好——一个做不成好事的好心人。契诃夫所有短篇小说中的人物——无论以医生、学生、乡村教师或从事其它种种职业的人物的面貌出现——统统都是这样一类人。
使他的那些具有政治头脑的批评家们烦恼的是,作者从不指明这种典型属于任何特定的政党,也从不给他以任何特定的政治纲领。然而,问题的关键就在这里。契诃夫笔下那些无能的理想主义者既不是恐怖主义者,又不是社会民主党人,也不是初露头角的布尔什维克。他不是俄国无数革命政党的无数成员中的一个。重要的是,这种典型的、契诃夫式的主人公是一种模糊而美丽的人类真理的担负者,不幸的是,他对于这个重负既卸不下又担不动。在契诃夫所有的短篇小说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种连续不断的颠踬,那是一个人因凝视星空而导致的颠踬。他是一个不幸的人,并且他还使别人不幸,他不爱他的兄弟,不爱最接近他的人们,却爱离他最遥远的人们。遐方绝域的黑人、中国的苦力、乌拉尔山僻处的劳工,这些人们的困境比他邻人的不幸和他妻子的烦恼更使他强烈地感到一种道义上的痛苦。契诃夫怀着艺术家的特殊兴趣将大战前和革命前俄罗斯知识分子典型中的各种细致、微妙的类别加以区分。那些人会梦想,但他们不会治理。他们破坏了自己以及别人的生活,他们愚蠢、软弱、无能、歇斯底里;然而,契诃夫暗示说,能够产生出这种特殊类型人物来的国家是幸运的。他们错过时机,他们逃避行动,他们为设计他们无法建成的理想世界而彻夜不寐;然而,世间确实存在这样一种人,他们充满着如此丰富的热情、强烈的自我克制、纯洁的心灵和崇高的道德,他们曾经存活过,也许在今天冷酷而污浊的俄罗斯的某个地方,他们仍然存在,仅仅这么一件事实就是整个世界将会有好事情出现的预兆——因为,美妙的自然法则之所以绝妙,也许正在于最软弱的人得以幸存。
正是从这一观点出发,那些对俄国人民的痛苦和俄国文学的光荣同样感兴趣的人们才欣赏契诃夫。尽管契诃夫从来不想为人们提供一种社会的、道德的教训,然而他的天才却几乎在不经意之间就揭露了那充满饥饿、前途茫茫、遭受奴役、满腔愤怒的农民的俄罗斯最黑暗的现实,而这种揭露要比那些凭借一系列着色傀儡来炫耀其社会见解的诸如高尔基那样的许多其他作家的揭露更为充分。我还要进一步说,爱陀思妥耶夫斯基或高尔基甚于爱契诃夫的人永远也不能掌握俄罗斯文学和俄罗斯生活的本质,而且,远为重要的是,他们永远不能掌握普遍的文学艺术的本质。在俄国人中间,常把自己的熟人按其是否喜爱契诃夫而分成两类,这几乎已成为一种有趣的游戏了。那些不喜爱契诃夫的人们绝不属于公正的一类。

我诚心诚意的建议诸位尽可能经常地拿出契诃夫的书来读读(即使经过翻译走了样也不要紧),并按照作者的意图陷入遐想。在一个到处是茁壮的歌利亚们的时代,读一读有关柔弱的大卫们的书是非常有用的。凄清的景色、排列在荒凉、泥泞的土路旁的枯萎的柳树、在阴沉的天空中鼓动着翅膀的黑乌鸦、在一个平常的角落里突然翕动起某种令人惊异的回忆——这一切勾人心魂的朦胧、这一切美丽动人的柔弱、这整个契诃夫式的鸽灰色的世界在极权国家崇拜者们许诺给我们的那个强壮、自负的世界的炫示下都是值得珍爱的。
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带叭儿狗的女人》(1899),写来直截了当,开门见山,没有丝毫拖沓之处。主要人物——一位金发少妇——在起首第一段就带着一只白色的丝毛狗出现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休养地雅尔达的一处海滩上。紧接着又出现了男主人公古洛夫。他那和孩子们一起留在莫斯科的妻子被描绘得很生动:结实的身躯,浓黑的眉毛,老爱说自己是个“会思考的女人”。你会注意到作者收集琐事细故的奇妙本领——这位妻子写字时总爱把不发音的字母省略掉,但在称呼丈夫时却总爱用最冗长、最详尽的全名,这两项性格特征与她皱眉蹙额的脸上那种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庄严以及僵硬、刻板的姿态结合在一起恰好形成所需要的印象。她是一个生性冷酷的女人,具有她那个时代强烈的女权思想和社会意识,但是在她丈夫的内心深处却认为她胸襟褊狭,头脑愚笨,缺乏优雅的风度。事情自然发展道古洛夫不断地对她不忠实,影响他对妇女的总的态度,他把妇女称为“劣等人种”,可是离了这劣等人种他就活不下去。它暗示着这类俄罗斯式的浪漫史全然不象莫泊桑笔下发生在巴黎的浪漫史那样轻快。对于莫斯科那些体面而犹豫不决的人们说来,麻烦和问题总是不可避免的。这些人开始行动时缓慢、迟钝,但一旦行动起来就陷入无尽的困境。
然后,小说以开头那种简洁、直截了当的手法,用套语“于是……”来连接,使我们不知不觉地重新回到那位带狗的夫人身边。她身上的一切,包括头发的式样,都向他说明,她心里烦闷。一种冒险的精神——虽然他明明知道,他对上等人聚居的海滨休养地的一位单身女人采取这种态度,是在效法那些往往是瞎编出来的通俗小说——这种冒险精神还是激励他去逗引那只小狗,而这一行动就成了他向这位女人搭话的因由。当时他俩正在同一家公共餐厅里。
他打手势逗引那只丝毛狗,等它走到他面前时,又向它摇动手指。丝毛狗嗥叫起来;他又一次恫吓它。
那位夫人瞥了他一眼,目光立即垂了下来。
“它不咬人。”她说,脸红了。
“我可以给它一块肉骨头吃吗?”他问;当她点了点头时,他又用亲切的语气问,“您到雅尔达已经很久了吗?”
“大约五天。”
他们交谈起来。作者早就暗示说古洛夫在女性面前是很机智的;然而,出乎读者的意料(你知道,若按老的手法就会形容这场谈话“才气横溢”,但又拿不出实例来),契诃夫却让古洛夫以可爱、动人的方式开起了玩笑。“您觉得沉闷吗?一个住在……(契诃夫在这里列举出几个选择得极妙的、土气十足的城镇名)的普通老百姓倒不觉得那里沉闷,但他一旦到这里来度假,就会觉得这儿气氛沉闷、满是尘土了。人家还当他是从格林纳达来的呢”(这个地名特别能激发俄国人的想象力)。这些话足以从侧面将他们谈话的其余部分间接地反映出来了。这里初次闪现初契诃夫用最简明地对自然景色的细节描写渲染气氛的独特方法,“大海呈现出温暖的浅紫色,在月亮升起的地方有一道金色的光带”;凡是在雅尔达住过的人都会知道这句话把那里夏季夜晚的印象表达得何等真切。小说第一部分结尾处,古洛夫上床睡觉时独自在旅馆房间里思念着她,想起她那娇柔、细弱的颈项和她美丽的灰眼睛。值得注意的是,直到此刻,通过主人公想象的媒介,契诃夫才给那位夫人画下一幅鲜明、确切的图象,她的相貌与我们早就知道的、她倦怠的举止和烦闷的神情十分切合。
躺下睡觉时,他想:不久前她还是一个女学生,就象他女儿一样做功课;他回想起她和生人谈话时,那笑声和举止仍显得羞怯和生硬。她独自置身于这样一个环境,准还是平生第一次,在这里,人们跟踪她,盯着看她,和她搭话,隐藏的目的只有一个,对此,她不会猜不出来。他想她那纤细、精致的前颈和她那可爱的灰眼睛。
“然而,她身上有一种招人怜爱的模样呢。”他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小说第二部分(全篇分成四个小型的章节或部分,每一部分不超过四至五页)的开始是一周后的某个炎热的、尘土飞扬的刮风天,古洛夫从商亭里为那位夫人买回了冰镇柠檬水;傍晚时西洛可风渐渐平息,他俩走在防波堤上,瞭望着蒸汽船驶进港来。“这位夫人在人群里挤丢了她的长柄望远镜”,契诃夫简短地交代了一句,说来如此漫不经心,对故事没有任何直接影响——只是偶然提了提——但不知怎么的,它恰好符合小说早就暗示出来的那种不能自己的、使人凄恻的情调。
接着在她旅馆房间里的一段,细致地传达出她举动的拙涩以及带着女性温柔的局促不安。他们成了情人。现在,她坐在那里,长发在她脸庞两边披拂下来,显出某幅旧画中犯罪女子那种心灰意懒的模样。桌上摆着一只西瓜。古洛夫给自己切下一块,慢慢地吃起来。这一现实主义笔触又是典型的、契诃夫式的独创。
她向他叙述她来自的那个偏僻城镇上的生活,而古洛夫却对她的天真、慌乱和眼泪有点腻烦了。直到此刻,我们才知道她丈夫的姓氏:封·蒂德里兹——或许是德国人的后裔。
他俩在晨雾中沿着雅尔达四周漫步。
在奥列安达,他俩坐在离教堂不远处的一张长凳上,低头望着大海,沉默不语。透过晨雾,仅可望见雅尔达朦胧的影子;白云静静地停在山顶上。树上的叶子悄然不动,蟋蟀在唧唧地叫,从低处升起大海单调而低沉的声音,诉说着和平以及等待着我们的永恒的睡眠。当这里还没有雅尔达、没有奥列安达时,它就已经在低处这样响了;现在它响着,到我们不复存在时,它仍将发出如此淡漠、空洞的声音……这位少妇在黎明时分看来如此可爱,古洛夫坐在她身边,周围奇妙的景物——海洋、大山、云朵、辽阔的天空——给他慰藉,使他心醉,他想,只要你认真思考一下,世间的一切,除了当我们忘却人生更高的目标以及我们做人的尊严时所想和所做的事情以外,都是真正美丽的。
一个男人踱到了他们身边——也许是个看守人——朝他们看了看就走开了。这件小事似乎也非常神秘和美丽。他们望见一艘从费奥多西亚开来的蒸汽船,船上的灯火在黎明的霞光里熄灭。
“草上有露水。”沉默了一阵,安娜·谢尔盖耶夫娜说。
“是的,是该回去的时候了。”
几天以后,她不得不回家去了。
“我也应该回北方去了。”送她动身后,古洛夫想。
这一章节就到此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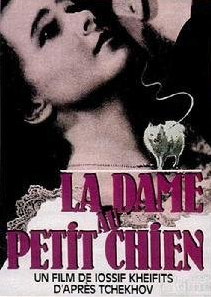
第三部分把我们直接带进古洛夫在莫斯科的生活中去。一个欢快的俄罗斯冬季的丰富生活、他的家事、在俱乐部和饭店里进餐……这一切都迅速而生动地暗示出来。接着用一页篇幅描写了发生在他身上的一件怪事:他无法把那位带小狗的夫人忘怀。他有许多朋友,他怀着一种奇特的渴望,想向别人讲述他那桩冒险奇遇,然而找不到一个倾吐的机会。当他碰巧非常笼统地谈到爱情和女人时,谁也猜不出他的用意何在,只有他妻子的黑眉毛动了动,说:“别说那种蠢话了,这可不是你应该说的。”
接着进入了在契诃夫含蓄、平静的小说里可称为高潮的地方。这里有普通人称为浪漫史的东西以及契诃夫称为散文的东西——然而这两者在艺术家手里实质上都是诗。这种明显的差异早已由古洛夫在雅尔达旅馆房间里吃的那块西瓜暗示出来了。在那个最富于浪漫色彩的时刻,他闷坐着,大声地把那块西瓜嚼了下去。这种差异出色地趁机发展下去,一天深夜,当古洛夫和一位朋友一起走出俱乐部时,他终于不假思索地冲口说了出来:你不知道我在雅尔达遇到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人!他的朋友——政府里的文职人员——坐上了雪橇,马拉着它往前跑,但他突然扭过头来喊古洛夫。怎么啦?古洛夫问,显然在盼望他能对自己刚才提到的事作出某种反映。顺便提一句,那个人说,你说得很对。俱乐部里的鱼肯定臭了。
这是一个自然的转折,下面就描写古洛夫的一种新的心境了。他感到自己生活在一群嗜赌、贪吃如命的野蛮人中间。他的家庭、他的银行、他生活的整个倾向似乎都没有价值,沉闷而无聊。圣诞节前后,他对妻子说要到圣彼得堡去办件公事,其实他动身到那位夫人所在的伏尔加河畔那座偏僻城镇去了。
在往昔的时代里,公民问题的狂热正席卷俄国,契诃夫的批评家往往被他的描写方式所激怒,当时,他们认为契诃夫描写的是琐细、无用的事物,而没有透彻地考察并解决资产阶级婚姻的问题。因为,当古洛夫清晨一到那座城镇并在当地旅馆租下最好的房间时,契诃夫并不描写他的心境,也不去着意渲染他在道德地位上的困难,却提供了真正富于艺术性的描写:他特别提到用军用毛料做的灰色地毯、积满灰尘因而也呈现出灰色的墨水台,那上边有一个骑马人像,骑士的手中挥舞着一顶帽子,可是脑袋却没了。就这些,似乎什么都没有,但真正的文学所要具备的一切这里都有了。还有一个同样性质的特写:旅馆茶房把德国姓封·蒂德里兹硬是读别了。古洛夫打听到了住址就到那里去看那座房子。房子对面有一道长长的、装着尖刺的灰色栅栏。一道不可逾越的栅栏,古洛夫自言自语道。在这里,我们对生活节奏的单调和灰色——这些,我们早就从地毯、墨水台和旅馆茶房缺乏教养的发音中受到了暗示——得到了总结性的音调。正是那意外的微小波折、轻巧精美的笔触使契诃夫能与果戈里和托尔斯泰肩并肩地在所有俄国小说家中占据最高的位置。
不久,他看见一个老仆人带着那只他熟悉的小白狗走出门来。他想喊那只狗(出于某种条件反射),但他的心突然跳得激烈起来,在兴奋中他竟忘掉了它的名字——又一个巧妙的笔触。后来,他决定到当地剧院去看戏,那里将初次上演小歌剧《盖伊霞》。契诃夫只用了六十个词就提供了一幅外省剧院的完整图画,就连谦虚地躲在他包厢的长毛绒帷幔后面,因而只能看见他的两只手的那位市长也没有漏掉。接着,那位夫人出现了。他分明意识到,对他说来,如今整个世界上再也没有比这个混在小城的人群里、手拿一架普通的长柄望远镜、似乎毫无出众之处的小女人更近、更亲、更重要的人了。他看到了她的丈夫,记得她曾把他称为奴才——他还真象个奴才。
以下是一个绝妙的场景,描写古洛夫设法和她谈话,两人在穿着各式外省官员制服的人群中,以疯狂而迅捷的脚步穿过各种楼梯和走廊,上楼、下楼、再上楼。契诃夫没有忘掉“楼梯上方有两个在抽烟的中学生正俯视着他俩”。
“你得走,”安娜·谢尔盖耶夫娜悄声说,“听见了吗,德米特里奇?我会到莫斯科来看你的。我一直没有快活过;现在我也不会快活,并且我永远、永远也不会再快活了,永远不会!所以,不要使我更加痛苦了吧!我发誓我会到莫斯科来的。但是,现在我们还是分手吧。我亲爱的好宝贝,让我们分手吧。”
她握了握他的手,快步走下楼去,又回头看看他,从她的眼神里,他可以看出她真的不快活。古洛夫站立片刻,倾听着,当一切都安静下来,他就找到大衣,离开了剧院。

短短的第四章,也就是最后一个章节,写出了他俩在莫斯科幽会的气氛。她一到那里总是立即派遣一名带红帽子的信差去通知古洛夫。有一天,他去和她幽会,他女儿和他一起走着。她去上学,正好和他同路。大片大片的湿雪正缓缓地降落下来。
古洛夫对他女儿说,气温表上指着零上几度(准确地说是华氏三十七度以上),然而却下起雪来了。这说明表上的温度只适用于地球表面,而高层大气的温度就大不相同了。
他边说边走,心想:没人知道他们的幽会,也许将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使他困惑的是,他生活中所有虚假的部分:他的银行、他的俱乐部、他的谈论、他的社会责任——这一切都是公开的,然而他生活中那真实、有趣的部分却是隐蔽着的。
他有两种生活:一种是公开的,任何想了解它的人都可以看见并了解它,其中充满传统的真实和传统的虚假,与他朋友们和熟人们的生活一模一样;而另一种生活是在暗中进行的。通过某些奇怪的、也许是偶然的机缘,一切他认为有趣而重要的东西、一切他认为必不可少的东西、一切他认为真诚地感觉着而并不自欺的东西、一切组成他生活核心的东西,都是瞒过别人而暗中进行的;而一切虚假的东西却是他用来掩盖自己、遮蔽真相的外壳——例如,他在银行里的工作、他在俱乐部里的议论、他关于“劣等人种”的论调、他同妻子在纪念会上的出现——这一切都是公开进行的。推己及人,他再也不能相信自己所看见的东西了,他总在猜想:一切人都在夜一般漆黑的秘密的掩盖下,过着自己真实的、最有趣的生活。每一个人的私生活都以秘密为基础,文明人如此敏感地渴望着个人秘密能得到尊重,部分原因也许正在于此。
最后一个场景中充满小说开始时即已暗示出来的那种使人凄恻的情调。他们相会,她啜泣,他们觉得他俩是一对最恩爱的夫妻,最亲近的朋友,他看到自己的头发开始灰白了并且意识到只有死亡才能结束他们的爱情。
他双手按着她温暖而颤抖的肩膀。他对这个依然如此温暖而可爱的生命感到怜惜,也许这个生命正象他的生命一样也早已开始凋谢和枯萎了。她为什么要把他爱得这样深呢?在女人眼里,他似乎总和他的本来面目不同,她们所爱的他不是他本人,而是她们在想象中创造出来、并热切地寻找了一辈子的男人;而当她们最后发现自己的错误时,却仍然爱他。她们中没有一个人能因他而得到幸福。过去他曾与一些女人遇合和分离,但他从来未曾爱过;随你怎么说都行,但那决不是爱情。直到此刻,当他的头发已经灰白,他才平生第一次实实在在、真心真意地爱上了一个女人。
他们商议,他们讨论他们的处境,怎样才能摆脱这种不得不然的鬼鬼祟祟,怎样才能永远在一起。他们想不出解决办法,小说没有明确的终结,而是按照生活的自然运动、以典型的契诃夫方式渐渐消隐。
似乎再过一会儿就能找到解决办法了,然后将开始过一种新鲜而灿烂的生活;他俩都明白结局还远得很,对他们说来,那最复杂、最困难的事情还刚刚开始。
在这个只有二十页左右的短篇小说里,一切传统的小说写法都被打破了。小说没有提出什么问题,没有通常的高潮,也没有一个有意义的结尾。然而这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短篇小说之一。

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 — 1977年7月2日),俄裔美籍作家,1899年出生于俄罗斯圣彼得堡。纳博科夫在1955年所写的《洛丽塔》,是在二十世纪受到关注并且获得极大荣誉的一部小说。作者再于1962年发表英文小说《微暗的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