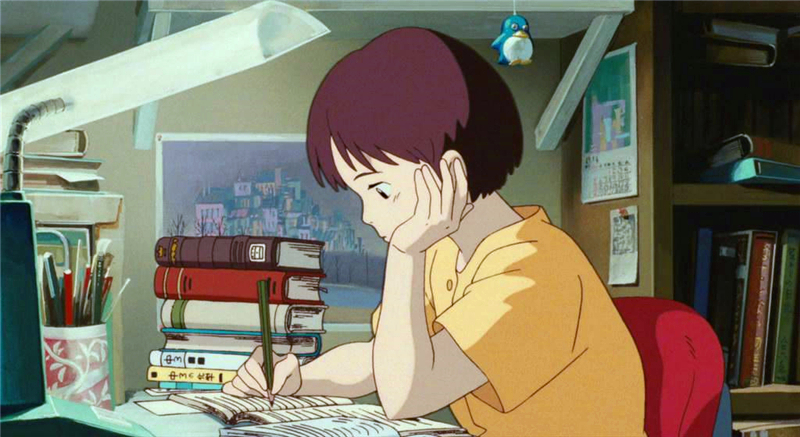
从我幼年时一直到长大离开家上大学,甚至在那之后,我舅舅迈克的小提琴一直被视为家中的珍宝。它已成为某种象征。
我还记得迈克舅舅第一次让我瞧他那把小提琴。他打开陈旧的黑盒子,里面衬垫着鲜艳华丽的绿天鹅绒,那把琴静静地平卧其中。“现在你可看见了一把出自名匠的古琴。”他语调庄重地告诉我,并且让我透过琴面的f形音孔观看里面褪了色的标记。是他父亲给了他这把琴,追根溯源,琴是一位先辈从意大利带来的。
我父亲是一位面包师傅,在爱塞克斯大街新开辟的铺面是他从事的一桩最大的冒险事业。下面打算作为面包房,背面将辟为冷饮室,里面的桌子都是大理石贴面。当父亲头一次告诉母亲这个计划时,他心里异常兴奋。
“我告诉你,玛丽,根本不会有危险,”看见母亲脸色不对头,父亲说道,“你只要在这份三千美元的借贷申请书上签个名就行了。”
“可如果是抵押贷款,”她呜咽地说道,“他们可以把我们一家子撵到街上,我们要成为叫花子的,卡尔。”
“我想稍微讲几句。”舅舅说。他站起来从陈列柜顶上取下那把小提琴,“我从报上读过,一把斯特拉·第瓦里制造的小提琴卖了五千元。把它拿去卖了,卡尔。”
“哦,迈克!”母亲很吃惊。
“我可不愿那么做,迈克。”父亲说道。
“如果你赶快的话,”迈克舅舅告诉他,“你可以在老埃雷特关店之前赶到他那里。”他的双手微微颤抖,可他的语调却异常平静。于是我父亲腋下夹着提琴盒出门了。
过了一阵子父亲从前门进来,他吹着口哨,脚步轻捷,可是仍然夹着那只提琴盒。他做的头一件事便是将琴盒放回到陈列柜顶上的老地方。
“我都已经走到埃雷特那家店的门口了,可我心里突然起了个念头,”父亲解释道,“我们干吗要卖它?就放在老地方不挺好的吗?这就像我们有了一只保险箱,里面放着崭新的五十张一百元面额的票子。有了这笔钱,我们就用不着为那笔三千元的贷款担惊受怕了。你说是吗,玛丽?如果我们要还的话,只消穿过三条马路到埃雷特那家店去就行了。”
母亲显出欣喜的表情:“我很高兴,卡尔。”
“一个很明智的主意,”迈克舅舅裁决道,“另外,我自愿把这把琴留给小玛丽,供她在大学里念书的费用。”
那笔贷款并没有给家里造成麻烦。我进中学后,上午上课,下午就在店里帮忙。
在我即将上大学的那年夏天,迈克舅舅溘然长逝,于是他的小提琴便传给了我。
“他们难道没有让你们勤工俭学的方案吗?”一天晚上,父亲问我。
我告诉他确实有。
“我想那样最好。”他突然说道,“我在你衣柜的抽屉里放了一个信封,里面有两百元,应该够缴你开始的那些费用了。你母亲可是就指望那把小提琴的。”
母亲确实是这样。不过她不再忧心忡忡,这把琴已经属于我了。
在我离家的头一天,父母都在店里忙着,我提着这把琴来到埃雷特的乐器店。这位老人从后房走出来,眼睛像猫头鹰般一眨一眨。
我打开琴盒:“它值多少钱?”
他拿起琴来:“卖二十五元,也许能卖到五十元,这就要看谁愿意要它了。”
“可这是一把斯特拉·第瓦里制造的小提琴呀。”我说。
“不错,这上面确实有他的标记,”他彬彬有礼地说道,“许多小提琴上都有这种标记,可并不是真的,这也绝不会是真的。”他好奇地凝视着我,“我以前见过这件乐器,你是不是卡尔·恩格勒的女儿?”
“是的。”我简短地回答道。当然,这把琴我没有卖掉,我把它带回家,放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去了。
在我离家前最后那次晚餐席上,母亲偶然朝陈列柜顶上瞟了一眼。“琴呢?”她问道,一面把手贴在自己胸口,“你们把它卖了?”
父亲显得很忧虑,直到我摇摇头。“在楼上我的衣箱里,”我告诉她,“我想把它放到学校我的房间里,平时看到它就使我想到自己的家。”
母亲高兴起来,显得很满意。“此外,”我继续说道,“那样的话,如果发生了什么事我需要钱用,你们就用不着为我担心了。这就像我拥有了一个装得满满的钱匣子,是这样吗,爸爸?”
“是这样,玛丽,是这样的。”父亲一面回答,一面避开了我的目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