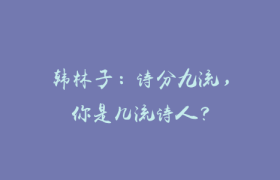中国新诗的发展,在改革开放的初年,出现了一次大的变动。在小宋佳和朱亚文主演的小众电影《诗人》里,希望改变命运的新诗诗人在荒漠戈壁上徘徊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勾画出爱情和艺术所特有的失落之美。
事实上,文学本身的发展远比影视作品和文学史来的充满激荡。
而就在这戈壁滩上,在影片主要拍摄地的石河子地区,四十余年前,带着诗歌气息的浪潮也同样在这里吹起烈风,并正式开启一个属于新诗的时代。在那个混沌初开,崇尚文学的八十年代里,这里出现的一本刊物,即将风靡全国。
时隔多年,创作新诗的人们将之称为“《绿风》时代”。

作为与《诗刊》和《星星》并成为“当代中国有较深远影响的三家诗刊之一”的《绿风》(《人民日报》的评价),其发展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1978年的《石河子文艺》。
七十年代末的新疆,是大批文人墨客的心灵牧场,由于政治和时代的特殊背景,以艾青为代表的一大批诗人被下放到新疆劳动,而石河子,在当时有着“诗窝子”的美誉,无形之中,这片沙漠里的绿洲成为了新时代诗歌的摇篮。
最早的《绿风》,正是在这种大环境下成立的,作为一本“刊中刊”,附带在《石河子文艺》的后面(之后该杂志改名为《绿洲》),在发刊词中,它这样介绍自己:
“《绿风》诗卷’是《绿洲》的一个刊中刊,既有全刊的统一性,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它不拘泥于某一种主张,也不专注某一种流派;只要有绿色的生命力,它就给予应有的位置。它的任务是探索,它的职责是催化……”,这种海纳百川的风格,在后来的《绿风》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
而《绿风》真正迎来自己的时代,则要等到1983年那场著名的“绿风诗会”。
那一年的九月初,在艾青的号召下,半个诗坛都跑来了石河子,上百位诗人云集于石河子,召开了这次“绿风诗会”,参与这次盛会的,有时任作协副主席的铁依浦江,有担任《诗刊》主编邹荻帆,以及后来担任《上海文学》社长的赵丽宏等等。

后来在重新给新的刊物起名字的时候,由于其中许多人都在西北感受过一段极其艰难的岁月,沙漠中的人对“绿”有一种特殊的偏爱,上百人七嘴八舌,起的名字大都带有一个“绿”字。正如艾青在诗歌《绿》中写的那样:
好像绿色的墨水瓶倒翻了
到处是绿的——
到哪儿去找这么多的绿:
……
刮的风是绿的,
下的雨是绿的,
流的水是绿的,
阳光也是绿的;
所有的绿集中起来,挤在一起。
最终,作为主编的杨牧在这首诗歌中找到了灵感,后来感慨道:“绿风之首创还真是那个老艾青呢”,刊物的名字于是被定为了《绿风》,并在次年1月正式发布,刊物的名字也由艾青题写,“绿风创新风”的字样至今能在刊物上看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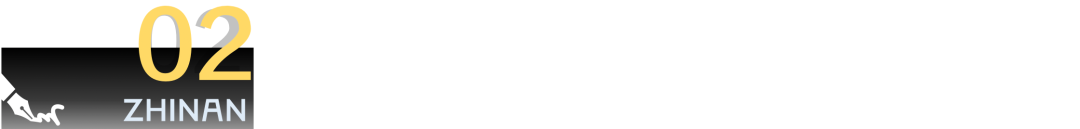
《绿风》最后决定采用双月刊的形式发行,这无疑与那个诗歌井喷般爆发的时代有关系,在整个1984年,《绿风》都处在一种摸索的状态下———新的独立的编辑、新的排版、新的定位—甚至连页面大小为32开都是那一年所确定的。
因此在1985年初,兴奋的主编杨牧在卷首语中写下了这样的话:“西部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家诗刊,开拓者故乡壮阔激越的绿色交响,国内中青年的荟萃园地”,并明确提出,“《绿风》不搞老气、粉气、小家子气”。
这种精气神在刊物栏目和内容的设置上也体现得非常明显。
早在八十年代末期,《绿风》就开辟了一个专门的栏目,名字很长,叫《国内群众性青年诗歌社团览胜》,简单来说,就是介绍中国当时大大小小多如牛毛的众多诗歌团体,这在当时来说,具有很强的风潮引导能力。
在这种风潮的带领下,《绿风》如同西部沙漠中难得一见的绿洲,呈现出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与之前的《绿洲》并驾齐驱,成为了新疆建设兵团的两大代表性刊物。

从《中国诗歌年鉴》所入选的诗歌书目来看,在许多年份中,《绿风》甚至要压过《诗刊》和《星星》一头,并列榜首。舒婷、顾城、梁小斌、西川等一系列的诗人都在那个时代的《绿风》诗刊上留下了自己的大作。
而与此同时,《绿风》还凭借其地域特色,开创了名震一时的“新边塞派”。新疆建设兵团特殊的时代印记和新疆边塞独有的时光,造就了昌耀、杨牧、周涛、章德益等一批“新边塞诗人”。
北大中文系的谢冕教授在提到这一新的流派时认为:“时代和政体的改变……必然地带来了这种被称之为新边塞诗的内在的质的变化,这就是新边塞诗之所以‘新’的原因,并不单是由于它是今人写的”。
从某个角度来说,中国的现代文学史,不应该忘记绿风,正如我们不应该忘记那个充斥着诗歌和想象的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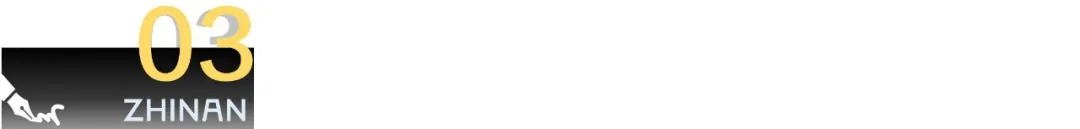
我们回忆文学刊物的意义,往往在于它们作为一种载体,可以承担一些独属于某个时代的记忆,《绿风》毫无疑问也担当了这个责任。
在“朦胧诗派”方兴未艾的八十年代,《绿风》曾经站在了一个风口浪尖上。
八十年代初期,诗歌的国度在悄然交替着,老一辈的诗人,如臧克家、艾青、卞之琳等人,依旧活跃在诗坛上。但在时代的另一个角落中,以舒婷、北岛等人为代表的“朦胧诗派”也在悄然崛起。
在最早一批发表“朦胧诗派”作品的诗刊中,就有《绿风》的存在。
从舒婷的《镌在底座上》、《神女峰》和《小诗赠友》(三首),到傅天琳的《你微笑着》和《半枝莲》,再到杨炼的《绿·红》(二首)、顾城的《那条小路》,无数的“朦胧诗歌”,《绿风》成为了众矢之的。

诗人芒克、北岛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在那个年代,“朦胧诗派”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词语。
以至于《绿风》不得不打出“抒情诗”的口号,为这些“朦胧诗派”打掩护,如舒婷的那首著名的《神女峰》,正是打着“抒情诗”的名义在《绿风》上发表的:
是谁的手突然收回
紧紧捂住了自己的眼睛
当人们四散而去,谁
还站在船尾
……
但即便如此,也难敌大趋势下对“朦胧诗派”的封杀,作为《绿风》老朋友的艾青就曾怒斥“朦胧诗派”,认为它们是“否定现实主义的传统,搞精神污染,早晚会被时代所唾弃”,在种种巨大的压力下,《绿风》不得不停止对“朦胧诗”的刊载,这也成为了当代文学史的一桩公案。
是是非非如何,如今已不重要,“朦胧诗派”的作品和那些老派诗人一同闪耀在语文课本中,依然说明了一切,在《绿风》上的挣扎,也成为了诗歌在那个年代发展的一种见证。

即使从1984正式独立算起,《绿风》也已然在西陲地区,走过了近四十个年头,一如顾城在诗词中写的那样:
“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在不知不觉间,诗人和诗刊都依然行将老去。
恍惚中还是八十年代戈壁滩上的风,但转眼间,那个以诗成名的时代竟然已经过去了这么久。

《绿风》已然存在,只是物是人非,当年的编辑,大多都已不在,当初的作者,也已渐渐封笔。世界开始逐渐遗忘了新诗,正如我们逐渐忘记了那个仗剑走天下的浪漫时代。
《绿风》的“无可奈何花落去”,也许只是当今的一面镜子,诗歌这种纯文学形式的小众化,是否也象征着当今的我们,已经不再“文艺”了呢?
但也许正如杨牧在离开《绿风》后所说的那样“《绿风》不垄断一个时代,《绿风》却折射着一个时代”。
让我们也期待着下一个“绿风时代”,亦或是“诗歌时代”的到来。
作者丨翟晨旭
投稿指南©️原创首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