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纪录电影《爱我长城》正在热播,记录了老红军及其感召下几代人进行长城保护故事,是一部反映传承保护长城文化的精品力作。
长城是读懂中华文明的一把钥匙,中国人不能不懂长城。
正巧,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看到周涛的散文集《游牧长城》,再一次带我走进历史,了解长城。
知道诗人兼散文家周涛的名字,是因几年前一文友的推介。他的散文,没有春花秋月的小情调,有的是大气磅礴,带着哲理性思考,有诗的特质。正是我喜欢的散文的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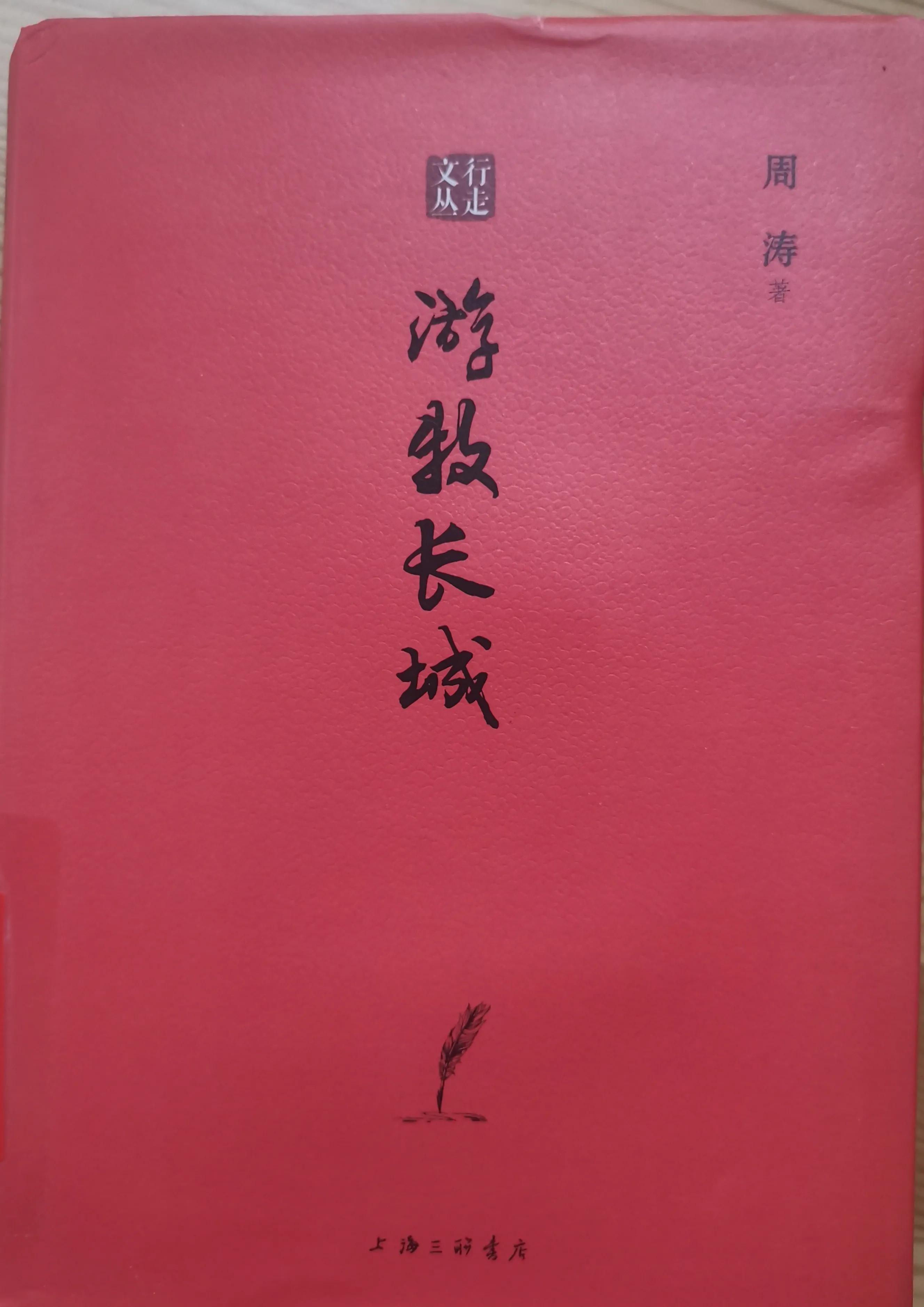
作者在《后记》中说,这本书的诞生,是因与几位朋友半年辛苦奔波,跑遍了甘肃、陕北、山西等省份,被长城的神秘力量深深触动。
长城与黄河是这样一类东西,无文字的文化,无课本的教育,像婴儿吮吸第一口奶汁一样,渗透到我们的生命和血液。
对我们中国人的影响比宗教的感染力更沉重,比父亲的慈爱更广阔,比所有的古人哲人学说加起来更雄厚。
长城是一条凝固的黄河;
黄河是一道流动的长城。
长城是把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分隔开的一道界限。长城是伟大的墙。也是一部史记。是镰刀和马蹄共同创造了它。
一
短文《黄河母亲》发出深省的疑问:黄河母亲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
在后工业时代,兰州已经成为一座化学城,上空黄云汹涌澎湃,形成一朵空中黄河。黄河远上白云间竟然成了现实主义预言,而真正的黄河干涸与营养不良。
在现代雕塑家眼里,黄河母亲是圆满的,安于现状的,幸福的样子。
然而从历史走来,万里长风吹过,她是一个褴褛、干瘪的老妇。她粗糙畸形,血管筋脉突现,紧闭的纹路倔强的嘴,还有哀伤的眼睛和眼角善良的皱纹。
在《那个人究竟想了些什么》一文中,一个西德人问:当时修长城的那个人究竟想些什么?面对这个德国人的疑问,怎能不警醒肃然呢?这样的民族怎么能不是强盛的、生机勃勃的呢?
当时修长城的那个人就是秦始皇,这位统一中国的第一位帝王,长城就是他想象力的极限。
使长城一次次失去防御意义的,是北方游牧民族的马蹄,使残缺的长城一次次重新站立起来的,是中原农耕民族的双手。
一名教授告知有关长城的知识,突然拐个弯?与水源有关。经过的地方松树都活而白杨树不活。
长城之所以能够超越了一座土垒城更垣的意义,长城之所以远远高于墙的意义,就在于它是古代中国的一部总结,因而必是未来中国的一个预言。
什么原因,什么心理,使古币收藏家对这些一般人眼里的破铜烂铁,形状怪异的石头,贝壳,小孩子踢毽子的垫底,显出如此的迷醉和嗜好呢?
古币,同一个朝代的,不同朝代的,碰在一起,他们偶然间互相碰撞,发出彼此问候似的清脆声响。更多的时候,是默默相望,仿佛在辨识对方身上的古怪胎记。
他们的名字都叫钱,货币家族里的成员。有些看起来最弱的是年长的,这些浑圆硬朗的是年幼的。收藏家可以说是另一种历史学家。
见到了许许多多的城墙,却没有见到修城墙的人。修城墙的人到哪里去了?翻遍历史书,也找不到他们的名字。历史是他们创造的,然而,历史却不记载创造了历史的人。
历来对长城,中华民族都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夸耀的赞歌,一种是凄凉的哀唱。
当地球引力保证全人类都能站立在地球表面,而不被风刮走的时候是什么?保证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无数次分裂而又重新聚合呢?
长城引力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二引力。
长城是一张绷架在中国大地上的万里巨弓。民族分分合合,历史最悠久,人种最复杂,民族最众多,但却数千年聚而不散,几百代争而不灭,是因为这种万里巨弓。
长城,还是中国北方商业精神的起跑线,古代丝绸之路的坐标。
长城不是诗,而是墙。历代诗人敢写月亮,敢写大江,敢写黄河,却没有人用他的笔墨去涂抹长城。长城是在许多朝代用一块一块的砖垒彻成的,旧的砖坍塌了,又补上新的。长城是无法表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