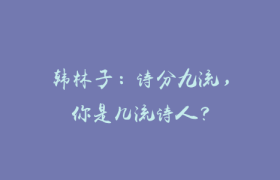小编按:中国文化界的主流话语由文言变白话已近百年,若以胡适发表在1917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杂志第2卷上的白话诗《蝴蝶》为计,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整整九十年的历程。在我们这个充满“诗教”的国度,一种新语言的诞生必然会伴随着各种质疑、猜忌和不信任。可以说,过去的一百年是“新诗”饱受争议的一百年:一方面是来自诗歌内部的纷争,一方面是来自诗歌外部的攻讦,两方面在相互撕扯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合力,使得“新诗”前进的每一步都举步维艰。百年过去了,“在争论中求生存”才是中国“新诗”走向辉煌的正道。

魏天无,1967年3月生于湖北荆门,祖籍河北饶阳。1988年本科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文学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华中学术》副主编,兼任湖北文学理论与批评研究中心、华中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美国孟菲斯大学(UM)交换学者(2012—2013)。出版专著(合著)四部,发表论文、评论、随笔百余篇。
失败是诗人的宿命
魏天无
我们今天的诗人真是脆弱到了令人不解的地步,一听有人说新诗失败了,就跳将起来,仿佛人家正指着自己的鼻子,或者无端抢走了自己的饭碗一样。
在我看来,失败是诗歌、尤其是现代诗歌的宿命。它首先表现为盘踞在诗人——哪怕是我们心目中的最伟大的天才诗人——内心的那种颓败感。1945年7月20日,法国诗人瓦雷里与世长辞,临终前他用铅笔写下这样的话:
机运,伴随这个憎恶它们的人的机运都是错的,更糟糕的是,都是些坏趣味,简单、庸俗的机运。
他曾经不遗余力地倡导和追求“纯诗”,但是,当他不得不承认“在诗歌中,一切必须表达的几乎都是不可能很好地表达的”,因此,不存在“纯诗”而只存在“纯诗的片断”的时候,他必定不会认为自己是一位成功的诗人;他或许并不关心他身后所能获得的评价,但却不能不担忧后人对于他如此执著的探索能否给予理解和体察。
事实上,一位真正的诗人,正是抱定了失败的信念而又视失败为无物的人。正如瓦雷里对他的导师马拉美一生所作的评价那样:
他根本的追求一定是为了定义和制造最精妙和最完善的美。……从这里开始他远离了其他诗人……同时,他也远离了绝大多数,也就是说远离了唾手可得的荣誉和好处;他朝着独自一人喜欢的东西走去。他轻蔑也受到轻蔑。他使自己精心写作的东西免受潮流的变化和时事变迁的影响,这种感觉令他欣慰。他思想的产物是荣耀的:它们美妙而且坚不可摧。
而马拉美身前就已清醒地意识到:“在这个不允许诗人生存的社会里,我作为诗人的处境,正是一个为自己凿墓穴的孤独者的处境”。诗人是孤独的、落寞的、隐忍的,却又是不可征服、绝不妥协的。这样的诗人形象,在里尔克笔下一位年轻浆手的身上得到充分体现。他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说,有一次在乘坐帆船航行遇到了突如其来的风暴,所有的人都非常紧张、恐慌。在几乎令人窒息的压抑气氛中,一位年轻桨手突然歌唱起来:
人们尽可以怀疑他在其他方面的位置,但他的这一个位置,世界必须折服。
马拉美、瓦雷里、里尔克以及其他的现代诗人对“定义和制造最精妙和最完善的美”、对“纯诗”的倡导和孜孜以求,给了我们什么启示呢?是遭遇失败甚至毁灭时的虔诚、坚忍、不可动摇的态度。任何时代、任何国度,可以配得上伟大诗人这个称号的,没有谁不具有这样的精神和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说,失败既是诗人的宿命,也何尝不是诗人的荣耀。
当下诗歌的失败以及我们的诗人听闻失败的那种态度,反映出新诗写作就是远远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只能在另一个层面上,也就是在自我作为诗人存在的合法性以及实际利益的前提下论成败。因此,私心以为,要和那些被季羡林先生的“失败论”所激怒的人进行讨论,还得先找到一个基点,可是谁有这份闲心呢。
索性再扯远一点。美籍华裔作家哈金曾经发表《伟大的中国小说》一文,引起国内许多作家、学者的讨论。文中说:“早在1868年,J.W.Deforest就给伟大的美国小说下了定义,至今这个定义仍在沿用:‘一个描述美国生活的长篇小说,它的描绘如此广阔、真实并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个有感情、有文化的美国人都不得不承认它似乎再现了自己所知道的某些东西。’表面看起来,这个定义似乎有点陈旧、平淡,实际上是非常宽阔的,并富有极大的理想主义的色彩。它的核心在于没有人能够写成这样的小说,因为不可能有一部让每一个人都能接受的书。然而正是这种理想主义推动着美国作家去创作伟大的作品。”而我们当下的情形是,伟大的作家、伟大的文学、伟大的文学标准,都被嗤之以鼻;蔑视理想和真理,糟践传统,玩弄文学、戏弄人生成为越来越普遍的时尚。在这种时尚中,诗人们越来越泼辣、泼皮,什么都能接受、忍受,除了人家说他失败。
新诗是否失败,自然要看衡量的标准是什么。如果今天的诗人能够意识到,诗歌的失败是命定的,那么他们将比较容易从“潮流”和“时事”中抽离,朝着自己设定的那个不可企及的目标,也就是朝着失败,从容迈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