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名
文丨刘庆邦
朱家运特别想出名,连睡觉时做梦,都云天雾地地做了不少关于出名的美梦。他很早就听说过一句话,叫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他对这句话的理解不是一带而过,是停留的,终极性的。他理解,所谓过,不是过一下子,是过一辈子,是在人世上走一遭。人的过是这样,雁的过也是如此。人在世间走一遭,要留一点名。雁在天空飞一遭呢,要留一点声。否则的话,人和雁的一辈子等于白活。朱家运还听说过一句话,叫人怕出名猪怕壮。这句话跟上句话唱的是反调,告诫人们千万不要出名,一出名就毁了。这句话不惜拿猪作比,说猪吃得肥壮了,就得被人宰掉,吃肉;人一出名呢,其遭遇和下场恐怕跟肥猪差不多。目前来说,朱家运对这第二句话不是很赞同。他想,这样的话很可能是因出名而饱受磨难的人总结出来的,或是想出名没出成、想吃葡萄没吃到嘴里的人所说的酸话。这两种情况跟朱家运的实际情况都不大符合。一是他尚未出名,还处在为出名而奋斗的过程中;二是他对成名的人还只有羡慕,没有嫉妒,不会把人家与猪相提并论。抛开别人不讲,单就朱家运对出名的渴望和强烈程度而言,猪不猪的也无所谓,只要猪肥了就能出名,他宁可当肥猪,不当瘦猪,先出名再说,后果可以暂时忽略不计。
人群如蚁群,想出名是很难的,是有先决条件的。想通过唱歌出名,得有好嗓子;想通过跳舞出名,得有长胳膊长腿好腰身;想通过打篮球打出名堂呢,起码得是个高个子。朱家运不可能通过唱歌出名,他的嗓子紧得很,用扩张器似乎都打不开。他也不可能发挥肢体语言的优势,上舞台跳舞跳出名来,因为他是五短身材,谈不上有什么肢体语言的优势。打篮球更不用说了,他个子低,身高连一米六○都不到,肚子却鼓得像个篮球一样。然而,天生我材必有用,西方不明东方明,朱家运出名的途径是什么呢?他选择的是写作,也就是写小说,当作家。
朱家运为什么会选择写小说作为他出名的途径呢?他觉得这个问题回答起来有点俗,因为不少因写作出名的作者都说到过,他们的写作才能最初是由某个小学或中学的老师发现的。朱家运的回答未能免俗,他不能不承认,他的写作才能也是一位中学语文老师发现的。他写过一篇作文,老师认为写得不错。老师不但在课堂上为全班同学读了他的作文,还评价说,朱家运同学如果照这样子写下去,说不定将来能成为一个作家。哇,作家!老师的说法引起同学们一阵惊呼。就这样,老师的评价和说法像是给朱家运启了蒙,指出了努力方向,又像是把朱家运给惹了,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和作家联系起来,做起了作家梦。说实在话,在此之前,他并不知道作家是干什么吃的,做的是加法,还是减法。听了老师的话之后,他查了一下字典,才从概念上明白了,原来作家是长期以文学创作为业,并做出一定成就的人。他在心里对自己说,好好念书吧,肚子里的书装得多一些,将来争取当个作家。

不能说朱家运不聪明,但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他只读到初中毕业,连高中都没考上,就随着进城的潮流,到城里讨生活了。他先是在城里跑来跑去从垃圾筒里捡废品,后来固定一个地点收废品。朱家运听有人把废品说成破烂,把收购废品的人说成破烂王,很不以为然。废品就是废品,干吗说成破烂呢?只听说过废品可以变废为宝,没听说过变破烂为宝。村里有人说他在城里收废品,他可以接受,如果把他说成在城里收破烂,他就会觉得对他的生意有些贬低。收废品是坐收,居民把废品送到他的收购点,他用电子秤约了斤两,从随身带的腰包里给人家付钱就是了。有的居民叫他老板,给他的感觉很是不错。一听有人叫他老板,他不由得就把腰板挺得板板的,心里说,好玩儿,一不小心,他也成了老板。比起农村人,城里人拥有的东西多,产生的废品也多。朱家运除了不收厨余废品和厕余废品,别的废品他几乎都收。他收的废品有旧衣服、旧报纸、旧杂志,还有旧书。有的杂志并不旧,比如五月份出的新杂志,当月就被人卖掉了。在无事闲坐的时候,他会把新杂志翻一翻,看看其中的小说。看小说的时候,他难免会想起当年语文老师对他的夸奖,看时几乎有了挑剔的目光。在他看来,那些小说不过那么回事儿,小说里所说的那些事儿,他也听说过,要是让他写的话,说不定他也能写出来。别看是新杂志,一当成废品卖就不值钱了。同样一本杂志,在报刊亭里卖十块钱一本,卖到他这里呢,只能卖两毛钱。朱家运把一些杂志看完,并不是随手扔到废品堆里去,而是摆放在地面上。他想试一下,这些杂志有没有人买。定价十块钱一本的杂志,他只卖两块钱。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有人卖,就可能有人买。有人把杂志翻了翻,真的掏两块钱把杂志买走了。细微之处见生财之道,朱家运的精明就在这里,一倒手的工夫,废品变商品,一本杂志他就赚了十倍的钱。
攒了一些钱之后,朱家运不再满足于收购废品。他在城市的郊区租了一块地,办起了一座工厂。朱家运的工厂不生产别的,只生产室内门。那些门看似木门,其实是用锯末、石膏、颗粒塑料等复合材料,通过高温处理压制成型,再趁热贴上一层带有好看木纹的塑料贴膜,一扇门就做成了。这样的门成本很低,每扇门也就几十块钱。可按市场价走,每扇门可以卖几百块钱。在朱家运看来,这就叫发财有门,门门进宝。他满面春风,得意坏了,很快买了小轿车、电脑、老板式写字台,还配备了女秘书。在收购废品时,别人叫他老板,他还有些心虚,有些不好意思。现在他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板,腰也板,脚也板,脸也板,谁开口不叫他朱老板,他反而觉得人家不够意思。
接着,朱老板的名字又和家联系起来,这个家还不是作家的家,是民营企业家的家。什么家都是家,不管干什么事情,后面一带家就有些不得了,都不是凭空而来。科学家、思想家、艺术家,具体来说,还有歌唱家、舞蹈家、书法家等等,都是在某些方面取得一定成就并得到社会认可的人。朱家运对企业家这个称谓比较认可,也比较看重,认为企业家比老板好听。老板的叫法像是从旧社会沿袭过来的,带有一点资本主义的味道。而企业家的称谓比较现代,名头也大一些。

什么家都不能白当,当了家就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为公益事业做一些贡献。市作家协会的秘书长张海艺到厂里找朱家运来了,就一项面向全市中学生征文大赛的合作事宜与朱家运进行商议。张海艺一上来并没有提让朱家运出资的事,只是说待征文结束评奖时可以请朱厂长当评委,召开颁奖会时请朱厂长当颁奖嘉宾,上台为获奖作者颁奖。
朱家运一听就明白了,张秘书长登门找他是拉赞助,是让他“出血”。他微笑着,说谢谢张秘书长的信任,我们厂是一个小厂,和市里其他大企业比起来,连个小拇指都算不上。不过,小拇指也是指头不是,张秘书长需要我们做什么,您只管说。他以为张秘书长会狮子大张口,跟他要六十万,他准备砍下一半,只给张秘书长三十万。张秘书长说了奖金、评委费、证书制作费,还有开会租场地的费用,却只提出了希望朱厂长能赞助二十万元。二十万,比厂里六个工人一年工资的总和还要多。朱家运装作出血出得有些疼,答应得不是很痛快。他眨眨眼皮,像是想了一下,又想了一下,说,那就这样吧。既然尊敬的张秘书长说出来了,我不能让秘书长的话掉在地上啊!
张海艺赶紧站起来握朱家运的手,说朱厂长,您太够意思了,太重视我市的文化建设了,我代表全市的中学生,郑重地向您表示感谢!
朱家运说,我这个人没什么文化,跟一个大老粗差不多。我觉得你们在中学生中搞征文挺好的,写作就是要从青少年抓起。朱家运对张海艺的情况略知一二,知道张海艺是个作家,既写诗,又写报告文学。他在报纸和杂志上看见过张海艺发表的诗歌,也看见过张海艺所写的报告文学。朱家运不爱看诗歌,觉得现在的诗歌比白开水还白气,一点儿味道都没有。朱家运认为张海艺写的报告文学也一般化,报告大于文学,为人说好话而已。朱家运听人说过,张海艺之所以两手抓,是用诗歌打名气,用报告文学捞钱。张海艺只要为某个单位或某个企业家写一篇报告文学,都能挣个万儿八千。朱家运预想,下一步,张海艺会不会提出为他写报告文学呢?倘若张海艺提出这话,他该如何应对呢?有些话他最好说在前头,堵一堵张海艺为他写报告文学的念头。他说,张秘书长,您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也做过当作家的梦呢!他把当年中学语文老师对他的鼓励说了一遍。
张海艺一听像找到了同道一样,认为这太好了!他建议朱厂长尽快把作家梦重新拾起来,使梦想成真。

行吗?
当然行了,您只要写就行。
那我写什么好呢?
我劝您最好不要写诗歌,诗歌界太混乱,浑水摸鱼的人太多,竞争太激烈,想出名太难。我要是给您提建议的话呢,建议您最好写长篇小说。您只要把长篇小说写出来,出书的事您不用发愁,我帮您联系出版社,搞个书号,把您的书推出来。您知道,现在干什么事都讲究规模效应。与其他文学样式比起来,长篇小说的规模效应是明显的。只要您的书出来了,加入作家协会就是顺理成章的事。市里的作家协会就不用说了,让谁入,不让谁入,咱哥们儿说了算。中国作家协会我不敢说,他们的门槛比较高。省里的作家协会,我可以推荐您加入。省里作家协会的秘书长是我的酒友,他每次到咱们市里来,我都把他灌得一塌糊涂。等他下次再来市里,咱们一块儿灌他如何?
可惜我不会喝酒。
不会喝没关系,您给我们提供好酒就是了。
那没问题。
张海艺走后,朱家运没有马上把赞助费打给张海艺。他要等一等,等张海艺发了征文启事,真正把征文搞起来,并搞得差不多了,他再给张海艺打钱不迟。他打钱也不能打到张海艺的个人账户上,须打到作协的账户上,以利于他所赞助的钱能真正发挥作用。钱还没打走,张海艺却把朱家运的写作之心和出名之心勾了起来。朱家运想过,人生在世,东奔西跑,南来北往,追求的不过就是两样东西,一个是利,一个是名。有人得到了利,还没有出名,叫有利无名。有人出了名,又得了利,叫名利双收。就朱家运目前的情况看,他虽说得到了一定的利益,积累了一些财富,名是说不上的,属于籍籍无名的一类。名和利相比,利是物质性的,名是精神性的;利是实的,名是虚的。恰恰因为名是虚的,利比较容易得到,名却不容易取得。好比肉是实的,风是虚的,人们轻易就可以抓到一块肉,却很难抓到一股风。人心比天高,也许越是人们不易得到的虚的东西,对人的诱惑就越大,人们越愿意追求。朱家运听从了张海艺的建议,在抓好生产和产品营销之余,果然写起长篇小说来。他不写则已,一写就写得兴致勃勃,每天都想写,一天不写像是缺了点什么。每天一大早起来,他不刷牙,不洗脸,所干的第一件事是坐下来写一阵子小说。晚上睡觉前,他还要写一会儿小说,才算完成了当天的所有任务,才上床睡觉。花了不到半年的业余时间,朱家运就把一部将近二十万字的长篇小说写完了。写完后,他让秘书打印出来,装订成一本书的模样,马上通读了一遍。他一边读,一边禁不住佩服自己,觉得自己太有才了,太厉害了!他自言自语地问过自己,这么棒的小说,是那个叫朱家运的家伙写的吗?以前没听说他写过小说呀!回答是,没错,这部小说正是那位叫朱家运的企业家写的。他保守估计,这部小说出版后,他的名气一定会升起来,想按都按不住。到时候,他不必再跟张海艺提加入作家协会的事,自然而然就会进入作家的行列。他写的小说,是在他们老家传说甚广的一个土匪头子的故事。土匪头子啸聚起一帮土匪,不仅到处打家劫舍,烧杀抢掠,无恶不作,还特别贪恋女色。每打开一个村寨,土匪们不仅抢钱抢物抢粮,还掠走有姿色的女孩子供土匪头子享用。据说土匪头子按皇帝的标准为自己定了指标,不抢够七十二个女孩子不罢休。官府为了除恶,派了一个训练有素的女刺客,潜入匪穴,伺机把土匪头子干掉。在女刺客的想象里,土匪头子应该是魔头怪脸、凶神恶煞一般,不料土匪头子却像一个温文尔雅的白面书生。加之土匪头子对女刺客的长相气韵欣赏有加,特别厚爱,使女刺客不知不觉间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与土匪头子谈起了诗文。直到有一天,官府让内线给女刺客递话,催促她赶快动手,女刺客才记起自己所负的重任。最后时刻,当女刺客用土匪头子的精致小手枪指向土匪头子时,土匪头子从容镇定、面带笑容地对女刺客说,我早就知道你是官府派来的刺客。只管开枪吧,我成全你!这样一部小说,如果再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的话,受众会更多,覆盖面会更广,影响会更大。到那时候,不知会有多少报社和电视台的记者采访他呢!他的工厂做了那么多门,他想出名都没门儿。而这一部长篇小说,就有可能使他名声大震,声名远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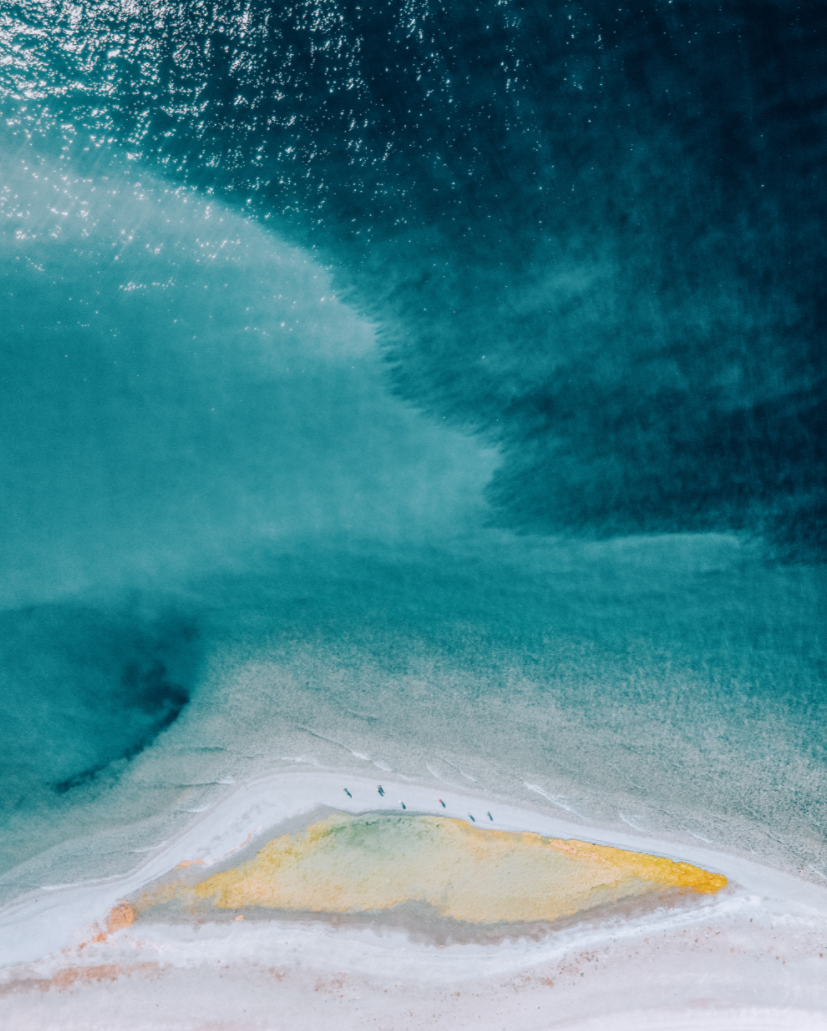
朱家运的书稿通过张海艺推荐给省里的文艺出版社后,出版社的编辑在两三个月后才对书稿提出审读意见。编辑的意见通过张海艺转达给朱家运之后,让满怀希望的朱家运顿时有些泄气。编辑认为,小说的传奇性太强,文学性不足。小说停留在民间传奇的意义上,还没有构成小说意义上的故事。小说的语言不够自然、朴实,虚张声势的形容词太多。另外,书稿中有不少错别字,表明作者写作的基本功还不够扎实。编辑的结论是,这样的书稿离出版标准还有一定距离,尚不能出版。不过,张海艺从编辑那里讨来的还有活话,说这部书是无害的,如果作者执意出版,又有财力的话,可以选择买一个书号,自费出版。
听说让他自费出书,朱家运不是很愿意。他说,那算了吧。
张海艺说,别呀,只要有国家的正规书号,自费出版也是出版,出版后就可以放进国家图书馆,在出版目录上就可以检索到,跟正式出版物没什么区别。
自费出版,哎呀,这个事儿听起来总让人觉得有点别扭。
朱厂长您想多了,无所谓的,咱出书才是目的,书能出来就是胜利。有些情况您可能不了解,现在不少领导干部都是自费出书,出了书下面的人争着买,出书的人赚的钱还更多呢。再说了,书上又不标明是自费不自费的,读者才不关心这个呢。比如您这部书吧,自费的事,您不说,我不说,别的人谁会知道呢!据我所知,近一两年来,我们市的作者没有出过一部长篇。长篇是重头戏,市里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一直很重视长篇小说的创作。您的长篇一出来,等于为全市的文学创作争了光,添了彩,不知会引起多么大的轰动效应呢!到那个时候,不知有多少媒体的记者追着您采访呢!
自费的话,需要多少费用呢?
嘿,对于您这样的大老板来说,多少费用都是九牛一毛。我向编辑打听了一下,书号费、印刷费、编辑费等各种费用加起来,有三十万就够了。
朱家运没养那么多“牛”,也没有那么多“毛”,三十万可不是“一毛”。他说,我想想再说吧。

张海艺似乎不容他多想,开导他说,朱厂长,我认为您目前所面临的是一个新的机遇,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就看您能不能及时把机遇抓住。咱这么说吧,两年之后,市作协换届,您若是有一部长篇小说在手,就有可能当上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还不算,您的影响一扩大,等市里的人大和政协换届的时候,您还有可能当上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您想想看,那是什么成色!
当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朱家运以前从来没敢想过,张海艺的话说得他心里一动,像是为他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是的,不管是代表,还是委员,他如果能当上一样,都非同小可,等于提高了他的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跟当了官差不多。商历来都是匍匐于官的脚下,有了官位才更有利于经商。不难设想,倘若他真的当了“官”,一名引来万利生,他的生意将会更加兴旺,发财的门路将会更加宽广。而这些名和利,必须以出书为前提。先出了书,有了作家的名,才有可能衍生后来的名和利。想到这些,朱家运心里几乎已经同意了自费出书。但他说了“想想再说”,不能把弯子转得太陡,便说,我明白张秘书长在为我铺路搭桥,处处为我着想,非常感谢您!
通过上次我们搞征文合作,我觉得朱厂长您为人特别实在,办事特别痛快,也特别有文人情怀,可以长期交朋友。换了别的人,我才不给他们出这些主意呢!
明白。张秘书长为我这么辛苦,我应该怎么感谢您呢?朱家运心里还有一个明白,人无利不起早,张海艺为他联系出版社出书,按生意场上的规矩,他需要付给张海艺一定的中介费。说不定,张海艺所提出来的三十万元出书费用中,就包括了中介费。朱家运隐约听人说过,出一本书花不了那么多钱,有十几万元就够了,花二十万元的都很少。张海艺所说的三十万元费用中,恐怕得有十万元进入张海艺的腰包。
张海艺的表现十分慷慨,朱厂长,您这样说就外气了,为朋友帮忙,我一分钱的报酬都不会要!帮助市里的作者出书,这本来就是我的职责。
朱家运的长篇小说出版后,拿到新书的他的确有些高兴,比厂里生产出第一扇新门还要高兴许多。他把新书拿在手里前看后看,左看右看,老也看不够。他在写字台上、枕头边、书架上等显眼的地方,都放上了散发着墨香的新书,为的是让自己一抬眼就能看到。他书架上所放的一些书,别的书都是书脊朝外,整本书只露一条窄窄的书脊。他的书放置在书架的最高层,是封面朝外,带有一花独放的展览性质。他最看重的是自己的署名,印在红色封面上的朱家运三个黑字,让他觉得有些熟悉,还有些陌生。看着看着,他的名字仿佛幻化成了他的身影,确认般地立在书的封面上,正在对他微笑。还有他名字后面的那个著字,初见几乎把他吓着了。以前他觉得著字重若千钧万钧,从不敢想有朝一日自己的名字会和著字联系起来。现如今呢,黑字红纸,红纸黑字,他的名字后面真的跟了一个著名的著字。这表明他也有了自己的著作,我的天哪,这可怎么得了!
书为朱家运所赢得的名声构成了一个系列。他在写字台上放有一摞自己的书,每当谈购门生意的客户来访,他必不忘送人家一本书,签名请人家指正。人家接到书,无不对他做出刮目相看的惊讶表情,说朱老板,您原来还是一位作家呀!朱家运表现得很谦虚,说写得不好,业余时间写着玩儿呢!人家问,出这么厚的一本书,得挣不少钱吧?他说,嘿,我不指望写书挣钱,读者爱读,就是对我最高的奖赏。市里的晚报,不仅为他的长篇小说的出版发了消息,还发了书评,称小说写出了人性的丰富性,有积极的阅读价值,是本市文学创作的又一重要收获。朱家运顺利地加入了市里的作家协会,成为市级作家协会的一员。在张海艺的运作下,朱家运还加入了省里的作家协会,并在市作协换届时,当上了市里作家协会的副主席。副主席比较多,有七八头十个。但副主席再多,也不会对副主席的名誉产生稀释作用,他也是副主席其中的一个。有时市里作协召开作者会议,他还被安排坐到了主席台上,座位前面的桌面上赫然摆放着有他名字的席卡。有作者叫他朱主席,要求与他合影。人家喊他主席,受宠若惊之余,他觉得很是受用。他当厂长时,没人要求与他合影。他当上了副主席,才有人与他合影。看来当厂长不算有名,当副主席才算有名。与他合影的有男作者,也有年轻貌美的女作者。女作者挽住他的胳膊时,他美得有些绷不住嘴。为他们照相的人指出了他的美气,说,朱主席好美呀!朱家运变得自信和幽默起来,说是呀,美是不能拒绝的,我不用再喊茄子了!

朱家运也有不甚满足的地方。市里的人大和政协换届的时候,他没能当上人大代表,也没能当上政协委员。还有,他申请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也未获批准。张海艺劝朱家运不要泄气,最好再写一部长篇出来。张海艺说,写小说如种庄稼,庄稼得一茬接着一茬种,不能只种一茬就不种了。张海艺还说,出书如开花,开完一朵还要再开一朵,只开一朵很难引起人们的注意。当上副主席后,朱家运多次请市里的作协主席王年吃饭,跟王年也熟悉了。王年是中国作协的会员,他对朱家运说,据他所知,中国作家协会的门槛是很高的,对入会资格的审查是很严格的。全国各地的写作者申请入会,须先通过专家咨询那一关。专家咨询组的成员都是著名的作家、评论家和编辑家,他们的文学眼光都很厉害,对申请入会的作者相当挑剔。一般来说,从五个申请入会的人中才能挑出一个。有的作者报上去一撂书,都入不了专家的法眼。还有的作者申报了好几次,黑头发变成了白头发,急得几乎撞头,仍没有获得批准。王年主席的看法是,一个作家还是要靠作品说话,只要作品过得硬,作家协会不会把任何一位好作家拒之门外。王年也劝朱家运继续写小说,但他不主张朱家运非要写长篇,把短篇写好了,也能写出名气,也能得到文坛的承认。王年以他自己为例,说他以写小小说为主,至今已发表了二百多篇小小说,小说集已出版了三部,获得过两次刊物的年度文学奖。他虽然没写过长篇小说,并不影响他在文学界产生影响。王年比较看重在文学杂志上发表作品,认为文学杂志构成了文学的阶梯和不同层级的平台,只有通过阶梯,一步一步向上攀登,才有希望登上比较高的平台,扩大在读者中的知名度,并创下自己的牌子。比如在北京的《人民文学》《十月》《当代》等,哪怕在这样的文学杂志上只发表过一篇作品,也跟中了文学状元差不多,可以一辈子都写进作者简介里。专家组里的那些作家、评论家,都是从大刊物里走出来的。他们除了对大刊物有感情,保持着对大刊物的阅读习惯,还通过阅读那些大刊,了解文学的发展情况,看看又出了哪些文学新人。有的新人虽然没出过书,但只要在大刊上发表过一两篇作品,专家看到也会眼睛一亮,说这个可以,有发展潜力,可以吸收入会。
朱家运把王年喊王老师,他说王老师的话是对他的教诲和鼓励,对王老师表示衷心感谢。像王老师这样在市里有名望的人,倘若不是他写了一部小说,当上了作协的副主席,是没机会见到王老师的,请王老师吃饭也轮不到他。王老师的教诲,至少让他明白两个意思。一个意思是,人的名气不能一劳永逸。风经常在大地上吹来吹去,人们才会记住风;云经常在天空飘来飘去,人们才不会忘记云的存在。如果他从此不写小说了,他的名气等于风也不吹了,云也不飘了,什么都没有了。如果说写作偶然使他登上了一条船,上船容易下船难,想下船不是那么容易。另一个意思,王老师希望他也写小小说,写了小小说在刊物上发。朱家运说好,他向王老师学习,写小小说试一试。他问王老师,等我写出了小小说,您你先帮我看一看如何?
王老师没有答应帮他看小小说。王老师说,一般来说,我不看作者没发表的作品,全市的作者那么多,我哪里看得过来!
朱家运听得出来,王老师并没有把门堵死,事情有“一般来说”,就可能有“二般来说”。他说,老师您也知道,我开了一个厂子,经济效益还可以,我不会让老师白辛苦。
王老师摇手,咱不说这个。
朱家运写完了一篇小小说,打印出来,登门请王老师帮他看。他知道王老师爱喝白酒,也爱喝绿茶,就给王老师送上两瓶最好的酒和顶级的茶。
以后再来不要带什么东西。
我请老师帮我掌掌眼,看看我是不是写小说的料儿。要根本不是那块料儿,我以后就不写了。
不管干什么,都不可能一蹴而就。
一篇小小说也就三四千字,不长,朱家运想在王老师家里坐一会儿,等老师把稿子看完后,当时就听听老师的看法。可王老师没有马上就看的意思,他说你不要着急,把稿子留下,我抽时间看,等看完了咱们再联系。
朱家运连说,不着急,不着急!
朱家运耐心等了两个星期,王老师才给他打电话,谈了对稿子的看法。王老师说,他的小说能够自圆其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小说的意思也不错,表达的是一种善意。但小说还是有一些问题,离发表的标准还有一定距离。主要的问题,一是取材不太好,过于离奇。二是立意没有自己独特的发现,缺乏新意。三是叙述语言太用力,太夸张,不准确,不自然。这三个问题都是写小说的基本问题,希望朱家运在今后的写作中加以注意。
那,这篇小说有没有修改的基础呢?
电话那头,王老师停顿了一下才说,修改的基础还是有的,但我建议你不要急着修改,放一放再说。你不妨另写一篇试试。记着,一定要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一定要找到自己。据我所知,你奋斗到今天这一步,也经历了不少艰难困苦,放着自己的生活体验不写,何必舍近求远、隔靴挠痒呢!
太好了,王老师您说得太好了,我觉得听了您的指点有茅塞顿开之感。我的创业经历是很丰富,恐怕写一部长篇都写不完。朱家运正要讲一下他的经历,王老师说,咱们有机会再聊吧!
王老师,今天晚上我请您喝酒如何?
你又不喝酒,我一个人喝,有啥意思呢!
那我把张秘书长约上,让他陪您喝,怎么样?
那就更没必要了。
按照王年老师的指点,朱家运以自己的人生经历为素材,又写了一篇小小说。这次把稿子送给王老师指教时,他没有给王老师送酒和茶叶,而是送上了一个信封,信封里装了三千元现金。王老师一见信封,大约就明白了信封里装的不是信,因为现在写信的人已经很少了,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说,这不好!
朱家运说,王老师,我尊重所有的劳动。
你这句话说得好,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有你这句话,我相信你不会拖欠农民工的工资。
那是肯定的。
这一次,王老师把朱家运的稿子看得比较快。朱家运头天送上稿子,第二天王老师就给朱家运打来了电话,说对了嘛,这样写路子就对了嘛,这篇小说比上一篇好多了。只是结尾处还没有提起来,再把结尾修改一下,往上提一下,这篇稿子就可以往外投了。王老师特别强调了小小说结尾的重要,说看一篇小小说写得如何,主要从结尾上判断。结尾好,作品就好;结尾不好,稿子就砸锅。从某种意义上说,写小小说就是写结尾。小小说的尾巴甚至比老虎和豹子的尾巴还重要,老虎和豹子没了尾巴, 似乎仍可以存活,而小小说的尾巴不好,小小说就活不了。这些都是他的私密经验,以前他没跟别人说过,是第一次跟朱家运说。对于稿子结尾的修改,王老师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几乎等于为朱家运的小说设计了一个结尾。
朱家运只有叫好的份儿。他说太好了,太好了,按照王老师的指教,他马上把结尾改一下。他还说,等他把结尾改好后,再请王老师过目。
王老师说,你改完我就不看了,你直接投给杂志社的编辑部,让编辑看就行了。稿子能不能发,由编辑说了算,直接投给编辑部,就省得绕弯子了。

朱家运把稿子改完后,先寄给了北京的一家杂志社。两个月后没接到采用通知,他改寄到省里的一家杂志社。又两个月过去了,一点儿音信都没有,他再次降格以求,寄给了省会城市的一家杂志社。他知道,这家杂志以发小小说为主,对这家杂志抱的希望大一些。然而,让朱家运失望的是,他把稿子挂号寄给这家杂志社后,仍然如泥块投水,杳无消息。偶尔,有男女文友结伴到朱家运的厂里蹭饭,聊天儿,谈起投稿的事,每个文友似乎都有一肚子怨言。他们说,现在投稿难得很,稿子投到杂志社后,编辑可能连看都不看,就扔到废纸堆里去了。原因是,现在识字的人太多了,有文化的人太多了,能诌两句文的人太多了,加上有了互联网平台,人打个喷嚏,吐口唾沫,出个怪声,都可以在网上发表。人们在自媒体上发了东西不够,还想在大家公认的纸媒上发表,导致涌向各文学杂志的稿子太多太多。虽说写稿子的人大量增加,而文学杂志并没有增加,各家杂志社连名家和熟人的稿子都发不完,哪里还顾得上那么多陌生作者的稿子呢!朱家运对文友们的话深有同感,但他并没有谈自己的投稿经历,他说,看来作者有作者的难,杂志社有杂志社的难。对杂志社来说投稿的人少了是个难,投稿的人多了也是个难。
这年的春节前,按照惯例,市作协召集市里的重点作者开了一个茶话会,是团拜的意思,也是总结全市一年来创作情况的意思。朱家运作为作协的主席团成员之一,作协副主席之一,也参加了团拜会。那部长篇小说出版之后,一两年过去了,朱家运再也没有发表过一篇作品,这让朱家运很有些不好意思。坐在会议室里,他心虚,眼虚,几乎想到了滥竽充数那个成语。朱家运听到一些风言风语,说他出书是花钱买的,当作协副主席也是用钱堆出来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创作才能。买个用塑料花扎成的作家的花环头上戴,图个虚名而已。这些传言让朱家运心里很不是滋味,名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人说名是虚的,给他造成的压力怎么有些实呢!怎么压得他有些喘不过气呢?
王年主席也参加了团拜会,他看出了朱家运情绪不高,单独跟朱家运聊了几句。他说,写小小说,一不要盯,二不要等,你不能盯着写完了的小说,等发出来再写下一篇。写小小说要有一定的数量,要一篇接着一篇写。往外投小小说呢,要像农民往地里撒芝麻一样往外撒。你撒得芝麻多了,总会有一些芝麻会发芽儿,会开花儿,会结果儿。王主席以他自己为例,说他仅去年一年,就在全国各地的报刊杂志发表了二十二篇小小说,月月都不落空。
朱家运承认,王老师太厉害了,简直就是当代的小小说大师。
大师不敢当,勤劳还做得到。
时间能销蚀生铁,也能消耗作家的名气。眼看朱家运作家的名义行将不保,情急之中,他起了一个大胆的主意,试试能不能跟王年老师借一篇小小说,以自己的名义发表。王老师发表了那么多小小说,多一篇少一篇应该无所谓吧。按照王老师把小小说比作芝麻的说法,他手里有那么多的芝麻,多一粒或少一粒,别人谁会注意呢!朱家运听文友说过,别看王老师发了那么多小小说,挣到的稿费并不多。稿费是按字数计酬,一篇小小说的稿费往高了说,也就是挣一千块钱左右。一年发表二十多篇小小说,合计下来不过两万多块钱的稿费。王老师家里的房子是贷款买的,月月都要还贷,手头紧得很。如果王老师能借给他一篇小小说,他愿意以超过通常稿费十倍的价格,付给王老师一万块钱。他事先想到,他一提向王老师借一篇小小说,王老师也许不同意,但等他说明向王老师付一万块钱报酬呢,王老师有可能会考虑考虑。
事情与朱家运预想的一样,当他打电话提出向王老师借一篇小小说时,王老师似乎想都没想,一口就回绝了。王老师说,世上有借钱借粮的,没听说过有借小说的。我的每一篇小说都好像是我的亲生孩子,我的孩子都姓王,一借给你等于将孩子送人,改成了姓朱,这算怎么回事!当朱家运说明借小说不是白借,借一篇付给王老师一万块钱报酬时,王老师的口气就不那么坚决了,说你这个小朱呀,你搞的这叫什么名堂嘛,是不是曲线扶贫的意思呀!
对不起,请王老师多多谅解!您让我当作家协会的副主席,我老是没有新的作品发表,感觉有些名不副实,心里虚得很。您帮学生要帮到底嘛!
这样的事情闻所未闻,要是传出去,岂不成了文坛的一个笑谈嘛!岂不成了别人写小说的素材嘛!
王老师您放心,只要您不说,就不会有任何外人知道。我是得便宜的人,我更会把秘密保守得死死的。
还有一个问题,不知你想过没有,就算我同意借给你一篇小说,但我不敢保证小说就一定能够发表。写小说难就难在它一直存在着不确定性,我对自己的创作也是有时有自信,有时不那么自信。
老师,您谦虚了,您的创作实力和水平在那儿放着,我相信一定没问题。
朱家运说的是向王年借一篇小小说,实际上是买一篇小小说,进行的是一次交易。朱家运一手交钱,王年一手交货,交易很快成功。朱家运拿到稿子一看,王年老师已经把稿子的题目下面署上了他朱家运的名字。朱家运拿到稿子后,还没回到家,坐在自己的小轿车里,就把稿子看完了。朱家运不能不承认,王老师的确是写小小说的高手,作品的确写得高人一筹。小小说虽说不长,却一波三折,意味深长。
事实表明,王老师的担心不无道理,朱家运把稿子从北投到南,从东投到西,不知投了多少家杂志,竟没有一家杂志采用。好比朱家运花钱买了一个闺女,一个不错的闺女,他急于把闺女嫁出去,给闺女找一个婆家,然而又然而,他试了一家又一家,闺女却迟迟嫁不出去。他曾给一家杂志社的编辑部打过电话,问编辑看到他的稿子没有?编辑说没看到。他说他是寄的快递,请编辑帮助查一下。编辑说,每天收到的稿子那么多,怎么查得过来。
一年过去,眼看又到了年底,市里的作家协会又该召开一年一度的茶话会了,朱家运为之救“名”的稿子仍未发出来。
由于和稿子的亲生关系,王年一直惦记着那篇稿子的命运。得知那篇稿子迟迟未能发表,王年对朱家运说,这样吧,你把稿子还给我吧,我自己投一下试试。
朱家运把稿子还给王年,王年把稿子换上自己的名字,投给一家杂志社,稿子很快就发了出来。
王年把一万块钱还给了朱家运。
选自于《清明》2021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