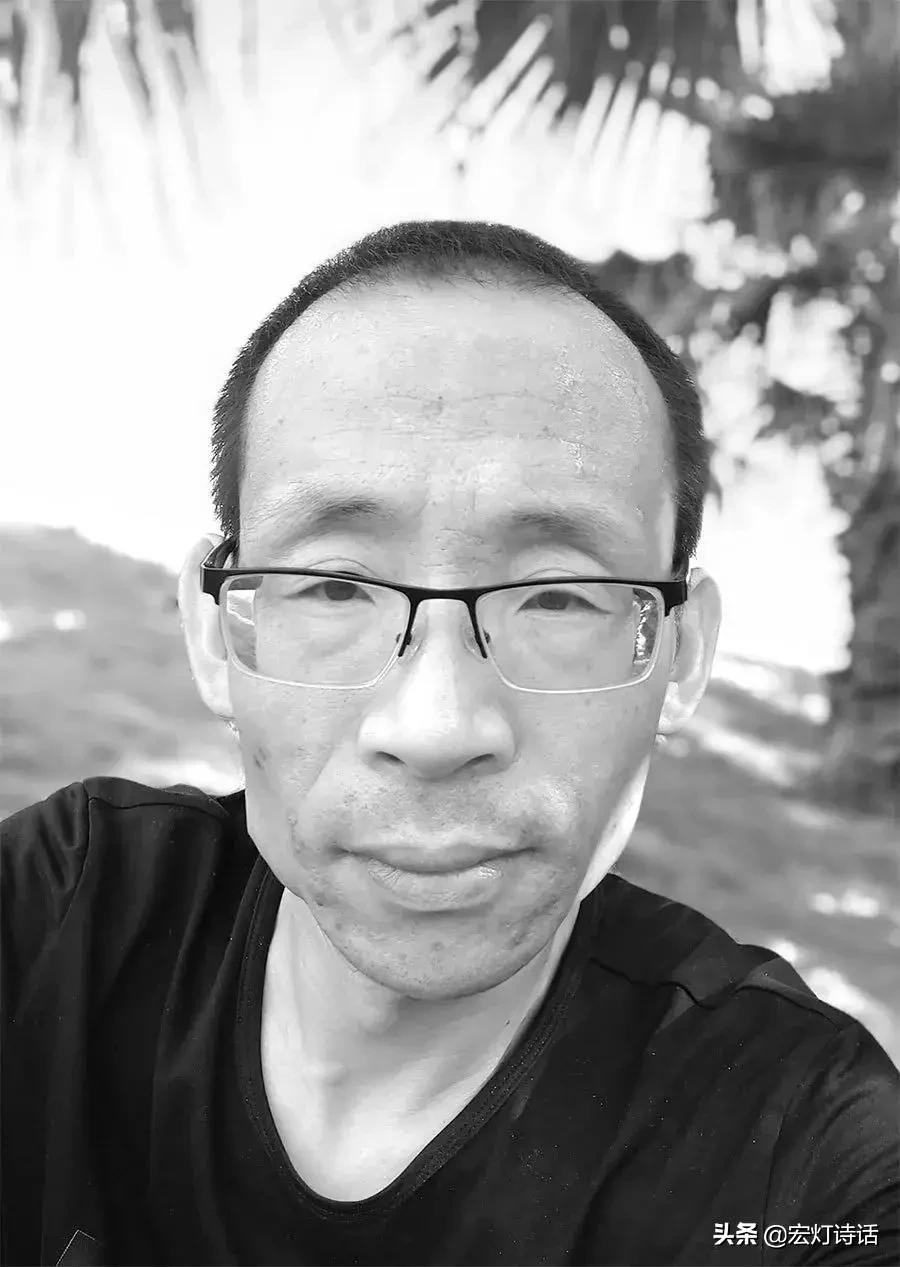
张二棍,本名张常春, 1982 年生于山西代县。曾获《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华文青年诗人奖、李杜青年诗人奖、 《诗歌周刊》年度诗人等。曾参加第 31 届青春诗会,2017 年度首都师范大学驻校诗人。现为山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诗集《入林记》入选中国青年出版社/小众书坊策划出版之“中国好诗 第四季”。
草民
说说韭菜吧。这无骨之物
一丛丛抱着,但不结党
这真正的草民
用一生的时间,顺从着刀子
来不及流血,来不及愈合
就急着生长,用雷同的表情
一茬茬,等待
老大娘
大炕宽,大炕长
大炕睡个老大娘
太老了,就一个人
糊涂地活着
就羞涩地
把前些年
准备的寿衣
里里外外
又穿了一遍
仿佛出殡
也好像出嫁
那年的光
七十年代的阳光,照耀着七十年代的襁褓
七十年代的小孩,咬着七十年代的乳房
七十年代的中午,饥肠辘辘的母亲们
刚刚从生产队回来
左手,拼命擦着汗水
右手,拼命挤着奶水
母亲们站在树阴下
阳光漏在她们的乳房上
仿佛每一个孩子,正在吮吸着的
就是,光
轮 回
雪化为水。水化为无有
无有,在我们头顶堆积着,幻化着
——世间的轮回,从不避人耳目
昨天,一个东倒西歪的酒鬼
如一匹病狗,匍匐在闹市中
一遍遍追着人群,喊:
“谁来骑我,让我也受一受
这胯下之辱”
满街的人,掩面而去
仿佛都受到了奇耻大辱
南 墙
传说中,曾有人撞穿过它
不知所踪。而更多不甘的人
头破血流才肯回来,并在其后漫长的余生
包扎起自己,只露出遍布血丝的眼眶
继续耕田,劈柴,打老婆
回不来的人,都被砌成了砖头
一块踩着一块。让南墙
又厚重了几分
也有人,双手藏在袖筒里
背靠着南墙,打盹,咳嗽
他们是活在自己影子里的人
被阳光,一寸寸搬动着
并将长久陷入,一锅旱烟燃烧过的
沉默里。他们不说,我们就无从知晓
谁曾撞穿南墙,谁又埋骨墙下
聋
总有人一生下来,就选择聋掉
总有人,慢慢变成聋子
有人听不见小一点儿的声音
比如,针尖刺穿血管
有人什么也听不见
比如,山洪冲走牛羊
有人听见了,装作没听见
有人不知道听到了什么,拼命点着头
我见过世界上有一个哑巴
用小到我们听不见的声音
对自己说话。一边说
一边摇着头
我只能听见,那摇头的声音
却无法听见,他对自我的
呵斥和羞辱
寒 流
寒流在清晨,叩响屋檐下的
风铃。它感觉到冷了,嘶哑着喊
娘也感觉到冷了,一路咳嗽着
去了姥姥的坟地。纸糊的衣服
绑在自行车后座上,一路颠呀簸呀
破了几个洞。她急得哭了
就像她小女孩时,给农忙的姥姥
送饭,不小心打翻了
一样的哭。她哭着哭着
就破涕为笑了。仿佛又一次
得到了谅解
勘探者耳语
经测,此山压着十万斤黄金
足够一千个诸侯风光的葬礼
一个老人死了
在这里,一个老人死了。就意味着
门前那棵大榆树,要跟着倒下去
树桠上的乌鸦窝,会被最快的孩子抢走
一个老人死了,李木匠就要连夜忙了
他的聋耳朵上,别着两头尖的铅笔
——这个少年时流落到此的外乡人
背驼了,总是用陌生的口音
把棺椁唤成船舶。一个老人死了
亲人们从四方赶来,张罗着买白布
做孝衣,打墓穴,请鼓匠
一个老人死了,
她养的几只羊就要被卖了
她的菜园子就要荒了
一个老人死了,
她戴了几十年的银镯子
就要从胳膊上,褪下来
戴在另一个人的手上。或者
干脆打成长命锁。一个老人死了
一只大鹅就慌慌张张地
不知道,蛋该往哪里下
一个人死了,还那么纠结
她的呼吸,早就断了
她的体温,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寺庙
那座庙宇荒废已久
僧侣四散。落叶
无人归拢
木雕的佛像里
驻扎庸庸白蚁。半抹残笑
为蛛网牵绊,唇角
沾满蚊虫的尸骸
多让人唏嘘。这最低等的
杀戮场,也曾是口吐莲花的
不二法门
黑夜了,我们还坐在铁路桥下
幸好桥上的那些星星
我真的摘不下来
幸好你也不舍得,我爬那么高
去冒险 。我们坐在地上
你一边抛着小石头
一边抛着奇怪的问题
你六岁了,怕黑,怕远方
怕火车大声的轰鸣
怕我又一个人坐着火车
去了远方。你靠得我
那么近,让我觉得
你就是,我分出来的一小块儿
最骄傲的一小块儿
别人肯定不知道,你模仿着火车
鸣笛的时候,我内心已锃亮
而辽远。我已为你,铺好铁轨
我将用一生,等你通过
旷野
五月的旷野。草木绿到
无所顾忌。飞鸟们在虚无处
放纵着翅膀。而我
一个怀揣口琴的异乡人
背着身。立在野花迷乱的山坳
暗暗地捂住,那一排焦急的琴孔
哦,一群告密者的嘴巴
我害怕。一丝丝风
漏过环扣的指间
我害怕,风随意触动某个音符
都会惊起一只灰兔的耳朵
我甚至害怕,当它无助地回过头来
却发现,我也有一双
红红的,值得怜悯的眼睛
是啊。假如它脱口喊出我的小名
我愿意,是它在荒凉中出没的
相拥而泣的亲人
我已经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了
哪怕一个人躺在床上
蒙着脸,也有奔波之苦
石匠
他祖传的手艺
无非是,把一尊佛
从石头中
救出来
给他磕头
也无非是,把一个人
囚进石头里
也给他磕头
哭丧人说
我曾问过他,是否只需要
一具冷冰的尸体,就能
滚出热泪?不,他微笑着说
不需要那么真实。一个优秀的
哭丧人,要有训练有素的
痛苦,哪怕面对空荡荡的棺木
也可以凭空抓出一位死者
还可以,用抑扬顿挫的哭声
还原莫须有的悲欢
就像某个人真的死了
就像某个人真的活过
他接着又说,好的哭丧人
就是,把自己无数次放倒在
棺木中。好的哭丧人,就是一次次
跪下,用膝盖磨平生死
我哭过那么多死者,每一场
都是一次荡气回肠的
练习。每一个死者,都想象成
你我,被寄走的
替身
太阳落山了
无山可落时
就落水,落地平线
落棚户区,落垃圾堆
我还见过。它静静落在
火葬场的烟囱后面
落日真谦逊啊
它从不对你我的人间
挑三拣四
乡下,神是朴素的
在我的乡下,神仙们坐在穷人
的堂屋里,接受了粗茶淡饭。有年冬天
他们围在清冷的香案上,分食着几瓣烤红薯
而我小脚的祖母,不管他们是否乐意
就端来一盆清水,擦洗每一张瓷质的脸
然后,又为我揩净乌黑的唇角
——呃,他们像是一群比我更小
更木讷的孩子,不懂得喊甜
也不懂喊冷。在乡下
神,如此朴素
蚁
一定是蚂蚁最早发现了春天
我的儿子,一定是最早发现蚂蚁的那个人
一岁的他,还不能喊出,
一只行走在尘埃里的
卑微的名字
却敢于用单纯的惊喜
大声的命名
——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