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彩霞
北京外国语大学校园里,绿树环绕着大卫•柯鲁克的半身铜像。
有一天,一位白发老妇来到铜像前,她掏出一方白手帕,先放在嘴边亲吻了一下,然后开始慢慢擦拭大卫的脸。
那一刻,她脸上闪耀着动人的亲情。
她叫伊莎白•柯鲁克,是大卫•柯鲁克的妻子,他们已经分别20年了。

伊莎白•柯鲁克夫妇在北外门前
爱情,由大渡河、铁索桥见证
1941年,四川璧山县兴隆场。在野狗狂吠、荒草过膝的山野里,一中一洋两位姑娘手持打狗棍艰难前行。
她们是受邀来参加乡村建设项目的。其中,一头金发的,是26岁的伊莎白•布朗。
伊莎白出生于成都一个传教士家庭,父母都在华西协合大学任教。
外祖母曾经资助过中国佣人,父母对当地那些衣衫褴褛、汗流浃背的苦力,也总是和颜悦色,善良和友谊的种子从小就播撒在她的心里。
1938年,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不顾抗日战争已经打响,伊莎白迫不及待回到中国。

青年伊莎白
条件恶劣、鼠蚊横行、气候湿热,兴隆场成为疾病频发之地。但这些都难以阻挡伊莎白的热情。
换上当地人的长衫、草帽、草鞋,她开始工作。
然而,谈何容易。那时,老百姓被征粮、征税、拉壮丁吓破了胆,再加上匪患严重,到处弥漫着恐惧惊疑的气氛。
因山上人家住得分散,为防盗贼、土匪,几乎家家养狗护院。为了安全,她们出门必得带一根打狗棍防身。
为了打消乡民的疑虑,伊莎白操着一口四川话,和当地人聊天,她的真诚和友善赢得了他们的好感。
整整5个月,近1500户人家全部走了一遍,长达36万字的田野手记终于完成。

伊莎白与父母
在乡下,最愉快的时光来自未婚夫大卫•柯鲁克的造访。
柯鲁克是英国人,比伊莎白大5岁。他有一头漂亮的黑发,英俊帅气。
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西班牙内战爆发后,参加了反法西斯国际纵队。
一次战斗中,他负伤了,养伤期间,读到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遂对中国革命发生兴趣,于偶然机会下来到中国。
结束上海的工作后,柯鲁克来到大后方,在成都华西大学执教。
有一天,在办公室里,他见到了身材高挑、美丽聪颖的伊莎白,她是来替生病的妹妹代课的。
对于中国劳工的同情和关注令彼此相见恨晚,共同话题不断,他们擦出了爱的火花。
而此前,一位追求过伊莎白的美国记者曾大发感慨:“她确实不错。但老实说,个性太鲜明,吓跑了我。”
柯鲁克没有被吓跑,恰恰相反,伊莎白的勇敢、毅力,正是他无比欣赏的。

大卫•柯鲁克
1941年夏天,为了寻找斯诺笔下的红军长征足迹,他们在横断山脉的皱褶间艰难行走了六个星期。
来到大渡河边,走上令人胆战心惊的铁索桥,脚下波涛怒吼,回声震撼两岸。
手抚冰凉的铁链,脚踩摇晃的木板,他们用目光对话。
一回到成都,伊莎白就和柯鲁克订婚了。没有任何海誓山盟,大渡河的每一朵浪花已为爱情作证。对于中国的热爱,已将他们紧紧连在一起。
正值希特勒大举进攻苏联,柯鲁克回到英国参加反法西斯斗争,成为英国皇家空军的一员。
1942年,兴隆场项目结束,伊莎白带着十大箱的田野笔记,去英国与柯鲁克团聚。不久,他们结婚了。
在柯鲁克的影响下,伊莎白加入了英国共产党。她加入了驻英国的加拿大妇女军团,为战场上的军官做心理培训。
可是中国难以割舍,一有闲暇,她就研究兴隆场的那批资料,并带着大纲去拜访著名人类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雷蒙德•弗思教授。
二战结束后,伊莎白师从弗思,攻读人类学博士,柯鲁克也进入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学习中文。
1947年,柯鲁克办理空军退役手续,得知从哪里到英国报名参军,就可以免费被送回哪里时,他郑重地签下他和伊莎白的名字。
尽管那时,整个中国都在战火硝烟中。在外国人纷纷逃离时,他们选择逆行。

1947年,柯鲁克在太行山下
中国,是唯一选择
身穿笔挺的英军军装,伊莎白和柯鲁克经香港到达天津。
冒着生命危险,他们穿过国民党封锁区,来到解放区,驻扎在河北省武安县十里店村。
土改正轰轰烈烈地开展,由于国民党当局对土改运动有许多诬蔑和谣传,外界极想了解真实情况。
这是兴隆场之外又一次丰富的人类学实践,伊莎白的眼里闪着激动的光,她希望自己也能写出一部向西方介绍真实中国的作品,就像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一样。
解放战争打得正酣,山村生活条件极差,伊莎白和柯鲁克拒绝了特别为他们的准备的白米粥、白面馒头,他们在农民家中睡土炕、吃派饭,和当地人一样,一天两顿。
笔挺的呢子军装换成了肥大的解放军土布军装,他们学会了把手揣进袖筒,吃饭时,和农民一样,在饭场上端着大碗“一圪蹴”。

柯鲁克夫妇
哪里有农民,哪里就有伊莎白的身影,田地间、打谷场、担粪路上,她用带着浓重四川口音的中国话和农民拉家常,和他们一起刨地,第一手资料就这样一一获取。
在当地农民眼里,伊莎白夫妇“是高级知识分子,但没有一点架子”,“每天比我们劳动的时间还长”。
每晚的豆油灯下,整理笔记,誊写打印,冲洗照片,装订文件,伊莎白参与着、感受着、记录着。
山村的夜晚已经宁静时,打字机还在啪啪作响。
在解放区的生活,已经把他们和中国革命捆绑在了一起。
在十里店的八个月,伊莎白和柯鲁克亲眼目睹了整个土改的过程。
以特约记者的身份,柯鲁克把所见所闻写成稿件,源源不断地寄给英国报纸;而伊莎白,则定期向弗思教授汇报自己的调查研究,继续学业。

柯鲁克夫妇
土改结束后,伊莎白和柯鲁克准备返回英国,完成十里店的研究报告。
恰在此时,中央外事组负责人王炳南找上门来,希望他们留下来,前往外事学校任教——新中国即将成立,要走上国际舞台,培养外交干部成为当务之急。
1948年夏天,一个炎热的下午,伊莎白和柯鲁克来到位于石家庄附近的南海山外事学校,校长叶剑英亲自接待了他们。
面对邀请,他们再次选择了中国。
写作计划暂停,也放弃了个人志向,伊莎白最终走上讲台,与父母殊途同归。
住在四面透风的土坯房里,夫妇俩开始英语教学生涯。
没有教材,就自己编撰;国民党的骑兵不时来袭击,有时会在夜间转移,一走就走到天亮。
艰苦环境中,他们为新中国培养了第一批外交人才,成为外语教育事业的奠基人。

伊莎白、柯鲁克夫妇与叶剑英(左一)在一起
心中有爱,眼底有光
建国后,学校迁往北京,更名为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外国语大学前身)。柯鲁克任英语系副主任,伊莎白则是口语老师。
身材修长的她,穿一身灰色列宁装,娴雅文静。三个儿子的相继出生,为小家庭带来了别样欢乐。
高鼻、深目,操一口地道北京腔的孩子们,成为北外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柯鲁克夫妇与三个儿子
每到星期天,伊莎白不仅会为成绩靠后的学生开小灶,还经常邀请学生来家里吃烧饼夹酱肉,尽管那时,他们的工资也是以小米来计算的。
教学的同时,夫妇俩坚持整理十里店的资料。1959年,他们合作撰写的《十里店——中国一个村庄的革命》在英国伦敦出版。
在国门封闭的年代,这本书成为西方人了解中国土改运动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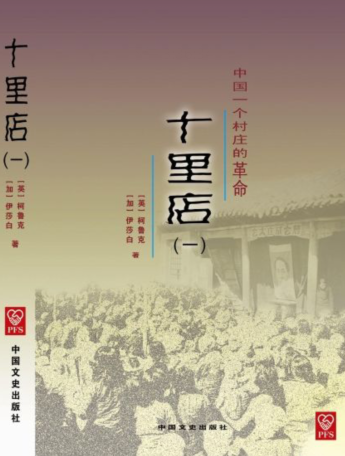
《十里店》
作品驰名国际,橄榄枝随之而来,英国一所大学为他们提供了优越的教职工作。
可那时,正值中苏交恶,“如果我们在这时候离开中国,就是抛弃最珍贵的朋友,这会良心不安的。”
在中国最需要的时候,他们仍然选择留下。
不曾预料的是,不久后的政治风波中,夫妇俩也遭遇了牢狱之灾。
1967年,作为“外国特务”,柯鲁克被捕入狱,被单独监禁在秦城监狱。
随后,伊莎白也被关在大学一个小楼房里,为防她自杀,专门派了两人看守。
1972年,伊莎白被释放,第二年,柯鲁克也回家了。
令伊莎白感动的是,在人民大会堂,周恩来总理亲自向他们公开道歉。
带着对过去的美好回忆,伊莎白和柯鲁克又满怀热情投身教育事业。

柯鲁克夫妇
1980年,离开教学一线后,伊莎白打开尘封了几十年的箱子,读着当年的家信,青春时光呼之欲出。
种种原因,兴隆场的研究一直搁浅,中断多年之后,她终于有机会重新拿起笔。
为了完善资料,她多次往返兴隆场,2013年,《兴隆场:抗战时期四川农民生活调查(1940-1942)》正式出版。
湮没于历史深处的芸芸众生鲜活呈现,伊莎白为中国历史画卷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而那一年,她98岁,柯鲁克已经去世13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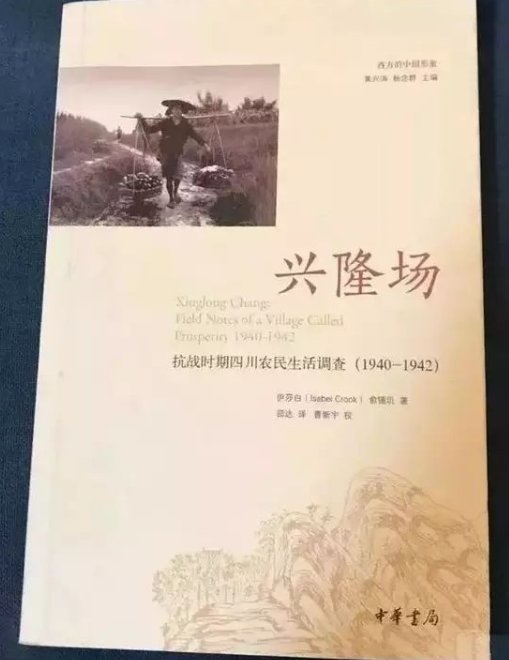
《兴隆场》
住在他们共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的北外专家楼里,翻看着柯鲁克当年拍摄的几千张照片,伊莎白的记忆一点点复活。
青春、爱情、梦想,一切的一切,她都献给了热爱着的中国。
“因为我们参与了中国伟大而曲折的革命,大卫的一生和我们整个家庭的生活都被极大地丰富了。”
金发已成白发,矫健的身姿也已不再。然而,心中有爱,眼底有光,走过一百年,她依然年轻。

伊莎白在柯鲁克铜像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