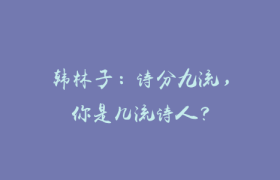内容摘要:新中国戏曲70年历程中,传统戏的生存既幸运又曲折,历经从禁戏、纠偏到传统戏退出舞台的波澜,改革开放后终于获得正常的生存环境;现代戏始终是最受重视的戏曲类型,虽有不少优秀作品,但是一直受非艺术的工具化理念影响,得失均令人思考;新编古装戏中包含了诸多影响深远、代表当代戏剧创作高度的新作,并且与传统戏一道支撑着演出市场。而从盲目遵从现实主义理念到戏曲化成为普遍共识,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古装戏终于成为具有艺术共性的整体。
关 键 词:传统戏 新编古装戏 现代戏 新中国70年 中国戏曲 戏曲评论
中国戏曲有数百年悠久历史,新中国成立以来的70年,戏曲生存发展的历程和语境却具有最复杂的特性。1949年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时,戏曲的身份特殊且微妙。中国文联的架构设计中有关戏曲的安排,和音乐、美术等艺术门类并不一样——戏剧领域既有中华全国戏剧家协会,同时还有筹备中的“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筹备委员会[1],这两个机构并置的现象,最清晰不过地说明了筹建中的新中国文化部门领导人对戏曲的矛盾和复杂的认识。但是发展了的现实很快就回应了戏曲在整体上是否应该和可以成为新文化的组成部分这个看似困难的问题,至少从第二届全国文代会至今,戏曲界的从业人员不仅毫无争议地进入“戏剧家”协会,并且,无论是会员数量还是理事、主席团成员的数量,都占据压倒性优势,始终是这个协会的主体。在新中国初生时有关戏曲身份的争议,说明在全国第一次文代会期间,“旧文化”和“新文化”之间的壁垒尚未打破;然而文化部在戏剧领域的工作重点,显然是在还被归属于“旧文化”范畴内的戏曲——在新成立的中央政府部门里,戏剧的主管部门名为“戏曲改进局”,在主管所有艺术门类的艺术管理局[2]成立之前,话剧的管理在文化部门反而是个空白。新中国70年戏曲的道路是从这样的起点开始的,因此注定要经历许多曲折。而戏曲之不同于其他艺术门类之处,就在于不同题材类型的戏曲创作演出在各个不同阶段的境遇截然不同,它们经常呈现交替发展的态势。所以,我们需要从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古装戏这三大类型的剧目各自的发展轨迹,来讨论和总结新中国70年戏曲的发展,如此才有可能总结过去,观照当下,展望未来。

一、传统戏历尽波折又见光明
“戏改”与戏曲艺术最直接的关联,当然就是针对大量戏曲传统剧目的“改戏”。新中国成立伊始,戏曲行业发展的重心就是“旧剧”的“改进”,而“戏改”的全面推进显然是对戏曲影响最为深远的事件;直至戏曲行业的代表人物被完整地纳入文联所属的戏剧家协会,尤其是文化部撤消特设的“戏曲改进局”,改而组建全面负责戏曲和话剧等戏剧门类管理的艺术局后,政府对戏曲正常运营的关注,才开始逐渐取代以“改进”为主轴的阶段。
1952年举办的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可以看成是“戏改”获得阶段性成果的标志,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3个剧种、37个剧团(包括院、校)参加演出,这次规模空前的会演的参演剧目中,既有像评剧《小女婿》、沪剧《罗汉钱》、眉户《十二把镰刀》这类著名的“解放新戏”,亦有像梅兰芳的《贵妃醉酒》,荀慧生、筱翠花的《樊江关》和张云溪、张春华的《三岔口》等传统经典剧目。参加演出的82个剧目中传统剧目多达63个,虽然其中越剧《梁祝》、京剧《白蛇传》和楚剧《葛麻》等传统剧目,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改编。这个会演剧目单让我们看到1949年至1952年这短短三年里戏曲政策不动声色地发生的重大变化,大量的传统剧目、尤其是京剧的传统戏被邀请参加会演,说明它们已经获得了在新社会的生存许可,而在1949年,梅兰芳还为《贵妃醉酒》这类保留剧目是否适宜于在新社会上演而担忧。参演的传统戏里绝大多数剧目,70年后依然活跃在当今的戏曲舞台,并且仍然是各剧种最重要的保留剧目,这恰恰是最初的“戏改”政策在经过了大幅度调整后的结果,也证明这样的调整完全正确。
如前所述,几乎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新政府成立的第一天起,“戏改”就是文化部门最中心的任务,然而对“戏改”的纠偏又是与之如影相伴的。毋庸讳言,戏曲在整体上最初被归属为“旧文化”范畴,各地相继实施过多项后来看实属偏激的禁戏政策。1950年底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将禁戏的权限收归中央,正是为了遏止各地方政府一度盛行的随意禁戏的现象;当然,正由于各地政府“戏改”部门对禁戏的理解和执行情况太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区“戏改”政策的极大差异,也有损于新政权的权威。1956年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张庚提出要“清除清规戒律”[3],并且从理论上对一批影响较大的传统剧目曾经引起的争议做了细致的辨析,让这些经典剧目继续流传有了充分的合法性,他的观点集中了1949年之后以田汉、马彦祥为代表的“戏改”部门领导人和戏曲学者的艺术与政治智慧,最大限度地为传统戏的生存和戏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关键性的保障。
从传统剧目的角度看,从1950年到1957年的这段时间里,国家戏剧政策的主轴并非禁戏,而是开放,这一趋势在1957年达到顶点,该年5月份文化部正式宣布,决定“除已经明令解禁的《乌盆计》和《探阴山》外,以前所有禁演剧目,一律开放。今后各地对过去曾经禁演过的剧目,或者经过修改后上演,或者原本演出;或者经过内部试演后上演,或者进行公开演出,都由各地剧团及艺人参酌当地情况自行掌握。”[4]这一公开文件为禁戏画上了一个句号,在某种意义上也意味着“戏改”的结束。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典型案例透视“戏改”初期禁戏的范围,在接获文化部开放的通知后,沈阳市文化局于1956年9月15日至28日在沈阳剧场举办了“久不上演剧目展览周”,其中上演的剧目包括京剧《盘丝洞》《梅龙镇》《杀四门》《探阴山》《六五花洞》等,这些剧目即使并不都在明令禁演之列,但是在各地确实也不受鼓励;然而连评剧《王少安赶船》《花为媒》等评剧界曾经最为家喻户晓的经典都作为“久不上演剧目”参加了此次演出[5],足以说明有多大范围的优秀传统戏因各种原因被限制演出,明令或“暗令”禁演传统剧目的现象一度是多么严重。

评剧《王少安赶船》
对“戏改”初期大量禁演传统戏的偏激政策的纠正,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新中国在文化上接续历史的努力,至少是就戏曲这一与普通民众关系最为密切的艺术类型而言,千百年来人民创造的那些传统经典作品的思想与艺术价值终于得到承认,它们应成为新社会文化艺术建设中的重要资源这一理念,逐渐为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接受;与此同时,传统戏必须经过甄别、整理和加工,其中大部分都应不同程度地加以改造的观念,在1949年至1957年这个特殊时间段里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所以,一方面从“纠偏”到张庚“清除清规戒律”的讲话,表达了对传统戏当代价值的积极认识,但是另一方面,对传统戏的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的强烈质疑依然屡见不鲜;一方面挖掘传统剧目逐渐成为戏曲界的共识,另一方面其中究竟有多少剧目可以任其上演,还存在诸多不同的意见。
按刘芝明1957年代表文化部在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供的数据,1956年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后的一年左右,全国各地共发掘了51867个传统剧目,记录了14632个,整理了4223个,上演了10520个。按这个数字,这些挖掘剧目在短短一年时间里就有20.3%被搬上舞台,且有8.1%得到了整理。他还指出,这些新发掘并且被搬上舞台演出的传统剧目,“较优秀的”有1065个,“坏的”有110个,且这些“坏”剧目里“也可能有些剧目不一定就是坏剧目,而是有改好的可能的”。诚然,如刘芝明所说,这发掘的51867个传统剧目“可能有重复的,或者有一些是去年六月以前发掘的”[6],但无论如何,都说明传统戏剧这个文化宝库里的大部分内容,曾经险遭丢弃;尤其是其中被认为“较优秀的”1065个剧目,假如不是由于“开放剧目”,这些好戏恐怕就只能永远含冤九泉。
1961年有关传统戏、新编历史剧和现代戏“三并举”的方针,让逐渐开放、上演传统戏的政策有了新的依据,但是这一趋势在1964年出现逆转。孟超根据传统戏改编的昆剧《李慧娘》受到的政治化批判,姚文元对京剧《海瑞罢官》的恶意构陷,直接导致了包括传统戏在内的所有古装戏被逐出戏曲舞台,更让戏曲剧团对上演传统戏噤若寒蝉。尽管在“文革”时期,各地仍有极少数农村地区的民间剧团偷偷演出部分传统戏,但是在整体上看,直到1978年春天邓小平在成都欣赏川剧传统折子戏后明确做了“这些川剧传统戏都不错,可以分别情况对待。一些优秀的戏可以向社会公演……一些剧目可以先在内部演出,听取意见,修改之后即可公演;有的戏一时难于改好,艺术、技巧上又有特点,可作教学剧目,传授给学生”[7]的重要指示,传统戏才重新回到戏曲舞台,而1980年12月中国戏曲学院在北京天桥剧场连演七场《四郎探母》,更是极具标志性的事件。
改革开放让传统戏重获生机,但传统戏的前路并非一马平川的坦途。在20世纪80年代初,有关京剧《四郎探母》的批评仍时有所见,文化部有关开放传统剧目上演的通知中仍强调“对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一定要严格掌握……在演出场次的安排上,要全面考虑,对恢复上演传统戏要适当控制,不宜过分集中”[8],而各剧种的传统戏重现舞台仍有一些若明若暗的阻力,甚至也有这样的观点,认为应该运用行政手段干预传统戏上演比例过高的现象。但是戏曲演出市场依然钟情于传统戏,20世纪80年代初偶尔出现的“探索性”的戏曲新剧目对它构不成任何挑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戏剧危机,对戏曲演出、尤其是城市戏曲演出市场的影响是全方位的,不仅包括戏曲、话剧,也包括其他几乎所有的剧场艺术样式。戏剧演出市场逐渐陷入萎顿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社会上一时兴起的对外来文化艺术的非理性迷恋显然是其原因之一,传统戏是最直接的受害者。如果认识到在审美趣味变化相对较小的部分农村地区,戏曲依然有其稳定的市场,更足以说明传统戏曲急剧离开舞台的主要原因。反过来说,21世纪社会对传统文化的兴趣逐渐升温,传统戏曲正因这一契机,才有重新复苏的机会。
改革开放为传统戏提供了全新的政策环境,“三并举”方针不再只被看成是传统戏改造尚未彻底完成前的权宜之计,经历30年阴晴不定祸福难料的起起落落,戏曲传统戏至此才真正获得正视。它还得益于这个时代的戏曲批评家从理论上解除了传统戏的“原罪”,同时得益于国家高层领导主持的“京剧音配像”工程等内在地深刻体现了对传统戏的尊重与保护的大型文化项目,更关键的因素,则是全社会对传统文化的认识的彻底改变。尽管很少有人提及演出市场的实际反馈,但是事实俱在,即使是在传统戏受到最多质疑的年代,它也始终是最受观众喜爱的戏曲剧目类型,有不在少数的剧团曾经因上演传统戏而被指“票房至上”受到批评,算是有趣的旁证。
戏曲传统戏在21世纪有了新的机遇,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只有在新世纪传统戏才获得了友好而温润的生存空间。尤其是2001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第一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激发了社会对文化遗产的热情,大部分戏曲剧种都陆续被列入国家非遗名录,“遗产”这个此前始终略带负面的灰色名词,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可激发各地民众文化自豪感的正面词汇。在全本昆剧《牡丹亭》《长生殿》上演时,主创和剧团强调的不是对该剧做了多少“创新”性的改变,而是反复强调这是“原汁原味”的演出,这样的传播策略获得极佳的效果,反过来也证明普通民众对“传统”的观感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昆剧《牡丹亭》
新世纪国家出台一系列扶持传统戏发掘、整理尤其是舞台艺术传承的政策,戏曲界传承经典的自觉意识明显增强,这对戏曲传统戏的存续都十分有利。新世纪的戏曲舞台上,传统戏的存在状况有明显好转,它们也仍然是演出市场的宠儿。只是由于长期的中断,除了京剧、昆剧之外,绝大部分剧种传承至今仍能完整演出的传统戏,都只是其经典剧目中的很少一部分,而且这少量传承至今的剧目多半是“戏改”年代加工整理过的版本,只能算“准传统戏”。传统戏挖掘的工作量依然很大,传承依然是其难点和重心。传统戏从来都是戏曲健康发展的压舱石,既然70年里传统戏的命运均与政策导向密切相关,当其身处70年里最优的政策环境,相信它会对戏曲健康发展起到更积极的作用。
二、现代戏得失兼具终有所成
戏曲界通常把遵从主流意识形态指向描写现当代生活的戏曲剧目称为“现代戏”。70年来,无论在哪个时期,各级政府始终不渝地通过政策倾斜与资源挹注等多种形式支持现代戏的创作演出,成绩固然不菲,但随之而来的还有诸多值得思考的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几年里,各地解放区创作演出的众多“解放新戏”曾经是最受欢迎的剧目,尤其是《九件衣》《白毛女》更是与解放大军如影随行般演遍了全国。像评剧《刘巧儿》《小女婿》、吕剧《李二嫂改嫁》、沪剧《罗汉钱》等主张婚姻自主的新剧目在妇女解放进程中,代表了占人口数量一半又长期受深重压迫的女性的反抗心声。但是从演出市场的角度看,这类“解放新戏”并不像传统戏那样能持续上演,解放的激情过后,它们也就逐渐淡出了舞台。在诸多“解放新戏”里,评剧《刘巧儿》差不多是唯一的一部堪称新经典的现代戏新剧目,它在这70年里久演不衰,至少说明现代戏并不是不可能有其生命力。不过能够持续上演的作品实在太少,即使是因表演艺术水平获得高度肯定而应邀参加成为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的九个现代题材新剧目(含两个剧种演出的《王贵与李香香》)之一,也未持久获得观众喜爱并且在演出市场里持续存在。70年后的今天,这些参演剧目中只有沪剧《罗汉钱》在舞台上偶尔露面,其中最广为流传的唱段“燕燕做媒”,还要托赖改革开放后流行歌手朱明瑛的演绎,才得以继续其影响力。

歌剧《白毛女》
1952年后,现代戏的创作演出陷入一个低潮期,这一现象并不符合文化主管部门的预期。1958年3月5日,文化部颁布了《关于大力繁荣艺术创作的通知》,强调“急需创作反映我国当前的和近十年来的伟大变革、歌颂我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英雄业绩的艺术作品”,并且于该年6月至7月召开了全国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周扬在会上提出,现代戏创作其实是“戏曲工作的第二次革新”,他认为这次革新“就是要使戏曲艺术不仅适合于新时代的需要,而且要使它能够表现工农兵,表现新时代”。而只有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戏曲艺术的革新才算是彻底完成”。[9]文化部副部长刘芝明在会议的总结发言中,更明确提出要努力解决戏曲表现现代生活的问题,要通过演现代戏“扩大社会主义阵地”,他甚至指出,“我们的口号是:鼓足干劲,破除迷信,苦战三年,争取在大多数的剧种和剧团的上演剧目中,现代剧目的比例分别达到20%至50%。”[10]刘芝明代表文化部所作的报告原本希望:争取在三五年内,有大批的现代剧目,在思想性、艺术性和表现技巧方面有更高的成就和更多的保留剧目。其初衷当然并不满足于粗制滥造的创作,但不幸的是时逢“大跃进”的特殊背景,各地一哄而上创作现代戏,在这样的创作环境中,根本不可能顾及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表现技巧”;虽然在这一时期,也出现了豫剧《朝阳沟》、眉户《梁秋燕》等佳作,但是从整体上看,并没有多少值得称道的成果。
1964年北京召开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是1949年以来推动现代戏创作的政策措施的重要结晶,在此前后全国各地都纷纷举办了区域性的现代戏会演,不仅京剧,包括昆剧在内的几乎所有戏曲剧种都在批量创作现代戏,扬剧《夺印》、昆剧《红霞》、京剧《审椅子》等都是各地有影响的作品。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更有众多相当成熟的现代京剧作品出现,除了后来被改编为“样板戏”的《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浜》和《海港》《杜鹃山》等等,还有像京剧《节振国》《六号门》《黛诺》等风格题材各异的优秀作品。

样板戏《智取威虎山》
无论江青曾经如何利用“样板戏”为其个人政治野心服务,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集中展示的一批现代戏作品,在中国当代70年里都是非常优秀的。诚然,它们在其后一些年里产生的巨大影响,尤其是在全国各地包括那些原本京剧观众并不多的区域里的广泛流行,并不完全是艺术自由竞争的结果,因为除了这几部“样板戏”之外的所有戏曲作品——无论是古代题材作品,还是包括《朝阳沟》在内的早就家喻户晓的现代戏,甚至还有其他舞台艺术作品——都遭到无情封杀,迫使全国人民只能借这几部作品满足艺术欣赏的需求,这种极端化的政治手段确实是令人厌恶的,而全国人民都对这些样板戏耳熟能详并不完全是由于它们的艺术质量高超;不过我们不能因“样板戏”被阴谋家利用就对它们的艺术水准视而不见,客观而论,它们不仅在题材上比20世纪50年代初的“解放新戏”更多样化,在艺术创作过程中长达数年的精雕细琢,也迥异于“大跃进”年代的急功近利。
在现代戏的发展过程中,“样板戏”的创作模式与艺术取向产生深远影响,即使进入改革开放时代之后,“样板戏”所遵循的“三突出”“高大全”等戏剧人物塑造理念,依然在现代戏领域若隐若现。如果说改革开放之初一度出现过的领袖题材戏曲作品,主人公的特殊身份决定了这样的作品很难避免对人物某种程度的神化与理想化倾向,其后越来越多以褒扬英模人物为创作动机的作品,要想在这一方面有所突破,也绝非易事。
现代戏在其发展的前30年尽管一直受到鼓励,然而从事现代戏创作的政治风险一点也不比其他题材类型小。改革开放为戏曲创作提供了更好的环境,现代戏创作者因此获得了更大的空间,但真正在这一领域有明显突破的作品并不多。从川剧《四姑娘》到汉剧《弹吉他的姑娘》、商洛花鼓戏《六斤县长》、豫剧《倒霉大叔的婚事》等,改革开放之初的几年里,戏曲界并不缺乏令人称道的现代戏,遗憾的是其中绝大多数都很难持续在舞台上存在,现代戏受题材内容之限较难超越特定时代的现象仍然很普遍。更何况现代戏创作从一开始就与功利化的艺术理念密不可分,对现代戏创作的鼓励,背后经常包含了即时甚至狭隘的非艺术动机,从编剧、导演到演员和剧团等创作主体,难免不同程度地受到功利化思维影响,所以很容易导致创作陷入误区。20世纪80年代后期戏曲面临市场滑坡的新挑战,剧团为解决生存困境不得不趋附于政府部门和企业,创作为之宣传的“行业戏”。一度盛行的“行业戏”成为现代戏创作的新契机,从短时期看,现代戏一时成了救戏曲行业渡过难关的灵丹妙药,然而既然以“行业戏”为创作目标,必然是尽可能地满足特定行业的委托创作者的需求,至少涉及这一行业时,人物塑造是很难追求立体化和丰富性的。没有立体与生动的戏剧人物形象,作品就无法获得普通观众的认同。在这一时期,现代戏的量与质的反差依然形成鲜明的对照。
进入21世纪后,从整体上看,国家对戏曲的投入迅速增长,更重要的是戏曲的生存环境有了明显的改善,“行业戏”的时代终于成为历史,戏曲现代戏创作也出现了突破“样板戏”模式的新迹象,尽管我们还不能对此过分乐观。创作投入的多元化,尤其是近年里以国家艺术基金为代表的跨地区创作投入的增长,都是现代戏的新机遇。近年里,各地陆续涌现出一批高质量的现代戏作品,如川剧《金子》、粤剧《驼哥的旗》、眉户《迟开的玫瑰》、秦腔《西京故事》、黄梅戏《徽州女人》、甬剧《典妻》、沪剧《挑山女人》、秦腔《狗儿爷涅槃》、上党梆子《太行娘亲》等等,尤其是河南豫剧院三团的豫剧《焦裕禄》,更是当代现代戏创作中思想性与艺术性兼具的代表作。如果从最近几届中国艺术节的“文华大奖”获奖剧目和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的入选剧目看,即使不考虑政策倾斜的因素,仅从艺术角度衡量,现代戏也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明显的优势地位。

川剧《金子》
现代戏的发展始终伴随着各种争论,而那些貌似围绕现代戏舞台表现形态的争论,背后也未始没有超艺术的动机。由于现代戏的舞台表现方式日趋成熟,围绕它的争论也愈益聚焦于政治与艺术的关系;只要能按艺术规律解决这个重大问题,跨过这个最后的难关,现代戏的前路就不再有大的障碍。戏曲现代戏的发展,终将冲破所有非艺术的约束。
三、新编古装戏影响深远成就斐然
当代戏曲舞台上的演出剧目不仅有大量传统戏和现代戏,还有另一类具有特殊重要性的剧目,即新编古装戏。
早在延安时期,京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就是红色戏剧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1949年之后的几年里,《逼上梁山》的编剧之一杨绍萱按同样模式创作的《新天河配》《新白兔记》和《新大名府》等剧目却因为被指具有“反历史主义”倾向受到严厉批评,他的这些作品甚至被周扬称之为“反历史主义者冒充马列主义而对历史进行新的歪曲”[11]的产物,按“历史主义”的态度创作“新编历史剧”,成为戏剧界一时的共识。然而,那些在流传广泛的古代文学作品(如《三国演义》《水浒传》和《包公案》等小说和说书、弹词等民间叙事)基础上改编的戏曲作品,还有用完全虚构的方式创作的古代题材作品,都很难被纳入“新编历史剧”的范畴之内。传统戏题材十分丰富,但是仍有相当部分民间叙事是改编的盲区,在此基础上创作的戏曲新剧目,当然也很难称为“新编历史剧”。越剧《红楼梦》、粤剧《搜书院》、莆仙戏《团圆之后》和京剧《杨门女将》等等,都是20世纪50年代很有代表性的新编戏曲古装戏而非所谓“历史剧”;改革开放之后出现的越剧《五女拜寿》、京剧《曹操与杨修》和黄梅戏《徽州女人》、梨园戏《董生与李氏》等影响广泛的戏曲优秀剧目,都无法归之为一般意义上的“新编历史剧”。当1960年齐燕铭代表文化部提出要实施“大力发展现代题材剧目;同时积极改编、整理和上演优秀的传统剧目,还要提倡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创作新的历史剧目,三者并举”[12]的戏曲方针时,这个后来广为人知的“三并举”方针,其实存在明显的缺失,它并没有包括并非基于严格的史实创作的古代题材戏曲新作,而无论是在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不仅以古代生活为背景创作的戏曲作品比现代戏更受欢迎;而且在众多古代题材作品里,最受欢迎的恰恰不是那些按所谓“历史主义”原则创作的作品,而是包含大量虚构的古代题材作品。这里所说的艺术虚构,不仅包括编剧者个体的创造与想象,还包括历史上的民间艺人甚至普通民众的创造与想象。
戏曲演员在古装戏演出中更能发挥传统表演的优势,而以虚构的古代生活为背景的作品与现实生活存在的明显距离,更能确保创作者有自由发挥的空间。杨绍萱和张庚曾经先后建议用“故事剧”或“古代故事剧”等特殊的称谓来包含此类剧目,但是未能获得广泛认可。在某种意义上说,恰恰是这些艺术化地虚构的古代题材戏曲作品代表了当代戏曲最高水平并不为过,将它们与“新编历史剧”一并称为“新编古装戏”,或许更符合实际。
如前所述,从1949年直到1964年因昆剧《李慧娘》受到激烈批判导致所有古装戏退出舞台之前的这15年里,新编古装戏和传统戏始终是戏曲舞台上两大类受欢迎的剧目。20世纪50年代,除了传统戏的整理改编外,古代题材的新创作卓有成就,李少春自编、自导、自演的京剧《野猪林》,和翁偶虹创作并获得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剧本奖的京剧《将相和》,都是最初的新编古装戏里极具影响的作品。在此之后的若干年里,全国各地都有大量新编古装戏,其中不少是根据传统戏做了较大幅度改编的新作,它们与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川剧《红梅记》、晋剧《打金枝》及各剧种共有的“三国”“水浒”“杨家将”、包公系列等传统戏,一并支撑着戏曲演出市场。对于那些没有自己传统剧目系列的剧种,新编古装戏的作用就更为关键,在20世纪50年代数以百计的新剧种里只有吉剧等少数几个剧种存活至今,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吉剧有王肯创作的《包公赔情》《桃李梅》等优秀的新编古装戏,正是它们让吉剧这个新剧种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

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
正如昆剧《李慧娘》、京剧《谢瑶环》和《海瑞罢官》、柳子戏《孙安动本》后来遭受批判时被指称的那样,这些新编古代题材剧目、尤其是那些“新编历史剧”中的相当部分的新剧目,确实自觉不自觉地沾染了始于《逼上梁山》的影射现实、贴附时事的风气,对它们的批判当然包含了政治陷害的成分,但如何让历史题材戏剧作品摆脱工具化的魔咒,始终是该时期戏曲领域的难题。邓小平1979年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的《祝词》中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3],解除了一直束缚着历史题材戏曲创作的工具论的绳索,新编古装戏的创作才有了新的广阔天地,这也是改革开放对戏曲最重要的影响。
在新时期的新编古装戏里,京剧《徐九经升官记》《膏药章》这类独特的充满喜剧风格的作品,尤为观众喜爱;在20世纪80年代的探索性戏剧创作潮流中,戏曲界也出现了桂剧《泥马泪》、湘剧《山鬼》、川剧《潘金莲》、京剧《洪荒大裂变》、淮剧《金龙与蜉蝣》等有影响的探索戏曲,为中国当代新编古装戏增添了亮色。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顾锡东的《五女拜寿》是浙江小百花越剧团艺术上的奠基之作,全国各地无数剧种剧团都有改编移植;他为当代越剧的代表人物茅威涛写的《陆游与唐婉》,无疑是改革开放40年来创作的无数越剧新剧目里首屈一指的作品。郑怀兴、王仁杰、罗怀臻在戏曲新编古装戏创作中都有重要贡献,他们是少有的几位几乎一直坚持从事新编古装戏创作的戏曲剧作家。郑怀兴为山西太原青年晋剧实验剧团主演谢涛量身写作的晋剧《傅山进京》和《于成龙》,罗怀臻的淮剧《金龙与蜉蝣》和昆剧《班昭》、李莉的京剧《凤氏彝兰》《成败萧何》,都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陈亚先的《曹操与杨修》(上海京剧院尚长荣、言兴朋主演)和王仁杰的《董生与李氏》(福建泉州梨园戏实验剧团曾静萍、龚万里主演),不仅是近年来新编古装戏的巅峰之作,也毫无疑问代表了新时期戏曲创作的最高水平。
进入21世纪,新编古装戏创作在戏曲领域占据多年的显著的支配性地位出现了动摇的迹象,在传统戏和现代戏的双重夹击下,新编古装戏的影响力正有逐渐下降之迹象。这一现象当然与政策导向有一定的相关性,与演出市场的萎缩也有关联。在相对正常的演出环境中,市场代表了普通观众的趣味与选择,它足以与代表政府意志的政策导向构成良性博弈。但是当市场环境不佳时,政策就成为单向度的力量,戏曲艺术家创作新编古装戏的意愿普遍下降,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新编古装戏和传统戏看似在舞台形态上较为接近,但是从戏剧结构方式与人文内涵方面看,实与现代戏有共生关系。因此它最易于汲取传统滋养,又可与现代戏互为借鉴,很多新编古装戏的优秀编剧、导演和唱腔设计者同时在现代戏创作中亦有显著成就。无论戏曲剧团和演员还是主创人员,他们多数的情感取向更偏于新编古装戏,这是无须避讳的事实。这就无怪乎70年来的戏曲创作中,新编古装戏成就最大,在可见的未来,新编古装戏仍将是戏曲创作演出旗帜性的存在。

晋剧《傅山进京》
四、余论
新中国70年戏曲创作演出成就的总结需要双重维度——戏曲剧目和戏曲舞台演出。无论传统戏、现代戏还是新编古装戏,都只有在传承戏曲独特的舞台呈现时,才真正是戏曲的。戏曲舞台表现形态在20世纪50年代初苏俄文艺理论强势影响下,一度遭遇严峻挑战。在全国各行各业都要接受苏联专家指导、按苏联模式改造的大环境下,境遇一度极为尴尬。
苏联模式对戏曲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强行要求它必须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无论是在苏联还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现实主义”都远远不只是一种创作方法,不只是众多文学艺术流派之一,它简直成了唯一正确的创作与表现模式,这里所说的“正确”不仅是艺术上的,更是政治上的。是否遵循现实主义原则成为艺术家是否接受新社会的试金石和分界线,尤其是在“戏改”的大背景下,现实主义原则更构成对戏曲界的巨大压力。所以当我们看到包括梅兰芳在内的表演艺术家都纷纷强调戏曲有“现实主义传统”[14]时,不难从中体会戏曲艺术家们化解这一压力的身姿。
假如我们以为表演艺术家的躲闪就可以完全摆脱现实主义艺术观念对戏曲的影响,那就太天真了。如果说为尊重知名戏曲表演艺术家与广大观众的意愿,传统戏的演出还总算能基本保持传统样式的话,那新创作的剧目却不可避免地受现实主义理论的影响,而“导演制”在戏曲创作中全面推进,更起着明显的助力作用。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各地戏曲剧团纷纷开始设置专门的导演职位,由其负责新剧目的编排工作,无论这些“导演”是否曾经接受苏联专家的直接熏陶与培养,他们从事导演工作的艺术观念与理论资源无不来自于现实主义体系。其中现代戏的创作受其影响最为直接和明显,由于在服饰与妆扮上不能像古装戏那样明显区隔于日常生活,表演者顿时丧失了沿用传统身段的理由,符合现实主义理念的生活化表演成为一时的风气。戏曲界和观众将这些作品讥之为“话剧加唱”,但是对创作者而言,这或许是在现实主义的强大压力下让戏曲音乐和演唱得以勉强保留的最好的方法。诚然,艺术家们一直有各种不同的借口让戏曲表演的特殊魅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持续,即使是现代戏的创作演出,终究需要以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吸引观众,因此戏曲包括唱念做打等明显非现实主义的丰富手段,仍然打着“现实主义”旗号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存在,只是它存在的合法性的疑虑,始终伴随在当代戏曲的发展道路上。
在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现实主义理念对戏曲更为直观的影响是舞台美术设计领域。戏曲传统的虚拟化表演与其简约的场景在美学上是互为援奥的整体,它体现了物质匮乏时代艺术家解决多变的戏剧场景之昂贵成本的智慧,但是在物质丰裕时代,“简约”也可能被解读为“简陋”,晚清年间的宫廷演剧就曾经有通过繁复的舞台置景炫耀其豪奢的现象,民国年间上海滩的机关布景也以耗费不菲的写实化景观为荣。现在追求逼真的写实置景有了更“艺术”化的理由,它成为现实主义理念最重要的舞台实践。舞台上的写实置景无论在现代戏还是新编古装戏都被普遍使用,传统戏的演出也按这一理念加以改造,场景与表演的冲突,深刻体现了戏曲表演艺术传统对现实主义艺术观念的妥协。
黄佐临1961年曾经指出“梅兰芳戏剧观”与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的戏剧观的差异。改革开放之后,他的这一重要见解唤醒了戏曲界的自我认知;更因为西方现代派戏剧的引进,让现实主义丧失了在艺术理论中的霸主地位,戏曲舞台美术观念的整体演变和对戏曲传统表现手法之价值的再确认,使“戏曲化”成为新的普遍追求。
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戏曲舞台上,写实化的布景逐渐退潮,谢平安、杨小青等戏曲演员出身的导演充分展现了熟悉戏曲化表演手法的优势,张曼君、韩剑英为代表的新一代导演进一步强化了戏曲化的趋势,跨界进入戏曲领域的一批话剧导演也在他们的带动下,共同让新世纪的戏曲舞台向戏曲化方向回归。近年出现的滇剧《水莽草》和芗剧《保婴记》说明戏曲化趋势不再只是地处文化中心的大剧种的艺术家的自觉追求,覆盖面与影响力早就遍及全国各地,基本成为整个戏曲界的共识。“戏曲化”成为普遍接受的理念的另一个重要标志,是曾经坚持“话剧加唱”模式的河南豫剧院三团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他们引进了传统功底深厚的优秀豫剧演员贾文龙,让他担任新剧目《焦裕禄》和《重渡沟》的主角,在这些新作品里,贾文龙深厚的基本功获得了充分展示的机会,同时也让这些原本很容易陷入“话剧加唱”模式的剧目,有了浓厚的戏曲化色彩。

豫剧《重渡沟》
从现实主义理论的主导地位到戏曲化成为艺术家的普遍追求,体现了70年来戏曲发展的基本路径,亦是70年戏曲舞台上最令人关注的现象。在它背后体现的是戏曲的价值体系从迷失到重新恢复文化自信的完整过程,其意义远远超出了简单的舞台表演层面。更重要的是,戏曲化的舞台表现超越题材类型,在戏曲化的旗帜下,传统戏、现代戏和新编古装戏重新成为具有艺术共性的整体,或许这才是戏曲现实中能给人们美好遐想的新迹象。
我们或可以将它看成新中国70年戏曲发展的主轴,展望明天,戏曲正因此才有光明的未来。
[1] 此前的当代戏曲史著多把这个委员会与1949年10月成立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局、1950年7月成立的文化部戏曲改进委员会混为一谈,尽管其中的人员有不少重叠,但性质截然不同,这个于1949年10月2号正式成立的“中华全国戏曲改进会”既非政府部门,也不是政府咨询机构,而是全国文联的团体单位。
[2] 其后艺术局还分出了艺术二局,负责戏剧之外的艺术门类管理事宜。
[3] 张庚:《对于一些清规戒律的看法》(1956年6月11日),《第一届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文件》,未公开发表。更完整的叙述收录在《张庚戏剧论文集(1949-1958)》(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中的《正确地理解传统戏曲剧目的思想意义》,他的大会报告题为《清除清规戒律,端正衡量戏曲剧目的标准》,在公开发表时对标题做了修改。
[4] 《文化部关于开放“禁戏”的通知》(1957年5月17日),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戏曲志•北京卷》,1999年,第1439页。
[5] 杨兆峰:《沈阳市久不上演剧目展览周简记》,沈阳戏曲志编辑部编:《戏曲资料汇编》1985年第一期,第301页。
[6] 刘芝明:《大胆放手,开放戏曲剧目——在第二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戏曲志•北京卷》,1999年,第1425-1433页。
[7] 蔡文金:《春风送暖百花香——忆1978年春邓小平同志关怀川剧艺术》,陈国志主编:《川剧艺苑春烂漫》,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1页。
[8] 《文化部党组关于逐步恢复上演优秀传统剧目向中央宣传部的请示报告》(1978年5月1日),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戏曲志•北京卷》,1999年,第1562-1564页。
[9] 《周扬同志谈戏曲表现现代生活问题》,《戏剧报》1958年第15期。
[10] 刘芝明:《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戏曲而努力——1958年7月14日在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上的总结发言》,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戏曲志•北京卷》,1999年,第1453-1454页。
[11] 周扬:《改革和发展民族戏曲艺术——1952年11月14日在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国戏曲志编辑委员会等编:《中国戏曲志•北京卷》,1999年,第1360页。
[12] 《戏曲必须不断革新》,《人民日报》社论,1960年5月15日。
[13]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一九七九年十月三十日),《文艺研究》1979年第4期,第6页。
[14] 梅兰芳不止一次刻意强调“毫无疑问,无论京剧或各兄弟剧种都是有其长远的现实主义传统的”(如1954年9月18日梅兰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会议上的发言,并且多次论述戏曲(京剧)的“现实主义”表演体系,见梅兰芳《对京剧表演艺术的一点体会》等),参见傅谨主编:《梅兰芳全集》第一卷,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
作者:傅谨 单位:中国戏曲学院北京戏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基地
《中国文艺评论》2019年第8期(总第47期)
《中国文艺评论》主编:庞井君
副主编:周由强 袁正领 胡一峰 程阳阳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