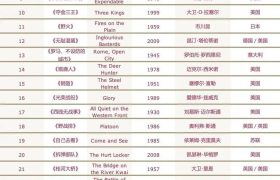11月20日,《气球》首映,
被誉为“年度最好的国片”,
有人形容是“一场对灵与肉的礼赞”。

这是藏族导演万玛才旦的第7部长片,
也是他的电影第一次有机会在全国院线放映。
影片围绕“被偷走的避孕套”展开:
家里的小孩把避孕套偷走当气球吹着玩,
间接导致母亲意外怀孕,
想打胎却被丈夫勒令不许,
生,还是不生?
女性是为了生孩子活在这世界上的吗?
藏人信仰佛教,堕胎等于杀生怎么办?……


一条专访了万玛才旦导演,
我们从电影聊到了现实中的拉姆案,
他说:“女性要觉醒,
但单单有自我的觉醒是不够的,
她还需要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撑。”
自述 万玛才旦 撰文 刘亚萌 责编 石鸣


万玛才旦50岁了。他讲起话来温言细语,声音很低。很难想象就是这么一个看起来谦逊甚至腼腆的人,十年前以一己之力开启了“藏地电影新浪潮”。
15年来,他拍了7部长片,统统都是藏族题材、藏语对白。尽管这些作品一再成为威尼斯电影节等知名电影节的常客,但从未上过主流院线。《气球》是头一回。
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点映会后,观众的反响总是异常热烈。人们纷纷说,这是他们看过的“万玛才旦最好的电影”,“万玛才旦用情最深的电影”。


《阳光灿烂的日子》剧照
把避孕套吹成气球,曾经是《阳光灿烂的日子》的经典桥段。有人说,姜文给了避孕套“气球”以生命,万玛才旦则为避孕套“气球”赋予了灵魂。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马小军偷偷吹破了父母藏在笔记本中的避孕套,他悄悄把破了的“气球”放了回去。于是,他家里多了个弟弟。
《气球》里,女主角卓嘎的两个儿子把她藏起来的避孕套偷走当玩具,她也因此意外怀孕了,但却非常纠结,因为她不想生。
生,还是不生?这是贯穿《气球》全片的问题。我们看到,仍旧穿着传统藏族服饰的女人已经开始觉醒,怀疑自己“与生俱来”的生育使命:女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觉醒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反思生育行为,反思女性地位,进一步延伸到了反思自己的信仰。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上师认定是家里长辈的转世。这下所有人都逼她把孩子生下来,包括她自己的亲儿子。她挣扎而绝望:上师说的就一定对吗?丈夫大怒,一巴掌扇过去:你竟然敢怀疑上师?
在上海点映时,有一位女观众非常感慨,因为电影里的场景似曾相识:女性好友怀孕了,犹豫要不要生,生育这件事的重大,不仅在于对女性个体的影响,更在于对一个家庭,“我没有立场告诉她一个确定的结论”。
迄今为止,万玛才旦所有的电影都是自编自导。在成为电影导演之前,他首先是个小说家。先写了十年小说,才开始拍电影。
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来自他的一个短篇。他的代表作如《塔洛》和《撞死了一只羊》,都是由小说发散而来。圈内评价说,他的电影都有一种“知识分子趣味”。

《气球》也有小说版本。甚至于他还在片中特意安排了一个中学男老师的角色,也写了一本小说叫《气球》。这个角色是他对自身的指涉吗?“并不是”他笑道,只是无伤大雅的一个文字游戏而已。
他对他笔下的所有人物,都有一种造物者的慈悲。在北京的超前点映现场,观众好奇《气球》“女性视角”,却被一旁的陈丹青挡了下来:“这不是女性视角,是万玛视角,他对片子中的每个人物都抱有同情心。”
影片以避孕套吹出来的“白气球”开场,儿子迫切地渴望一只气球作为玩具,父亲答应了去买,却迟迟没有付诸行动。同样也是这个男人,导致了自己妻子的意外怀孕,面对妻子拒绝生育的想法,他解决问题的终极方式只剩暴力。

父亲最终去镇上给儿子买回了红气球,然而,所有的纠结都已发生,所有的痛苦女性也都已经承受。红气球最终飞上了天空,谁也没有能够拥有它。“这是我一开始就想好的结局。”
以下为万玛才旦的自述:
在藏地,性话题是比较敏感的
《气球》的灵感是偶然间诞生的。那是2010年的秋末冬初,我要去中央民族大学见朋友,路过中关村,突然在天空中看到一只红色的气球在飘。

侯孝贤《红气球之旅》剧照
我觉得那是一个特别好的意象,立即想把它拍成电影。当时已经有很多以气球意象为主题的经典电影。我的电影,怎么才能跟藏地的当下发生关联?
我马上就想到了“白气球”,避孕套。
故事背景设定在90年代中后期,当时全国实行计划生育,藏地也不例外。卓嘎家有三个孩子,大儿子上中学,两个小儿子即将上小学。家里还有丈夫,以及孩子的爷爷。有了人物,整个故事就慢慢建构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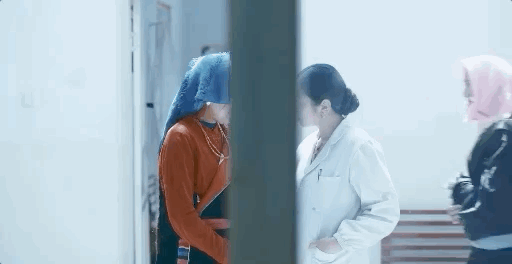
在藏地,性这个话题是比较敏感的。片中的人物,凡是在聊到性或者避孕套的时候,就会有点闪烁其词。
卓嘎去卫生院,遇到男医生,不愿开口,偏要等女医生。等女医生真的来了,问她要看什么病,她也还是羞于启齿。两人到了门外,避开周围的人,压低声音才敢谈论这个事。
拍摄时,我们就在中间隔着一层窗户之类的东西,好像镜头在窥探,营造一种私密感。

片子里有一个情节,卓嘎的小孩拿着避孕套吹成的气球,和邻村小孩换玩具,邻村小孩的家长发现了,非常愤怒,找上门来跟卓嘎老公大打了一架,骂他们家不知廉耻。
这个情节是小说里没有的,是拍电影时新加的,也是突出一种性羞耻的感觉。
《气球》的短篇小说大概1万多字,但是一个电影长片的剧本通常需要3到4万字,所以需要扩充。在这个基础上,我还添加了一条人物线,讲卓嘎的妹妹,因为情伤受挫,出家当了尼姑。

尼姑妹妹之前的感情经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片子里没明说。但通过很多细节,你能隐隐地感觉到,尼姑妹妹可能曾经跟这个恋人在一起怀孕了,打胎了。在佛教里面,杀生是最大的罪过,所以她为了赎罪,就去了山上的寺院修行。
卓嘎想堕胎,等于她此刻也遭遇了“杀生”困境,两姐妹的命运形成了一种参照。

另外,我还有意把“人的世界”和“羊的世界”做了一个对比。
羊的世界是下崽越多越好。卓嘎家有一只母羊,2年没产崽了,就会被认为是无用的,养肥了被卖给屠宰场。
人的世界是刚好相反的,人口需要节制,要使用避孕措施。电影里面出现医院的宣传栏里“优生优育”的标语,都在推广这个观念。

我其实一直是魔幻现实主义
藏族是一个全民信仰佛教的民族,“转世轮回”等等一些概念是融入到日常生活里的。
影片里,卓嘎的大儿子被认为是他奶奶的转世,因为他生下来背上就有一颗痣,和他奶奶的一模一样。
我本人有过类似的经历。我从小跟我爷爷生活在一起,他把我当做他舅舅的转世。
爷爷的舅舅是一个宁玛巴的僧人,他对爷爷特别好,教授他经文和佛教的仪轨(礼法规矩)。可能因为我在懵懂的幼年时期,曾说过我来自某个地方、有很多经文之类的话,所以爷爷就坚信我是他舅舅的转世。
也因为如此,家里会给我一些特殊待遇,提供更好的环境和条件让我去学习。

《撞死了一只羊》剧照
我早期的电影风格比较平实,去年《撞死了一只羊》出来之后,大家觉得我的电影开始变得有些魔幻了。
这部《气球》里面,魔幻的段落更多。比如有一场戏是“梦中捉痣”,弟弟把哥哥背上的痣,很轻易地拿下来,给哥哥看,然后他们嬉笑着在沙漠上奔跑,跑向蓝色的青海湖水。

还有卓嘎姐妹的“窗前谈话”。年轻的妹妹(未出家时留着长发)缓缓走来,她美丽地笑了一下,停在姐姐的身后,而姐姐的表情有点恍惚。这里表现出,姐姐和当年的妹妹的命运产生了某种重叠。
其实对我自己来说,并没有刻意地转型。我的小说里很早就有了超现实主义的元素,比如在《乌金的牙齿》和《嘛呢石,静静地敲》里,现实与梦境,此时和彼时完全是没有界限的。
《撞死了一只羊》的剧本,在《塔洛》拍出来好几年之前就已经有了。只能说早期拍电影,会受到很多外部条件的局限,那时只能拍一些现实题材的。

《塔洛》剧照
以往,我拍的都是生活在“故土”的藏族人,接下来,我的题材可能会做一些改变,比如去拍生活在城市里的藏族人。
之前有个藏语杂志发起了一个同题小说征文,题目就叫“城市生活”,请了四个作家,每人写一个中篇,我就写了一篇。
我觉得成为一个城市人是要经过几代人的积累的。现在生活在西宁、成都的藏族人,几年前可能还是个牧民,对于“城市人”的身份,他们肯定有很多困惑和纠结,这样的状态,我觉得特别有趣,特别值得去拍。
有机会的话,我也想尝试藏族之外的题材,拍汉语电影。

拍出藏地的美,没想象中那么容易
《气球》的剧本我大概花了2周就写好了,但是因为种种因素,当时没法拍,我就把剧本改写成了小说先发表。
2018年,机缘到了,立项和投资都到位了,8月份我们就开始拍摄。中间因为《撞死了一只羊》去了一趟威尼斯电影节,停了10多天,回来继续拍,总共拍摄了40多天。
小说里面写羊的文字比较多,电影里面展现得比较少。这是因为我们有现实困难。电影拍摄的时候是八九月份,其实羊的交配季节已经过了。
可能大家觉得藏地很美,随便拿一个傻瓜相机去拍,都能拍得很好看。但其实在拍电影的时候,是挺有难度的。因为很多地方的风景都是一样的,没有太多的变化,一部电影看一两个小时,观感上会比较枯燥。


我们到处去看景,走了很多地方,最后决定在青海湖边。它周围有草原牧场、有沙漠,青海湖从早晨到黄昏,色彩一直在变化,这就让整个电影的氛围营造有了基础。像“梦中捉痣”那场戏,我们就是在青海湖边的一个沙漠里拍的。
这个电影里的人物都处于一种焦灼的状态,所以我们用了手持长镜头跟拍,跟随这个人物,去抵达他的内心。

比如“火中取书”那场戏,卓嘎为了断掉妹妹的念想,把妹妹以前的恋人写的书,扔进了火塘。妹妹很着急,徒手从火里把书抢出来,手也被烧伤了。
这场戏是一镜到底,我们拍了很多遍。火力大小、书烧起来的程度、把手伸进火里的时机、镜头的推移,都需要恰到好处。演员的手其实是做了一些防护措施的,但肯定也是有一些风险吧。
但是,正是这种一镜到底跟拍的方式,能够更加强烈地凸显出妹妹对以往情感的那种期待。不用太多台词,只通过她的行动,观众就已经感受到那种刺痛了。
如果是固定镜头、来回切的方式,我觉得那种代入感就会弱很多。

我没想过拍一部女性主义电影
这部片子是讲生育的,很多人说在这部电影里看到了女性主义的东西。比如女医生对卓嘎说“我们女人又不是为了生孩子才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以及最后卓嘎对妹妹说,有点羡慕她出家当尼姑,无牵无挂。
这两年女性主义的话题很热,但我的初衷其实并没有这么一个先入为主的东西。卓嘎的处境,也让她不可能像女医生一样彻底觉醒。
影片里,卓嘎家里“5男1女”的性别局面,是一个巧合。就算爷爷的角色换成是奶奶,或是卓嘎肚子里的孩子被认为是她自己父母的转世,她丈夫觉得家里经济条件不好,不想生,她非要生下来,这样一个故事在我这里也是成立的。

关于丈夫的暴力问题,他确实打了她一巴掌,因为他的父亲刚去世,情绪很焦灼。然而他是有反思能力的,第二天向妻子承认错误,讨论未来的生活。所以我对这个角色也抱有一种同情心。
但是女性主义的议题之所以被热议,我想也是有原因的。像今年9月曝出来的拉姆案,我们看了报道都很震惊。

藏族女性拉姆在家中被前夫用汽油焚烧而亡
我看了很多藏族知识分子写的文章,大家都感到很可惜。藏族知识界进行反思和讨论后,形成了一个共识:女性要觉醒,而且是彻底的觉醒。单单一个自我意识层面的苏醒是不够的,她还需要经济等多方面的支撑,才能有一个真正的反抗。
在这个议题上,可能女性知识分子的思考会更多一些。她们会搜集相关案例,分析其中的共性,找出解决办法。
还有一些人,会付诸行动,到基层去普及新观念。
前段时间,西藏社科院有一个藏族的博士,叫白玛措,她看了《气球》以后,受到了启发,前往藏地边缘牧区,对“节育措施、生育观念”进行了详尽的田野调查,写了一篇论文,论文题目就叫做《严肃的气球——西藏牧区妇女生育变迁》。
她访谈了82位已婚育龄妇女,提到在西藏牧区最广为使用的避孕措施,是静脉避孕和宫内节育器,男性使用安全套的概率比较低。

我的微博还转发过她的文章,里面有一段她和受访者的对话很有意思——
G:我已经有2个孩子了,不想再生。现在最想知道的就是怎么能不怀孕。我以前上过环,身体不适应,又取了。
我:你的丈夫可以采取避孕措施啊。
G:啊 男的也可以上环?
我:可以使用避孕套。但是也要用质量好的,不然,劣质的那种对你身体也有伤害。
G:下次我去拉萨时,打电话联系你,你能不能帮我给超市的售货员说质量好的那种牌子。
我:有一种牌子叫杜蕾斯
G: སྟུ་ལ་གཟེད།/Stu la gzed/杜蕾斯(大笑不止)…
《气球》这个片子拍的是九十年代的事情,那么到了现在,藏区女性也都不太愿意生了。农村里一般都是两个孩子,多了就有经济压力。
影片是一个开放式结尾:已经有三个小孩的卓嘎跟着妹妹去了寺庙,她到底要不要把孩子生下来,甚至于她会不会出家,我们不知道她最后是如何决定的。
我很难替我的人物做出一个抉择,未来在她们自己手里,我没办法帮她们把握自己的命运,所以最后我让气球飘走了。

它从小孩的手中脱落,越飞越高,几乎要消失不见了。它本身就有一点象征含义,象征着生命或者希望,大家在不同的空间里,抬头看着这么一个即将消失的气球。你也不能改变什么,只能是一种怅然地,无奈地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