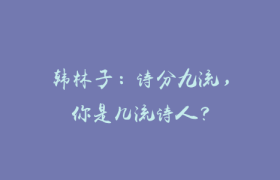新华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张漫子)8月23日,《新华每日电讯》刊载题为《徐则臣:作家要将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作品》的报道。
得知《北上》获奖时,徐则臣正在上海书展为新作《从一个蛋开始》做签售。茅奖揭晓的消息传来,现场沸腾了,热情的读者将他包围,为他祝贺。还有读者冲到台上求合影。100多本深蓝封皮的新书一抢而光。
面对读者、出版人的祝贺,徐则臣频频道谢。
(小标题)运河是一面镜子
本届茅奖的获奖作品《北上》是一部写运河的小说。
杭州、无锡、淮安、北京……河畔的城市收录了大运河的古今。从婚俗、船事、水文、景观,到摄影、戏曲、收藏、绘画,由南到北,从古至今,包罗万象。
经时间的开凿,运河人的气息汇入这条河,中国的历史、运河边的故事也聚到这条河上。“我们的四大名著如果找一找,没有一部是跟运河没有关系的。你看林黛玉入京,就是从京杭运河抵达张家湾,弃船登岸。”徐则臣说。
京杭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它沟通了北京到杭州之间的地理,加强了南北文化的交流,造就了沿线城市的繁华。
几年前,一位运河专家陪徐则臣在通州作运河考察。当专家指着一片房屋和树木说“100年前运河就在那里”的时候,徐则臣感受到曾经旷世风华的运河正面临新的时刻。
2014年,大运河申遗成功。“这是一个重新审视运河、唤醒运河的契机,也是我动笔写《北上》的开始。”徐则臣说。
于是,《北上》以历史与当下两条线索,写了这样一个故事。一百多年前,意大利人“小波罗”和弟弟怀着对马可波罗书写的美好中国的期待,分别来到中国。谢平遥作为翻译陪同他们走访,并先后召集起挑夫邵常来、船老大夏氏师徒、义和拳民孙氏兄弟一路相随。他们从杭州、无锡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北上,将一个想象中的“马可波罗的中国”,转化为一个耳闻目见、鲜活生动的中国。而当他们最终抵达大运河的最北端——通州时,小波罗意外离世。同年,清政府下令停止漕运,运河的实质性衰落由此开始。
一百年后,中国各界重新展开对运河功能和价值的文化讨论。当书中谢平遥的后人谢望和与当年先辈们的后代重新相聚,恰逢大运河申遗成功之时,运河人之间原来孤立的各个故事片段,最终拼接成一部《清明上河图》式的恢宏图卷。
在《北上》中,大运河成了一面镜子,河中有一个民族的秘史。徐则臣在《北上》中勾勒出这样一幅夜航船的画面:千里长夜,灯火为伴。谢平遥船舱夜读,想到1839年龚自珍自京南归,而他此时北上,南归是重返故里,北上却是无所知之地,不禁神伤。
看得见的是运河,看不见的是来时与去往。大水汤汤,溯流北上,这一行崎岖渺茫,还乡却不知路在何方。“这其中,有知识分子面对古老中国遭逢巨劫奇变的举目茫然,运河之子在漕运断流之前的隐忧与敏感,中西文明碰撞之时国人寻找精神原乡与到世界去的矛盾与撕裂……这一个民族的秘史与旧邦新命,最终尽皆赋予了眼前这一条大河。”《北上》的责任编辑陈玉成说。
(小标题)靠着这条河想象世界
用福克纳的话说,很多作家都是从自己“邮票大”的故乡出发展开自己的文学创作。
用徐则臣的话说,京杭运河是他的文学原乡。“运河对我很重要。20多年的写作中,我的小说在大河上下游走,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开辟出一个纸上的新世界。”
生于江苏的徐则臣从小生活在水边。“对农村孩子来说,水就是我们的天堂,那个时候没有变形金刚,没有超人,连电视都没有。但是我们有水,可以打水仗、游泳、溜冰、采莲……”徐则臣回忆道。
初中校门前是江苏最大的一条人工运河。徐则臣记得,“一到冬天,宿舍的自来水管冻住,我们就一大早端着牙缸、脸盆往校门口跑。石安运河的河面上水汽氤氲,河水暖人。”
“如果把想象力固定在一点,而这点是一个流动的点,你会发现世界将随着这个流动的点不断地往远处跑。你想象的世界会不断开阔。”徐则臣说。
在素有“运河之都”美誉的淮安生活的几年里,他每天在京杭运河的两岸穿梭,耳闻目睹的一切促使他审视运河与城市的关系:“从韩信到吴承恩,从近代摄影家郎静山到京剧麒派创始人周信芳,都出生在淮安,这样的巧合说明了什么?在运河的运输功能弱化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看待部分沿岸城市的‘衰落’,以及运河存在于此时的意义?”
本着对运河的天然兴趣,但凡涉及运河的影像、文字、研究乃至道听途说,徐则臣都要收集、揣摩,以至于一闭眼,1797公里就活灵活现地出来了。
然而,了解越多,越会发现了解得还不够透彻。2014年,徐则臣决定重走运河。“这一次,我带着眼睛、想象力、纸笔行走。我看,还要看见,看清楚,看清楚河流的走向、水文,看清楚每一个河段的历史和现在,看清楚两岸人家的当下生活。”
这是个大工程。京杭运河从南到北1797公里,跨越浙、苏、鲁、冀四省及津、京两市,平常工作忙,杂事多,难以一次性沿运河贯通南北,徐则臣只能等待出差还乡等机会。
就这样,四年间断断续续的一次次“南下”后,徐则臣用双脚把运河丈量了一遍。部分疑难河段还反复去了多次。徐则臣说,“没办法,大运河贯通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加上中国南北地势起伏、地形复杂,河水流向反复多变,不亲自到现场做详尽的田野调查,各种史志资料中的描述根本弄不明白。尤其是几处重要的水利工程,比如山东南旺分水枢纽,仅凭纸上谈兵是理解不了的。”
尽管现在荒草萋萋,河道淤积,当年“七分朝天子,三分下江南”的遗迹所存鲜见。“但到现场一站,只10分钟,就比之前苦读10天的资料都管用”。做足了充分的田野调查,徐则臣豁然开朗。
“当你对每一朵浪花,某一根水上的草,它的想象不断展开时,这条河会越来越长,你想象的世界越来越大。”他说。
小说写完,徐则臣一边散步,一边听陈铎解说的《再说长江》。在听到片头曲里一段录音中,有一滴水落进水里的非常清晰的声音,而后又听到长江边一个小女孩在芦苇里非常清脆的咯咯咯的笑声,徐则臣的眼泪一下掉下来。
“和一条河耳鬓厮磨了这么长时间,在我听来,这些声音是那样悦耳。如果哪个读者能从我的书里找到一两个细节,能像我听见那滴水声、那个笑声一样心动,我觉得就值了。”徐则臣说。
(小标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
某种意义上,《北上》见证了徐则臣的中年写作。
写作《耶路撒冷》的时候,徐则臣三十出头,曾以一位青年人的心态与豪言,要进入宽阔复杂的中年写作,甚至认真想象过中年写作究竟是什么样子。
到《北上》告成,他已身处中年写作当中。他发现自己要面对和处理更为复杂的问题,作品中要容纳更丰富的社会历史和人生经验。
正因经历过《耶路撒冷》《王城如海》的锤炼,《北上》让41岁的徐则臣成为本届最年轻的茅奖得主,尽管比史上最年轻的茅奖得主、《芙蓉镇》的作者古华获奖时略大一岁,依旧有人将《北上》的胜出视作70后作家的一次胜利。
在此之前的文坛,70后作家的写作不可避免地陷入一种“进退两难”——前有拥有文坛话语权的,因亲历历史更迭、见证乡土逝去,有写不完的物是人非与社会深刻性的50后60后作家;向后面临着冉冉升起的、题材内容焕然一新、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学法则与价值观念的80后90后作家的冲击。没有太多故事和历史,70后作家夹在中间,看似格外黯然。
在徐则臣看来,作家除了才华与勤奋之外,一个关键在于能否看清自己,能否忠实有效地表达自己。“这一代作家中有众多葆有才华者,正沉迷于一些所谓的‘通约’的、‘少长咸宜’的文学款式,这样的写作里没有‘我’的切肤的情感、思想和艺术的参与,只能被称为假声写作。”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文学。徐则臣认为,70后看见的、听见的、想到的、焦虑的、希望的,应该借助有效的表达,提供一代人对世界的独特看法。这是70后作家的价值所在,也是文学的应有之义。
在写作中,徐则臣这样破题。不疾不徐、稳扎稳打的写作态度为他的写作打下了扎实的史料根基。为了保证作品“经得起推敲”,徐则臣总是下足繁复的案头功夫,将历史细节形之于物。“写每一部小说,自始至终我提醒自己最多的一句话是:要坐得了冷板凳。跟别人我不比聪明,比笨。”
更为可贵的一点是,他知难而进,掀开并剥开日益坚硬的历史茧壳,以雄健的笔墨寻回了历史记忆,为“到世界去”的文学版图提供了兼具历史维度和文明深度的参考系。
于是,运河上几个家族的百年故事有了内在的精神深度,其间有了关于起源与去处的疑问,有了关于兴盛与衰亡的探寻,有了关于战争与和平的思考,有了关于情感与心灵的救赎。
正如本届茅奖评委张莉所说,徐则臣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恢复了中国长篇小说应该有的长度、宽度和密度。“长篇小说就应当承载历史中最宏大、最沉重、最耀眼的那些内容。”评论家李林荣说。
文学在发展,每一代作家面对的世界不同、想法不同,表达方式和途径也不尽相同。徐则臣说,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在思考问题的过程中,“写作本身逐渐改变了我,修正了我过去的很多想法,比如我的历史观,和看待世界的方式。一代代作家要将自己的精神体温灌注进笔下的作品,通过‘有我的文学’和时代互动同行,与时代血肉相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