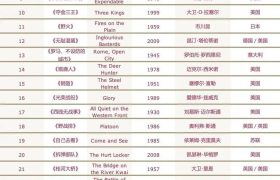引子:生于泥潭的人物似乎只能通过犯罪手段来改变命运,冲破阶级的枷锁。

影片《过春天》以高中生佩佩的视角为切入点,将故事格局放置在阶层割裂严重的香港城区,用青春少女青涩的、懵懂的“实现梦想”之路展现了边缘人物的原生渴望,一针见血地刺中了边缘群体的阴暗生活。
影片以破旧的老城区作为盛放罪恶与窘迫梦想的场所,展现国产青春片在脱离了海豚式温和的青春寓言之后,形似于鲨鱼的锋利批判意味。

不论是身为大排档帮工却仍然渴望成为“香港之王”的阿豪,还是以色视人、沉迷麻将、依靠男人,整日做着发财梦却最终失败的母亲,亦或是为了达成“去东京看雪”的梦想,逃离现状而宁愿犯法攒钱的女主人公佩佩,同处于边缘群体的他们正如同阿豪袋子里的那一群拥挤的小鱼,渴望像鲨鱼一样,成为生活更富裕、更自由的人。
佩佩身为生于香港的深圳人,“香港走读生”的大众定义上就携带着“逐利”“渴求翻身”等代名词,这侧面写出了佩佩身处校园这一基本生活环境的无归属感。她身处于香港而又不属于香港,只是作为香港的外乡人而存在,海关这边的香港,和海关那边的大陆,过春天同样是对青春期——成年的诠释。

片中台词:“过了这道海关,就要讲香港话”,再次凸显出佩佩身份的尴尬性,佩佩作为一个“水客”,过春天同样也是一种犯罪、冲破禁忌的象征。为此,开篇我们便知晓的佩佩的那个梦想——与朋友一同去日本看雪,这场驱动佩佩犯罪的行动目标就显得格外重要了。
而“雪”也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冲突动机,而是代表了一种远离拥挤、燥热的香港的一种罕见的“冷”,是对遥远生活状态的物化对象。可以这样说,她渴望的并非抵达东京,而是摆脱香港。所以在闺蜜满心期待日本之行的条条细节时,佩佩只是不断附和着。离开“香港——深圳”的一切都将是陌生的,她所期待的,也只是以离开香港为暗喻的逃离阶层的原始欲望。

导演在剧情安排上一波三折,以闺蜜与佩佩的争吵摧毁了东京行这一目标,并伴随着佩佩始终羞于承认的伤疤——母亲以色待人的形象——被揭开,闺蜜居高临下的带有侮辱性的指责摧毁了佩佩的自尊,由此她被迫重回边缘地位。当初始目标消失后,导演又设计了阿豪求助这一情节。使得这场双重偷运成为了另一场逃离现状的梦境,并带有青春少女的初恋情感的解救。
只是任务再度随之失败,动力再度戛然而止,生活归于平静。奔逃的计划失败,母亲最终放弃不服输的发财梦想,为了安分的主妇,佩佩也回归生活,象征“梦想”的鲨鱼被放回大海,不仅告知逐梦之旅的收尾,也表现了青春少女的无力与茫然。

在影像语言层面,影片在色调的明暗上将社会与校园割裂为两个世界,校园环境的影调光亮、明媚,充满青春气息,而社会场景则在香港拥挤的夜市中显得诡异、阴暗,充满危险。这两者的反向对比越明显,观众对于佩佩的处境就越不安,这也就更强化了佩佩这一角色对于“雪”这一目的的执着程度。
其次,在镜头语言上,影片多采用抖动镜头,多用斯坦尼康由佩佩的近景围绕进行拍摄,且多取景佩佩的侧脸,于表情表现中略显克制,试图加强观众的旁观感。但同时又十分注重将观众由旁观者向行动者这一观影视点的置换:在佩佩跳水的片段中,视角立即由甲板上的旁观者转换为了佩佩在水下的挣扎,音效立即增强,观众瞬间被拉入角色立场,成为了溺水者本人。

最后,氛围的渲染是影片的亮点,也由此贡献了影片最富张力的一场暧昧场景——佩佩与阿豪在阴暗的房间内,彼此互绑手机,房间内的影调为暖橘色,窗外偶有闪烁的车灯,镜头由远缓慢推进,在封闭空间里模糊的光线强化了音效,观众看不清阿豪的动作,而只有喘息声与胶带声此起彼伏,导演在该场景中把握了一种恰到好处的暧昧,展现了一种只有青春期独有的舒服、干净的情感,以细腻的笔触刻画了一场关于两名边缘人物间纯净的情感关系。

故事的发生地香港。在由大众定义的许多年来,都始终作为“罪恶之城”的代名词而存在。但显然,《过春天》想讲述的绝非是《小丑》中“哥谭逼人造反”的反向批判故事,它更想切入的是一个以高中生佩佩青涩视角下一个被香港极度放大化的阶层社会,且偏重于佩佩的个人感受,是一种内化的“内聚焦”视点。
影像中的老城区,阴暗的写字楼,狭窄的夜市,这些香港知名的城市特性此刻亦成为了佩佩的生活注解,它们所代指的关于“底层、肮脏、窘迫”等等代名词,作为大众意象被注刻进佩佩的行为定义中,成为了观众自然而然理解人物的手段。

而与之相对的闺蜜姑妈家所拥有的豪华房子、巨大游泳池,同时亦加强了闺蜜这个角色对佩佩而言,是人生目标似的羡慕对象。巨大的阶级落差不仅是香港的特写,也成为了佩佩选择“过春天”的重要动力。拥挤的香港街景,其作为风景的意义被消解,转而成为了观众窥探佩佩生活的犯罪场所。
而在这个场所中,我们亦能看到许多特定的符号,例如阿豪喜爱的鲨鱼所暗指的梦想,亦由侧面表现了阿豪与佩佩的相似性,一个想要成为鲨鱼,攀上食物链顶端,另一个想去看雪,逃离拥挤的环境,哪怕只是暂时的逃离。这些目标的本质都是要冲破阶级,试图解救边缘处境中的自己,以一种快捷的方式摆脱贫困。

这代表的是一种典型的底层逐梦视角,侧面隐喻了阶级固化的严重性,生于泥潭的人物似乎只能通过犯罪手段来改变命运,冲破阶级的枷锁。而之后母亲由性感衣衫换回主妇穿着,佩佩将鲨鱼由鱼缸放回大海,宣告着梦想的破碎。失败过后的妥协带着茫然,梦境的破裂导致目标消散,生活的意义消失,这正是作者由成长视角试图揭示的一种现代综合官能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