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场战争中,中国方面损失惨重:经营多年的福建水师被法国舰队在马尾港内全歼,屈指可数的国有军工企业福州船政局几乎尽毁。但在其他方向,台湾守军虽然遏制了法军深入,但危如累卵;而在中越边境要冲镇南关(今广西友谊关),清军击溃了法国远征军一部,迫使法国政府放弃军事解决,回到谈判桌前。
战后中法签署了《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又称《中法新约》):清政府放弃了对越南的宗主权,承认法国与越南签订的各项条约有效,撤退驻越军队,开放中越边境口岸,并承诺在关税上给予法国商人特别优惠;法军撤出台湾澎湖。
通过该条约,法国基本拿到了战前向中国方面索取的权益,正式将大部分中南半岛纳入其殖民帝国体系。中国历史对此评价说:西方列强从此打开中国西南门户,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程度进一步深化。
时人曰:(中法战争)“法国不胜而胜,吾国不败而败”。
一、鸡肋之战
关于这场战争,首先指出,中法双方其实没有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越南虽然算东亚儒家文化圈的一员,北部还曾属于中国版图,但该地远离中原王朝核心区,不能有效辖制,最后还是听任其游离出汉家体系。历代王朝只是出于天下共主的虚荣,接纳他们作为藩属国。

中国藩属制度特别奇葩,除了一些礼仪任务,藩属国几乎不需要对宗主国尽任何义务。由于皇帝喜欢打肿脸充胖子,惯例是对进贡要加倍回赠,因此藩属国不仅没半点用,还构成极大经济负担。
当法国照会中国要求“保护”越南时,清政府虽然明确表示不予承认,却同意就此进行谈判。潜台词就是,越南给你没啥,但你就不能顾及一下我面子吗?
如果法国能像英国人那样立足经济利益,在外交上圆滑一些,其实完全没必要打这一仗。
二、洋人边将也是祸害
中法双方走到兵戎相见,很大程度上跟法国远东殖民当局的本位利益有关。
欧洲殖民者都是相当放飞自我的。这也好理解,殖民地跟本土大多远隔重洋,联系一次最快也要一个月以上,真要事事请示,那什么黄花菜都凉了!所以按照惯例本土都会授予殖民当局很大自主权,甚至包括一定程度的发动战争授权;而殖民当局也就习惯拿鸡毛当令箭自作主张了。

时至19世纪晚期,科技虽然有了大发展,但远程通讯问题尚未明显改善。当时最便捷的通讯工具是有线电报,但显然没有从法国本土直达远东的线路,最多也就中转拍发到埃及,然后还是要用低效的邮船送达。法国本土想对远东殖民当局发什么指令,没有一个月是不可能到位的——法国舰队7月中旬进入马尾,8月下旬才翻脸,就是在等指令。
仅从经济利益看,战前法国已经控制了大半个越南,物产丰富的成熟农业区已尽在掌握,北方多山地区其实相对低价值,不必急于攫取。至于说在广西方向打开中国西南门户,那是想多了,该地区地形崎岖不便深入,只有广州才是合适的桥头堡——后来法国抢占的租借地也是雷州半岛的“广州湾”(今湛江)。20世纪初法国主导修建了滇越窄轨铁路(昆明至越南海防),但长期货运量甚小,没能攫取可观利益。

真正通过控制中越边境口岸获益的是教会,主教神甫们进入中国传教方便了不少。
但是殖民当局要做业绩,不然猴年马月才能升官?所以他们忽悠了法国政府,软磨硬泡弄来了援军。
舰队一到就由不得本土了,远征军将领同样有建功立业需求,很容易和殖民当局形成同盟,扩大事态无可避免。于是开弓没有回头箭,无法实时掌握前方情况的法国政府,就这样被绑架着投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
三、李中堂的“怂”
站在清政府的立场,真心不想打这一仗。
当时已经不是1840年了,满清中枢不再那么昧于大势,对中法实力对比还是有所了解的。而长期负责“夷务”,很清楚自己“裱糊匠”本质的李鸿章更有清醒认识。

才初步迈入近代化的中国,显然不能与早已登堂入室的法国同日而语,双方资源投放能力有天壤之别。法国固然远隔重洋万里运兵劳师远征,清军要在中越边境部署重兵也不轻松。法国正规军组织程度,绝对甩绿营、团练乃至半新不旧的淮军八条街,真打起来几乎是碾压性优势。关键是就算走狗屎运打赢了又如何?没半毛钱收益,却要花费无算白花花的银子。
所以李鸿章根本不想打,一心避战,怂。但这不是他自己就能做主的,他需要说服上司同僚,在这之前他还得尽量拖着法国人。
李鸿章对形势判断没有问题,他毕竟是那个时代最有见识的中国人。他的弱点是怵洋人,总想打“痞子腔”蒙混过关,殊不知战争不是一方不想打就一定打不起来的。
四、“清流”们的“怼”
李中堂腰杆子软,满清政府一样不硬,在他们多次遭到洋人毒打后,更不敢“轻启边衅”。
但当时中国朝野对法国观感很差。主要是因为法国人讲究“价值观”,长期以天主教保护人自居,攫取殖民利益时总不忘加入传教条款。这恰恰是清政府最讨厌的,19世纪中晚期中国教案频发,多数原因是相互缺乏了解,但与天主教会过于强势的传教方式也是有很大关系。而法国人正是其中最跳的角色——天津教案时法国领事丰大业枪击通商大臣崇厚那个流氓样,绝对能让满清大员们记恨几十年。

所以李鸿章的说服工作很艰难,朝廷中以张之洞、张佩纶为代表的“清流”势力反对尤力。
现在有观点认为,清流们对国际形势毫无了解,纯粹出于党争排斥李鸿章的意见。
这种观点不是没有根据,但以偏概全。
二张一些判断确有拍脑袋之嫌——比如他们道听途说法国兵败割地赔款,便想当然以为法国必然内忧外患无力持久,殊不知普法战争已过十余年,法国早赔付完毕并还清相关贷款,重整旗鼓上路。他们又受左宗棠西征胜利鼓舞,盲目相信“一切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却没有看到左公如何战战兢兢步步为营,历尽千难万险才取得差强人意的结果。

但他们阵营中有曾纪泽,当时中国最好的外交官,没有之一。曾纪泽驻外多年,长期往来于英法,见识广博,有他把关不至于出现原则错误。当然,曾纪泽也可能把个人情绪带进了公事,当年他家老爷子曾文正公处理天津教案弄得几乎身败名裂郁郁而终。
其实“清流”的主张并不是一定要跟法国人干一场,而是不轻易退让。正所谓“能战方能和”,爱好和平要建立在备好棍子和工兵铲的基础上。不做准备一味怂,只能让敌人更骄横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
二张对全球形势认识不足,但他们也是在官场摸爬滚打几十年的老运动员,在把握人心上方面并不差——利益讹诈洋鬼子并不比中国人强。这在立意上就高于李鸿章。
五、两何无奈何,两张无主张
清流在现代为人诟病的主要原因是张佩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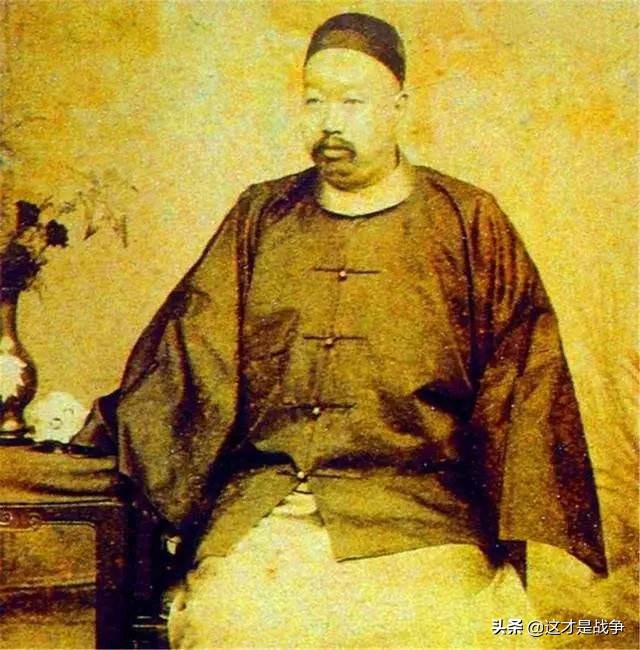
《清史稿》记:(光绪)十年,法人声内犯,佩纶谓越难未已,黑旗犹存,万无分兵东来理,请毋罢戍启戎心,上韪之。诏就李鸿章议,遂决战,令以三品卿衔会办福建海疆事。佩纶至船厂,环十一艘自卫,各管带白非计,斥之。法舰集,战书至,众闻警,谒佩纶亟请备,仍叱出。比见法舰升火,始大怖,遣学生魏瀚往乞缓,未至而炮声作,所部五营溃,其三营歼焉。佩纶遁鼓山麓,乡人拒之,曰:“我会办大臣也!”拒如初。翼日,逃至彭田乡,犹饰词入告。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张佩纶抵达福建后事是积极筹划抗战的。他曾主张用沉船阻塞闽江口,使法国舰队不得侵入,这本来纯属防务调整,但朝廷却认为有挑衅之嫌,明令禁止。结果法舰长驱直入,形成敌对舰队战前同泊一港的奇观。

即便如此张佩纶也保持着高度警惕,马江之战中福建水师诸船都曾启航开炮——船用蒸汽机需经数小时升火积蓄蒸汽才能带动螺旋桨,而炮弹火药作为管制物资也不可能随时置于炮位,可见一直处于枕戈待旦状态。海战失败完全是因为双方实力相差太远,法军又背信弃义发动突袭——法酋孤拔故意将最后通牒递交到福州船政大臣何如璋,而不是闽浙总督何璟或会办福建海疆事张佩纶,何如璋既非封疆大吏也没有朝廷授权当然无法回复,当然只能紧急联系上级,而孤拔不待收到回复即开始炮击。
所以张佩纶事前应对上并无不妥,事中不过是自我保护转移,并非逃避。以当时形势,哪怕是左公亲至,也很难做得更好。
战后张被革职流放,主要原因是政敌攻讦——“两何无奈何,两张无主张”(另一张为福建巡抚张兆栋)的“谣言”之精巧,绝非乡间绅民能作。
六、乘胜求和
后来李鸿章收留了前途尽毁的张佩纶,还将爱女许配其为续弦——他们的孙女就是大名鼎鼎的张爱玲。

有人据此以为,这是张向李认错,李宽宏大量予以包容。这完全是脑补加戏!李中堂爱才不假,张佩纶尽心辅弼也是实;但他从未否定自己,不过是他们翁婿搁置这段公案,不作结论。
从某种意义说,如果不是李鸿章避战思想干扰,朝廷能放手让张佩纶抢先阻断航道,福建水师也丢不了。
李鸿章“怂”论于战有害,但战后收尾却尽显裱糊匠本色。

一段时间来,国人对李鸿章“乘胜求和法人必不妄求”论调批评颇多。细掰起来,李鸿章做得并不太差。镇南关大捷固然难得,但却有侥幸因素,很大程度是老将冯子材凭个人能力击溃法军,不能说明清军战斗力占优。而且法国已大举增兵,实力已远远超过冯子材部,如果再战胜负犹未可知。此时福建水师全军覆灭,法军在台湾也占据绝对优势,实际上中国处于劣势。
不过有些人为了给李鸿章贴金,一味尬吹说:法国还想再战挣回面子,全靠中堂手腕圆滑,才挽回大局不致糜烂。这就过火了,李鸿章的长项在于大局底定后出面收场,他对世界局势的了解,加之善理繁剧的细致,让他能够找到一个相对有利的收官方式。但也仅限于此。
李鸿章虽然领兵征战多年,但一直没打过逆风仗,所以他缺少曾国藩左宗棠乃至曾国荃的韧性或者说狠劲,这也是北洋集团通病。别看现在有些文人把李鸿章、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等人死命吹捧,如果李鸿章等人真有经天纬地的大才,中国近代史会糜烂如此吗?
本文作者:鳄鱼不哭,“这才是战争”加盟作者 ,未经作者本人及“这才是战争”允许,任何媒体、自媒体不得转载,违者必追究法律责任,读者欢迎转发。
公众号作者简介:王正兴,原解放军某野战部队军官,曾在步兵分队、司令部、后勤部等单位任职,致力于战史学和战术学研究,对军队战术及非战争行动有个人独到的理解。其著作《这才是战争》于2014年5月、6月,凤凰卫视“开卷八分钟”栏目分两期推荐。他的公众号名亦为“这才是战争”,欢迎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