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山西高平县孝义村出了桩轰动一时的怪案,小小的孝义村因而名闻遐迩了。
这孝义村在黄土高原上也算一个大村子了。一条大街,两侧都是砖瓦房舍。村中临街有座大庄园,气象自与別人不同。庄院主人姓祁,名叫祁轼,三十九岁,是个秀才。他弟弟祁辐喜爱武功,骑马射箭,样样在行,中了个武秀才。叔父祁桂元,用银子捐了个监生。他家在县里知名乡绅中,排不上名次,但在孝义村里倒是首富了。他家田产多,习文的习文,练武的练武,田地只好雇人耕种。家里请了扛长活的、赶车的、做饭的,农忙季节,每天还要请短工八九个。
这年的闰四月十九日,村边柳丝重绿,白杨耸翠,地里庄稼已有半尺高,一片绿汪汪的。早饭后,长工祁大孩与短工吳起凤向院里的西南角走去,那里是厕所,他们要起粪上肥,那粪坑很大、很深,口小肚大,象个大斗,坑是砖块砌的,年深月久,粪水的腐蚀加上掏粪时的磕碰,坑壁上的砖已参差不齐、坑底有一尺多深的粪水。
吳起凤与大孩边抽烟边到粪坑,拾头看见祁轼在台阶上闲望,说:“瞅,东家在监视我们哩。”他赶快从嘴里拔出烟袋,由于心理紧张,一个没拿稳,烟袋扑哧一声掉到粪坑里了。若是平常烟袋,也就罢了,这杆烟袋的嘴儿是绿玉石的,穷人家有此一物,便是镇家之宝了。打从吳起凤的爷爷的爷爷开始,便代代相传,一直传到吳起凤的手上,吳起风往粪坑里一瞧,恰好有一抹阳光照在坑里,照见烟袋落在浮着的干粪上。那玉嘴儿还闪着绿光哩。他实在舍不得,连忙出来,到牛房里去取梯子。大孩也跟在后边跑。
台阶上闲望的祁轼,看见吳起凤扛梯子,觉得奇怪,问道:“你不是掏粪吗?取梯子作甚?”
吳起凤笑笑,说:“掏雀儿。”
祁轼搖搖头;“尽干作孽的事儿。”
“不是掏雀。”大孩见祁轼信以为真,连忙说:“他的烟袋掉到粪坑里了。”
吳起凤将梯子从坑边伸下去,斜斜搭在坑沿,攀梯子下到坑里。大孩同他开玩笑,说:“吳大叔,这烟抽起来更有味儿了。”吳起凤既沒答话,也沒上来,大孩趴到坑沿一瞧,只见吴起凤在粪坑挣扎,他大吃一惊,高声喊到:“吴大叔出事了,快救人啦。”他喊着,

沿梯子而下,刚下得几级,头一晕,也掉在坑里了。短工赵玉英听见厕所里有人喊救人,连忙跑进去。看见吳起风、祁大孩都躺在坑底,连声呼救,同时也顺梯子往下爬,刚下两级,突然头晕、恶心、要吐,他害怕了,赶紧爬了上来。孝义村的保正祁兹成打门口路过,听到呼救声,连忙跑进,看见坑里倒了两个人,他冲祁轼、赵玉英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见死不救,光喊顶啥用。”他一边埋怨,一边脱掉布衫,登梯下去。临近粪水,他一手攀梯,伸出一手去拉祁大孩,刚拽住他的衣,正想攀梯而上,突然,他身子一晃,也栽进去了。祁轼、杨玉英不知粪坑里是什么怪物,吓得朝外退去。他们喊救的声音,凄厉而又嘶哑,短工冯奎、厨工李成本、祁成的妻子丁氏都闻声赶来了。一会儿,厕所里外都是人,哭的、喊的,乱成一片。有的说坑里藏了怪物,有的说是粪毒伤人,七嘴八舌,议论纷纷。
“柏树枝能除秽气。”
“拆掉坑梁,开大口子。”
“找绳子,拴了人下去捞。一有危险,赶快拽”。
柏枝向坑里投了一捆又一捆,坑梁拆除了,坑口扒大了。乱了一阵,冯奎将绳子一头拴佳自己的腰,一头让李成本等人拽住,他沿梯而下,祁茲成靠梯子近些,他先把兹成捞上来,众人接住,抬到庭院里。随后又捞出祁大孩和吳起凤、三人躺在庭院里,已是气绝身亡。
祁茲成的妻子丁氏看见丈夫死了、吳起凤的妻子看见丈大死了,祁大孩的父亲祁彦和看见儿子死了,个个嚎啕大哭,顿足捶胸,围观的乡邻睹此惨状,也鼻子发酸,抽抽搭搭。
祁轼看看三具尸体,他搓着手,直转圈,“人命关天,这怎好?这怎好?”
一会,乡约祁恺,地保祁景也赶到现场,他俩一面人保护现场,一面派人去高平县衙禀报。一直闹腾到夜里,人们才陆续散去。
第二天,高平县知县就要进村验尸。乡约地保祁恺,祁景一大早就奔孝义村安排迎候。他俩路过一处乡村旅店。店主王进贤看见乡约、地保路过,老远就招呼道:“祁乡约,祁地保,你俩起这么早,是去迎候县令吗?进来喝杯酒吧,天还早,褚县令还来不了,进店坐坐吧。”两人相跟着进了店。
这店主王进贤是个极和气的人,他认为和气生财,那笑象是长在脸上的,你打他三个耳瓜,那笑容也减少不了半分。乡村小店是那时的清息集散中心,孝义村粪坑里一时死了三个人,又是一条大新闻,王进贤便自然知道了。他那小店的成本还是借祁轼的,因此,他特別关心祁轼家的事情。祁家倒霉了,旅店也得关门。乡约、地保进店后,他笑迷迷地迎进去,拣张洁净桌子给二人座下,又给二人端酒端菜,他笑着说:“有人说,吳起凤三人是祁轼害死的,这不是冤枉人么?祁轼害他们干甚呢?图他们的钱?他们是苦哈哈。图他的萋子漂亮?大孩沒成亲,祁兹成的老婆,吳起凤的婆娘都又老又丑,谁去图她们?你们两位关照关照祁秀才吧。那人对扛活的虽抠一点,但人却是好人。”
“晓得晓得。”祁恺说:“王店主,你同祁秀才不错,我们同他也不错呀。”
祁景说:“王店主真精。你是怕秀才遭冤么?是怕旅店开不成哩。”
“嘿嘿,嘿嘿”王进贤笑了一会,说:“你说的也有理儿。”他受了抢白,半点也不生气。
祁恺、祁景是等县里仵作宋正祥的。眼看日头老高了,宋正祥还沒来,祁恺说:“这时还不来,是不是他沒走这条道?”祁景也拿不准,说:“不如我们且到孝义村去,反正他要到哪儿的。”
“也好。”祁恺站起来,说:“王店主,你替我们留点神,宋正祥一来,请你告诉他,我们先去孝义村了。”
“好好。”王店主连声答应,一直把乡约地保选出店外,他刚刚接待了两个客人,却见一个三十刚出头的青年走进店来。他正是宋正祥,高平县的仵作,专管验尸的人。王进贤又笑着迎上去,说:“宋仵作,快请坐。”
“祁恺、祁景呢?”
“先走了。刚去不久,他们说在孝义村等你。”王进贤说着,又给宋正祥端酒端菜,缠着硬要他喝一杯。宋正祥无奈,说:“今日验尸,含糊不得,酒,免了吧。”
“谁不知你海量,喝一杯有啥呢。”
宋正祥被缠不过,端起杯子。
“嘿嘿。”王进贤未说先笑,“你到孝义村验尸,不要刁蹬了那秀才,胡乱要东西。我送你三百文脚钱,你回来就给。”
这时,只见大路的远处一行人飞也似的朝这边过来。宋正祥说:“啊,褚大人到了。”可不是,高平县令褚天纬乘坐小轿,家人孟福扶着轿扛,前有执事,后有书办、小卒、衙役一大帮,已快到面前了。宋正祥一推酒杯,赶紧站在路边迎候,当轿子到面前,宋正祥上前行礼说:“禀大人,仵作宋正祥问安。”褚天纬的轿也沒停,孟福朝后一甩头,示意让他跟了走。
知县老爷到孝义村验尸,惊动了全村百姓,他们几乎倾“村”而出,看看县令大老爷是什么模样,祁轼连忙接待。褚天纬落轿后,在书办、仵作、护卫、衙役簇拥下,在堂屋里临时设置的公案后坐定,他先叫祁轼,让他汇报了吳起凤等死的经过,然后,又叫仵作宋正祥,让他仔细看验,立等回报。
这时,吳起凤、祁大孩、祁兹成的尸体放在庭院的老槐树下,尽是粪污,宋正祥让人提水冲洗干净。死者肚腹俱胀,指甲里有黑泥,牙根呈青黑色。他点点头,已断定是中毒而亡。吴起凤等中毒后,失去自制力,憋闷难忍,极力想爬上来,双手乱抓,指甲里便留下黑泥。昏迷中,大量粪水灌进嘴里,肚腹就肿胀起来。他再细验,见祁茲成的脑后有块磕伤,眼胞上有红印,肩胛上也像有磕伤的痕迹。他忽然想到王进贤的嘱托,加上尸体上的粪便虽已冲洗,但是仍然臭味难闻。既然结论已有,死因已查明了,何必再验个没完呢?三人是毒死的,同祁秀才确无关系呀!他走到堂屋前,说:“回禀老爷,小的验完了。
“怎的?”
宋正祥把验出的情况禀报一逼,说:“小的察验确实,三人都是中粪毒死的。请老爷的示下。”
“填验尸单”。
吴起风等是中毒而亡,祁轼长长地出了口气,祁辐以手加额,不由自主地说:“谢天谢地。”他们的叔父祁桂元年纪大,听到仵作的结论,全身立到松驰,浑身发软,似乎站立不住,连忙扶住墙壁。尸亲祁丁氏、祁彦和、吳祁氏哭的哭,掉泪的掉泪。褚天纬安慰道:“你们失去亲人,这是人生的不幸,我也替你们难过,但人死不能复生,死的死去了,活的还得活著,你们不要过分悲痛。损害健康,因为这对死者无益,只能让他们在九泉下也不心安。”他看见祁丁氏、吳祁氏衣衫褴楼,面色发黄,知道他们生活贫困,日子艰难,不觉皱皱眉,回头对祁轼说:“你在村中也算首富了,为富不仁是要不得的。你并不是那种为富不仁的人,我只是说为富不仁,有违圣道。吳起凤三人,是给你家干活,在你家粪坑里中毒死的。尤其是保正祁茲成,是替你家救人死的,对你家更是有恩。他们三家都极贫寒,你就破费点,替买三口棺木,三疋缠尸布,把三个埋葬了,这也是功德无量的事情。我这么定了,你们同意不同意呢?”
“悉听大人吩咐。”祁轼一口答应了。
祁桂元赶忙表态:“大人断得极是。”
三家尸亲见县令如此处置,连忙跪下叩头:“谢老爷恩典”。
太阳西沉,繁星滿天,直到掌灯时刻,褚天纬才处理完验尸事务,坐轿回县衙。孝义村里,祁轼忙了一个通宵,他连夜派人找来三口板材,三疋布,同尸亲一起,七手八脚将三人入殓完毕。个个累得臭死,嘴里还不停地感念褚县令。

褚县令却独自在县衙犯嘀咕了。他回到县衙,吩咐书办缮写上报详文,自己回到后堂休息,等详文拟完后,再行审阅。他这个人是多疑多反复的,他边喝茶边回忆白天的事情,眉头慢慢皱起来了:“粪毒是有的,它能伤人,怎会一下子夺去三条人命呢?这里面有沒有别的文章?”这个疑字一上来,他就坐立不安了,他是正派的书呆子,一心想做个廉明的好官,甚至在他接见乡绅等人的大厅里,挂出一副对联:送钱送物,是君害我。收金收银,乃我毒民。他上任以来,官清如水,廉字倒做到了。只这“明”字,差得太远,他一辈子钻在书堆里,沒有接触过实际,办事尽凭想当然,结果事与愿违,捅出不少漏子。现在,他疑心白天的处理是有问题的,不信粪毒能一下子毒死三人,于是就查《洗冤录》,左翻右翻,沒有查到粪毒毒死人的先例。他的疑心又增加一分:“《洗冤录》列举种种冤情,怎么就缺粪毒一条呢?莫不是粪毒不能毒死人,故书上未载吧!毒虽有毒,人在毒粪里滚儿滚,也许使人皮肉溃烂而死,那也不是一会儿的事情呀!啊,对了,白天验尸时,保正祁茲成的兄弟祁茲顺强调死者身上有伤,当时宋正祥说是跌下时磕的。自己便轻轻地放过去了。当时沒详加追问,实在马虎了。如伤是致命伤,那么,人就可能是被打死后扔入粪坑的,恶奴常常蒙蔽有司,宋正祥是不是在蒙蔽我呢?他对宋正祥的验尸结果也疑上了。那么,为什么要打死他们呢?祁轼是大戶,会不会买通仵作,匿伤不报呢?原通知宋正祥到县衙集合再去,他今天偏在一家旅店门口等待,未去县衙,是不是祁轼在验尸前赂嘱仵作呢?而且,他轿子从小店门口路过时,他曾分明看见店主同宋正祥打手势,并说什么“仵作,拜托了”,而宋正祥还回了一句“请放心吧。”“拜托”什么?“放心”什么?恐怕与验尸有关。宋正祥受了赂嘱,于是匿伤不报!他越想越觉得有理,一拍桌子,说:“对了,吳起凤既是捞烟袋下坑死的,那烟袋呢?怎么沒捞出来?烟袋价值几何,掉到坑里还去捞?捞起来已被粪污,还能用吗?”他按他的逻辑推理,最后作出决断:“今天要去捞烟袋,如果坑里沒烟袋,那么,骗局便都揭开了。”
第二天是四月二十五日,天沒大亮,褚天纬便爬起床,吩咐差人速传刑书陈相卿,招房张耀候,仵作宋正祥,牛增等人到衙门议事。这些人被人从梦中惊醒,闹不清发生了什么事,只好迷迷糊糊地赶来县衙,宋正祥问褚天纬的家人孟福:“大老爷这么早叫我们来是为了什么事呢?”
孟福摇摇头。
“老孟,你别不够意思了,”宋正祥说:“你是老爷的贴心家人,能不知道?”
“真的,老爷办事,谁也不信,能告诉我?”
“嘿嘿,你别嘴紧了。”宋正祥说:“你先透透,让我们有个准备,老爷问起来,也不致于慌乱,这是积德的事情。你先透透风吧,呆会儿我请你吃羊肉泡馍。”
“真不知道。”孟福说:“我想吃你的羊肉泡馍,可惜吃不上。”
他们的对话,恰好被褚天纬听见了,他想:“我就谨防属下愚弄本官,一直小心注意。现在果然应了。宋正祥就向孟福摸我的底了,好在我事先沒讲召他们来的原因,否则,宋正祥摸了底,早就想好对付我的办法了。”他冷冷一笑,装出大声咳嗽,慢慢踱出后堂。
听见褚天纬咳嗽,孟福、宋正祥连忙住嘴,垂手侍立。褚天纬斜了他们一眼,说:“备轿。”
他坐上轿子,孟福问:“老爷,去哪里?”
“让他们跟着”。褚天纬吩咐一句,“去孝义村。”
“去孝义村?”大家都莫名其妙。大老爷既然说了,谁还敢问去干什么,只好跟轿而行。
褚天纬到孝义村,预先沒打招呼,村里人不知道,祁轼也不知道,他昨夜忙了一个通宵,正睡着沒起呢!听说县令到了,赶紧披衣起床迎接。褚天纬一下轿,看见三口棺木已经封了盖,马上又起疑了:“昨天我离开时,已是掌灯时分,今早到村,棺木已买了,死者已装殓了,为什么这么快?夜里从何处弄来棺材?看样子,他们是急于把死者埋葬了事,以掩饰谋杀的罪行吧!”他面孔沉下来,在堂里那临时公案后坐下,叫道:“牛增。”
“小的在。”
“你把棺木打开,重新验看。”他朝宋正祥,说:“你不要去啦。”
宋正祥一见这架势,知道县令不信任自己,怀疑自己昨天的验看了。心里直打鼓。脸色也变了。
众人不知为什么,看见褚天纬板着面孔,谁也不敢询问。
牛增招呼祁轼家的一帮长工、短工,撬开棺木上的大釘,揭开盖,剝去裹尸布,把三具尸体重又细细察验一番。牛增是机灵人,预感这重验有名堂。昨天他沒到场,不知宋正祥验的具体情况,如果验得与宋正祥的不准,势必要受责罚。因此,他认为只有验得过细,才能与宋正祥的验看结果一致,否则就会遭殃。这样想了后,他倒员的过细起来,连尸体上任何伤痕都不放过。
褚天纬自己呢?他走下公案,朝随从一招手,直奔厕所。他不怕臭,站在那里,对祁轼说:“你们不是说吳起凤是捞烟袋下的坑吗?派人去把烟袋捞起来。”他双眼紧紧盯着粪坑,看人下去捞烟袋,一个长工爬进去,费了不少劲,终于把烟袋捞起来了,用水冲洗后,捧到褚天纬面前,褚天纬一看,只是个六七寸长的小烟锅儿。心想:“这么点东西,掉就掉了,还值得为他送命!”
他同大家一起回到堂屋。一会,牛增前来禀报:“验看完毕。”牛增除了说死者肚腹肿胀,指甲里有黑泥,牙根青黑外,还汇报说,死者身上有伤痕。褚天纬细细地听,还拿宋正祥昨天填的验尸单对照,嘿,他发现问題了,牛增看验出的伤痕,竟比宋正祥多了四处,少了一处。宋正祥昨天说祁茲成眼泡上有擦伤,牛增说沒有。这是少处,多的四处是:祁兹成脊背上有擦伤,脑后有一伤;吳起凤后脑有一伤,祁大孩头顶有一伤……为什么伤在头顶要害部门?为什么三个人的伤处都一致:褚天纬更起疑心。牛增验看后,他又亲自再去察验一逼,证实牛增验的对,宋正祥是漏验了。这时,他脸孔一变,滿面怒色,对宋正祥道:“你怎么验的?”
“小的该死。”宋正祥吓得双膝跪下。
“为什么漏验啦?”
“小的初学仵作,沒看仔细。”
“胡说,拉下去,打五十板子。”
他冷冷一笑,众人更不敢言动了。偌大庭院,格外安静,只那衙役挥动竹杖的鸣鸣声,宋正祥那喊痛的声音,比平时更叫人心胆俱寒。
一会,宋正祥挨完板子,一瘸一拐地上来谢罪。
褚天纬亲自看验时,发现祁茲成脑后那伤不小,问道:“牛增,既是毒死的,为什么又带伤呢?祁茲成那脑后的伤不小呢,到底是什么伤呢?”
“招伤”。
“什么伤?”褚天纬沒听懂,又问了一句。
“那伤皮肉外卷,可能是梯子磕的。”
“好像是铁器打伤的。”褚天纬这么想,他吩咐刑事陈相卿,“你重新填个尸单”。
众人早上来时,不知县老爷是要重新验察尸身,所以沒带验尸单。刑书陈相卿只好临时找张纸,记录了重新看验的情况,并画了一张尸图,标明尸身伤痕所在,尤其在祁茲成尸图上,注明脑后有致命伤一处。

祁轼、祁辐、那祁桂元叔侄三人,一见褚天纬大早赶来开棺重新验尸,就感到情况不妙。这时见陈相卿标明祁茲成脑后有致命伤,便更紧张:脑后有致命伤,说明是打伤的呀。这便是杀人罪了。祁轼、祁辐年纪都轻,一个文人,一个武人,吓得都不敢言声了。祁桂元年纪大,见的世面也多些,他不服气,却不敢直接同褚天纬顶,便冲陈相卿说:“你不能那么填报。”
“为甚?”
“这么填报,岂不是坐实祁茲成是被打致死的吗?”祁桂元脖子都粗了。
“祁茲成脑后有无伤?”陈相卿质问祁桂元。
“有。”
“那伤在脑后,脑后是不是致命处?”
陈相卿这么一反问,一时弄得祁桂元张口结舌。
“争什么?”褚天纬脸露不悦之色:“你沒打人,怕什么?现在沒人说你是打伤人命嘛。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啊!”说完,他站起来,说,“回衙。”他没同祁桂元等人打招,走出堂屋,在庭院里上了轿,在衙役前呼后拥下,一直朝县城而去。
祁桂元叔侄愣怔怔的站在堂屋里,预感到灾祸即将来临了。他们认为这是褚天纬要敲錢财,不知该怎么办好。
其实,褚天纬根本就沒有想敲诈的意思,他只是怀疑而已。他因怀疑搞了个突然袭击的重新验尸,重新验尸后,伤痕多了四处,反而把怀疑加深了。他在县衙踱步,想:“问題沒搞清楚,就这么填写报府详文,如果追问起来,怎么对付?更重要的是县令为民父母官,案情不清楚,冤屈了死者,死者在九泉下也不安稳呀,为民父母的不为百姓作主,还算什么父母官呢?”他转而又想;“如果是毒死的,弄成打死人命,又会伤害无辜,冤枉了好人,这就更不好了。”他思前想后,不免有些急躁。他认为一切问题的根本是查明死因,弄清事情的真相。怎么弄清真相呢?应该实地查访?派谁去察访呢?孟福,不行,他总是个家人、奴仆不应该干政。刑书陈相卿?太年轻。帮办张耀侯?不合适,听说他同四乡首富关系密切,祁轼是个大戶,他们会沒有关系?他想了一串的人,这个不合适,那个不妥当。最后他想起一个最相信的人,那人就是他自己。一县之长,人人注目,谁不认识呢?他最后决定,谁也不告诉,来个微服私访!
第二天,他没同任何人打招呼,青衣小帽,装成个老百姓模样,早早离开县衙,悄悄走向孝义村的大路。临近晌午,肚子饿了,也沒打听出什么消息。看见前边一店,便踱了进去。正巧是王进贤的小店。客人上门,店主王进贤不在,一个小伙计上前招呼:“客官,往里请。”
褚天纬也不出声,走到一张空桌子边坐下来。他买了两碟菜,一碗饭,愁眉不展地吃起来。旁边桌上有一伙客人在喝酒,谈些生意上的事情,他也无心去听。饭快吃完了,起身正要走。忽见两个客人边争边说的进店,只听一个说:“三个人都中粪毒,沒听说过。”
“昨不能?粪就有毒嘛。”
“粪是有毒!但能一会儿把三个都毒死?谁家沒粪,那还不家家都沒有人啦。”
反诘有力,对方一时语塞。褚天纬一听,他重又坐下,想听听这场争论的结果。这时,那反诘者嘻嘻一笑,说:“告诉你吧,那三人都不是毒死的,全是打死的。”
褚天纬一惊,赶忙竖起了耳朵。
那两个客人沒要菜要饭,只要了茶喝。一个客人问道:“那秀才无缘无故干吗要打死人?”
“怎会沒原故?”另一客人说:“那秀才的女人上厕所,吳起风看见秀才娘子挺水灵的,就撞进去了。那秀才小时得病,药不对症,把那玩意儿变得象小虫子。秀才娘子嫁一个阉人,就沒偿过味儿,吳起凤一上手,她先还掙扎,但一接触,她倒主动起来,两人在厕所草堆里正瞎闹腾,祁大孩去起粪,撞见了,那小鬼转身就走,告诉了祁轼,祁轼操了把铁锹冲进去,砸中了吳起凤的后脑勺。”
“我不信。”另一客人反问道:“吳起凤做那事,秀才打死他,这可理解。祁大孩送信,干吗也打死呢?”“你这又不懂了,”前边那个客人说:“祁家是啥人家?大戶,一个秀才、一个武生、一个监生。能象一般百姓不讲脸面吗?这种事张扬出去,还受得了?他们怕祁大孩漏嘴,索性也把他打死扔进粪坑。”
“啊!果有冤屈。”褚天纬暗暗心惊。
“那保正呢?”
“祁轼连伤两条人命,恰好被祁茲成路过撞见了。逼勒祁家银子。祁家的银子是好要的。祁保正说不如数付给,就要报官。争执不下,祁家人打红了眼,两条人命是死罪,多条也是死罪,因此又把祁兹成打死了。”
“那三家的亲属能干?”
“自然不干。”客人说:祁家咬定是粪毒死的,他们打时,只一过路老太太看见,当时吓晕了,倒在厕所的破墙外面。祁家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哩。死者家属自然怀疑,祁家拿出四十两银子,十五匹布,让三家分了。三家见祁家有钱有势,告官也沒用,只好算了。”
褚天纬还想听下去,他想:“当他们说得差不多了,自己过去,再加询问,然后把他们带回县衙门,细细盘查。”所以,他坐着不动窝儿。
“我还不信。”另一客人说:“县里褚大老爷不是验过尸么?验的结论是粪毒死的呀。是打死的,仵作还验不出来?”
“对,算问得有理。我呆会讲。”那客人从怀里摸出一个大钱,往桌上一扔,说:“茶钱,不用找了。”回身一拍同伴的眉头,说:“好戏还在后头呢。够你听的。走,路上说。”两人站起来就出了店。
“喂,”褚天纬站起来去追客人。他心里着急,沒想到撞在邻桌的一个酒客身上,直撞的那客人的酒杯掉到菜碗边上,碗碎了,汤流一桌。酒客一把抓住褚天纬,喝道:“你怎么了?想捣乱吗?”褚天纬连忙道说:“对不起,请见谅。”他是江南人,一口江南口音,山西人听不懂,那人更生气了:“不是你,睁眼看?”那是个鲁莽汉子,举拳要打,但被别的酒客拉住了。正在纠缠不清的时候,王进贤踏进店来。他与祁轼关系密切,所以褚天纬连续两天去孝义村,他都赶去了。因此认得褚天纬,他看见酒客打架,连忙上前劝解。一眼就认出了褚天纬,连忙叫道:“不得动手,这是咱县的褚大老爷。”鲁莽汉子和酒客一听撞跌酒杯的人是县令,吓得一个个都软了。当王进贤扶住褚天纬坐下,替他整理衣服时,他们便一下溜掉了。褚天纬顾不得整理被揪坏的衣服,赶紧出店找那两个谈论孝义村命案是谋杀的人,那还有那两人的影子呢?连刚才同他吵闹的酒客,也都躲起来了。“嗨,嗨。”褚天纬见那知情酒客走了,急得直跺脚。

他无可奈何地回到县衙。立即传令让差役传祁桂元,祁轼、祁辐及祁家长工短工、左邻右舍到庭,准备第二天审理。他跑了一天,两腿酸胀,坐在椅子上,轻轻揉着、揉着………
第二天,即四月二十三日,褚天纬升堂,先审祁家的帮工李成本、赵玉英、张二、祁祝及左邻右舍祁绪、祁海,从早到晚,问得喉干舌燥,坐得屁股生痛,果得精疲力竭,但那些人一致咬定吳起风等三人是中粪毒死的。他火了,想到旅店內那位客人说的是多么确实啊,既合逻辑,也有细节,为什么就审不出来呢?褚天纬心急气燥,在审祁轼的邻居祁绪时,他想到用刑。一拍案子,说:“不用刑,你是不肯吐实话吗?来人,夹棍伺候。”
衙役将夹棍往祁绪面前一扔,祁绪浑身一颤,说:“老爷,我说实话。吳起凤等人是被打死的。”
“怎么打死的?”
“我说不清楚。”
他不想是自己主观臆断,却认为是祁轼先行用财物贿赂了。他叹息道:“钱能通神啊!”
四月二十四日再升堂时,褚天纬便用严刑了。众人熬刑不过,便胡乱招认起来。他先提祁祝,问道:“你叫什么?”
“祁祝。”
“你与祁轼是什么关系?”
“我是他家帮工。”
“吳起凤怎么死的?”
“中毒死的。”
“你肯定?”
“肯定”。
“你是不见刑不吐实话!”褚天纬大声喊道:“重刑伺候。”
先打了一顿板子,祁祝嗷嗷乱叫,撕心裂胆。褚天纬放了他,问道:“怎么死的?”
“中粪毒死的。”
“你还不说实话”。褚天纬满脸怒色:“夹手指。”
夹手指是把细圆木棍夹在犯人的指缝里,衙役再用劲捏手。这一捏痛彻心脾。祁祝已杀猪般的叫了。褚天纬松了刑,问:“祁祝,你说不说实话?”
“我说实话。”邢祝想若说是中粪毒,又得夹手指,他实在害怕,说:“是打死的。”
“这差不多。”褚天纬又问:“为什么打死?”
“因为争车道。”
“你又不肯说实话了?”褚天纬说:“本县已私访查得实情了。”说着,他拿出一张纸条念道:“因祁轼老婆与吳起凤有奸情……”他把小店里听到的传言一口复逃出来。无奈他的南方口音,山西农民听不懂。褚天纬让帮办张耀侯复逃一逼,褚天纬叉问:“祁祝,你听清沒有?”
祁祝点点头。
褚天纬脸色平和,说:“你讲实话,我赏你银子,不说,再上夹棍。”
祁祝的双脚已被打得红肿起来,火烧火燎的,痛得钻心。他自忖道:“再上夹棍,我的两腿就残了,谁养活我呀。既然老爷访闻清楚了,我就照他的话说吧。县令大老爷肯定沒错的,否则,怎么能当县令呢?再说,祁轼家既然有这事,我虽沒看见,别人看见也是一样呀!这不算冤枉人。”他拿定主意后,便照张耀候传的话复述了一遍。褚天纬笑了,说:“你早如此,皮肉会吃苦么?”他随后又问:“三家尸亲为什么不告状?是不是得了银子?”
“是。”
“多少?”
“十两。”
“不对吧。”褚天纬说:“我老爷也访闻清楚了,祁家给了三家共四十两,十五匹布。”
“对,对。”祁祝顺竿爬,“我记错了,是老爷访闻的这个数。”
“每家多少?”
祁祝是农民,简单的帐还会算的,说:“每家十三两三錢多,五匹布。
褚天纬松了口气,可算审出来了。但又想,不对呀,每次都是我先说,祁祝才说的呀?这是套供,怎么能算呢?不行,祁祝的话不能全信,诱供是会误事的。他让衙役把祁祝带下去,关进马房。他实在累了,说:“我到后堂歇歇,你们也休息一下,等下再审其它人。”褚天纬的嗓子发干,到后堂端起茶壶,连杯子也不用,嘴对嘴儿的嘟嘟几大口,说:“真甜,饥好吃,渴好饮,真不错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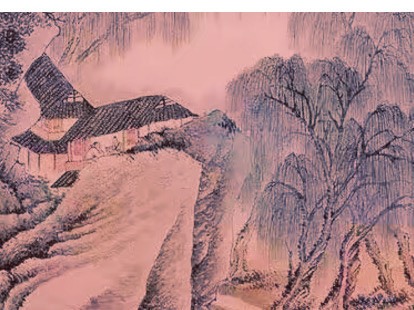
祁祝被衙役夹着扔进马房的草堆里,別人围过来,见他浑身伤痕,滿脸血污,个个心胆俱寒,不凉而抖。祁祝喘着气,说:“唉,吳起凤他们不是粪毒死的,是被打死的。褚大老爷都访闻清楚了。”
“是么?”众人吃了一惊。
“可不是。”祁祝说:祁轼秀才这个沒卵子的家伙,平日对咱们帮工真剋…唉哟,痛死我了。”
“怎么打死的?”众人齐声询问。
“秀才娘子上厕所,吳起凤乘机把她按在草堆里,…祁祝便把褚天纬的话复述给大家听,末了,还说:“既然这样,我们就这么供吧,免得吃夹棍,那味儿不好受。”
一会,差人来带赵玉英,褚天纬刚要上夹棍,他连说:“我说,我说…”赵玉英便把祁祝刚才说的内容说出来。
褚天纬高兴了:“嘿,这个帮工沒上刑,就说了,可信,可信。”
随后提李成本,这李成本是胆小的。一到大堂,连忙朝下一跪,说:“我说实话。”接着又把祁祝的说法重复一番。再提审其它人,人人都象背书似的背下来。褚天纬轻松了,自言自语:“古人提微服私访,果能获真情,我若不是这样做,这次让恶人跑了,好人冤枉了。”忽然,他想到宋正祥,不禁怒从心上起,咬牙道:“可恶,妄验误报,差点让我办错了案。”他便大声传呼:“叫宋正群。”
仵作宋正祥早已魂飞魄散。他从同事们嘴里知道吳起凤三人是被打死的消息,一直忐忑不安。他本是新手,经验不足,自信心不强。听了大老爷的访闻结果,害怕受到责罚,整天心绪不宁。听到褚天纬传呼,两腿软得像带子,他挪到大堂上,连忙双膝跪倒,直掉眼泪。
“你知罪么?”
“知罪、知罪。我误验了。”宋正祥连连磕头。
“误验?”褚天纬一瞪眼,“你是故意的。受多少贿,从实招来。”
“受贿?”宋正祥一愣,他想起二十日早上,王进贤拉他进店说的话,许的钱,他似乎恍然大悟,这不是祁轼派王进贤行贿么?他磕头如捣蒜:“小的该死,小的该死,我全招,我全招。”他于是把到孝义村验尸时,在王进贤小店歇脚,王进贤说的话,许的钱,都供出来。褚天纬这次沒打他,说:“看你坦白得好,这次不打你,你下去吧。”
他差人去捉王进贤,王进贤也说吳起凤三人是打死的,正后悔不该怕祁轼收回成本而主动去向仵作求情,他一上大堂,就招供了:“小的千错万错,不该请宋仵作验看时马虎些,还答应送他钱。”
“多少?”
“三百文。”
“哼,好大的胆子。”褚天纬冷笑道:“吳起风三条人命只值三百文?”
褚天纬这本是一句驳斥,谁知王进贤晕了头,沒听懂语气,连忙又说:“事成后给二两。”
“谁让你这么做的?”
“祁…祁秀才…他……”王进贤已晕过去了。
接着他开始审主犯祁轼、祁辐,他们初不承认,弄得刑伤滿身。祁桂元看见侄儿如此,不觉心酸,他说:“熬刑不过,先招了吧,我再想法解救。”两人只得屈招。依据条例,杀人偿命,祁轼为首犯,判为斩刑,下到死囚牢房。祁辐“助恶”,充军边塞。褚天纬一面呈文学政,虢夺祁轼功名,一面缮写详文,申报到泽州府。
一桩冤案这么造成了。
祁桂元看见侄儿判了死刑,哪敢怠慢,连夜写了状词,赶往泽州府喊冤。他到泽州城时,褚天纬的详文也到了。泽州府知府李樟审阅高平县的详文,看到连伤三命,大吃一惊。细阅一遍,又生疑惑:吳起凤在厕所奸祁秀才之妻,祁秀才怒杀吳起凤,因怕丑声传扬,又杀报信人祁大孩。保正祁茲成碰见要挟索贿,祁轼又再杀保正……朱樟自言自语“蹊跷,蹊跷,真拿人命当草了。”再看验尸单子,发现详文与单子有出入。详文写明是擦磕招伤,验尸单子却注打伤,两者互相矛盾。他说:“这对不上呀?怎么回事呢?”
“咚咚咚”,堂上鼓声大作。并传来喊冤的声音。他问家人何事,这时,衙役上来禀报,有人击鼓喊冤。
“谁?”
“高平县监生祁桂元。”
“升堂!”
朱樟从后堂出来,大堂上两班衙役已经站好。朱樟问道:“你有何冤枉?”
祁桂元便将吳起凤三人中粪毒而死,知县褚天纬头天察验,仵作报中毒死亡。第二天,知县如何再验,如何拘禁众人,严刑逼供,非要断为因奸杀人,将侄儿祁轼断斩。他接着说:“大人,祁兹成脑后伤痕是他小时生疮留下的,这次擦破了,并非打的。这次褚县令误断,全是刑书陈相卿搞的鬼。那陈相啣會经向我侄儿敲诈,我侄儿送他八两,还许他十两,这事有小店主王进贤为证。他嫌少,拿了银还害人性命。”这后面几句,倒使朱樟震动了。他挥手让祁桂元下去,自己回到后堂筹思:案情重大,处理不慎,将影响前程。自己先不出面,另要他人出审,摸清情况,自己再出马吧。这样能左右逢源,谁去审呢?他想到凤台县知县罗著藻,这罗著藻是泽州府下第一能员。办事干练。

罗著藻到泽州后,很痛快地接受了任务,他说:“我求大爷借几个得力仵作。”
“邻县武威文,阳城县张德,赵应魁。”
“可以。”朱樟一口答应,拱拱手说:“人命关天,拜托拜托。”
罗著藻等三个仵作一到,便动身到了高平县孝义村。褚天纬接到泽州府的通知,同时到达村里,他拱拱手,说:“有劳罗县令。”
“上峰差遣,不敢辞劳。”罗著藻还了一礼。
当时,天热,吳起凤等人的尸体已腐烂了,皮肉擦伤已难分辯,罗著藻说:“蒸骨。”
褚天纬一听蒸骨,他就不高兴了,他认为尸体已朽,伤痕就看不出来,若再一蒸,还能验啥?他上前说:“慢着。罗县令……”
“放心。”罗著藻说:“毒死打死,骨上都有痕迹,你别多虑。”
“恐怕不是我多虑吧。”
罗著藻见褚天纬阻拦,也不高兴了,说:“褚县令,我是奉知府大人的命令行事的,一切由我负责。”
褚天纬无话可说了。
罗著藻手一挥:“蒸!”
褚天纬在众人面前丢了脸,滿面通红,独自坐在一边冷笑。
一会,骨蒸完了。死者个个的牙根发黑。身上的骨头却是白的。罗著藻也沒见过这种现象,问道:“死因是什么?”
“中了粪毒。”武威文答道。
“为什么是中粪毒,不是砒霜等毒物?”
“回老爷,”张德说:“小的师父传授,凡是中粪毒死的只牙根发黑,身上其它骨头颜色不变。因粪毒入口所至。比不得砒霜毒,四肢都发黑。”
“这粪水不深嘛。”
“粪积久了,都散毒气,以气伤人,同粪水深浅沒有什么关系。”赵应魁连忙解释。
罗著藻很细致,他指着祁大孩顶心左的一个黑点,问:“这是什么?”
“这不是伤。”张德用棉条展拂,说:“沒有滞碍兜挂,如果是伤,骨必破裂,会挂棉条。”他思索一会,说:这黑点是治病留下的痕迹。”
祁彦和站在一边,说:“这孩子两岁时得病,會拿艾火烧过这里,当时烧得过重了。留下个大疤。”
罗著藻点点头,问:“祁成身上有无伤?”
“沒有。”三个仵作齐声回答。
看验完毕,罗著藻朝褚天纬一拱手,说:“褚县令,小县按刚才看验的结果向知府禀报,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褚天纬搖搖头。两人分别乘轿而去。

褚天纬用严刑峻法逼供,差点造成冤案,罗著藻受命蒸骨,他又阻拦。错上加错。朱樟把三条人命案的详文层次送上去,山西巡抚觉罗石麟很快批下来,他批道:“褚天纬严刑逼供,致酿错案,罗令复审,又出阻挠。无能无识,岂能作宰?著泽州知府朱樟、解州知州王适赞共同审理。”
褚天纬等人被传到泽州府。朱樟先审祁家帮工,追究吳起风等人的死因,众人都答是中粪毒而死。既无李氏上厕所之事,也无贿赂戶亲的行为。王进贤确會答应三百文给仵作宋正祥,嘱他验尸时不要刁蹬祁秀才,目的在于怕祁家收小店,替人作人情,并未受祁轼嘱托。案情大自。当审祁桂元时,朱樟问:“你會告陈相卿索贿,到底情况如何?
“禀老爷,无此事!”
“你为何诬告?”
“犯生冤迫无伸,情急到府告状,诚恐不准,故意编造此事,好使大人重视。”“祁桂元看看陈相卿又说:“犯生也是挟嫌报复。二十一日,褚县令到村验尸,陈相卿说祁茲成脑后有致命伤,我未打人,何来致命伤,显系害我侄儿。我因此恨他,故以此泄憤。”
“诬告是有罪的。”朱樟说:“姑念你家平白遭此大难,殊堪同情,这次就不治罪了。”
最后审褚天纬。这褚大老爷此时低头搭脑,精气全无。
朱樟问道:“审讯时,为什么动严刑呢?殊不知严刑出伪供的道理么?”
“犯官私访,见店内喝茶之人言之凿凿有据,便当做实情。”褚天纬便把他在王进贤酒店两个喝茶客人的对话叙述出来。什么李氏上厕,吳起凤乘机奸污,祁大孩撞见给祁轼报告,祁轼打杀吳起凤,因怕丑声张扬,又杀祁大孩。保正祁茲成见祁轼杀人,上前敲诈,祁轼又将祁茲成杀了。褚天纬接着供道:“我审讯赵玉英等人,他们供认是中毒死的与我访闻的内容全不相同。以为是祁轼用金钱收买,预先串供好的。心里有个先入的案情,求之不得,只好用刑,以为重刑之下,必有真言。”褚天纬汗水滿头,愧悔满脸,说:“这次误判,总是犯官当日误听道路讹传之故,现在已追悔莫及了”。
朱樟也了解这个褚天纬,为人清廉,银子送到他手里,他都像捧了活炭火,扔之犹恐不及,只是判事主观,因而常办错事。朱樟喜其淸正,恼其“不明”,对褚天纬又佩服,又惋惜。他问道,“那些说是因奸被杀的人叫什么名字,今在哪里?”他想,如果找到这些人,也能为褚天纬减轻一点错误。
“犯官是在小店碰见的,不认识他们。”他把当时想找那两人交谈,讯问,由于匆忙,撞了一位酒客,发生纠缠,待纠缠停息,那说因奸被杀的客人早无踪影了的情况叙述出来,逗得朱樟也忍不住笑出声来,褚天纬不知朱樟为什么笑,说:“犯官的句句是实。”
“怎能凭此断案呢?”朱樟深深叹息。
“总是犯官糊涂。”
“那么,罗令奉委复验,你为什么阻挠蒸尸呢?”
“这也是犯官的妇人之见。”褚天纬先给自己戴个帽子:“我当时见尸体虽烂,但皮革犹存,伤是验得出的。既然死了,其罪可消,还要蒸骨,犯官于心不忍,故此阻挠。”他说着眼圈红了,似乎仍为死者被蒸伤感,他沉痛地说:“这也是犯官的错处。”
朱樟点点头,自付道:“这个褚天纬,简直善良得发呆。可偏偏动用重刑,弄得別人骨损筋伤,这又是残忍。所以残忍,又是为了除恶扶善。一做人是好人,一做官则不是好官了。”他想一个问題,问道:“明明是粪毒死人,你偏要审个因奸被杀,有无图钱财而冤陷无辜呢?”
“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名声是比钱财更重要的东西。犯官的信条是舍财取义。”他沉思一会,说:“我在审理案件时,如果索要过钱财,今日祁家因我遭受如此损失,我与祁家是仇家了。现在,我也受审,权势全无,祁家用不着害怕我了,怎还不揭露我索财贿的事呢?”
朱樟又点点头。他对褚天纬的认识更全面了;人品端正,只是疑心太重,性情愚呆、不谙吏治,难胜其任。他想:“这个好人,我同情他,却挽救不了他了。”
朱樟据实地缮写了审案详交,呈报皋台,藩台,巡抚衙门,经过重重审核,最后批复下来了:恢复祁桂元叔侄功名、安埋吳起凤三人,释放一干人犯。革掉褚天纬县令职务。一桩错案终于得到纠正了。
褚天纬丢官后,回到江南,从此不再涉足官场,因其心地纯正,成为四乡八镇有名的敦厚长者,名气比县令还大三分。
那杀死三人的看不见的凶手,实际是甲烷。粪坑肚大口小,又很深,粪便在坑里发酵,便产生甲烷,甲烷越积越浓,把氧气挤跑了。吳起凤等人下去,因无氧气,憋闷晕厥,倒进粪水里断了气。这看不见的凶手,连杀三人,还间接地让祁轼受了罪,褚天纬丢了官。
错案纠正了,真凶是谁当时谁也不清楚,它倒逍遥法外了,故此案就是未了案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