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地之角,知交半零落。一壶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问君此去几时来,来时莫徘徊……”
这首《送别》流传久远,耳熟能详。词曲的作者是李叔同,他还有一个名字叫做弘一大师。他的学生里有个叫做“丰子恺”,他还是夏丏尊的挚友。李叔同这一生可谓是“悲欣交集”,有太多说不完的故事值得后人去一一探寻。抱着对这位民国大师的好奇,最近看完了苏泓月写的《李叔同》这本书,书中用优美婉转的语言细细描绘了他曲折传奇的一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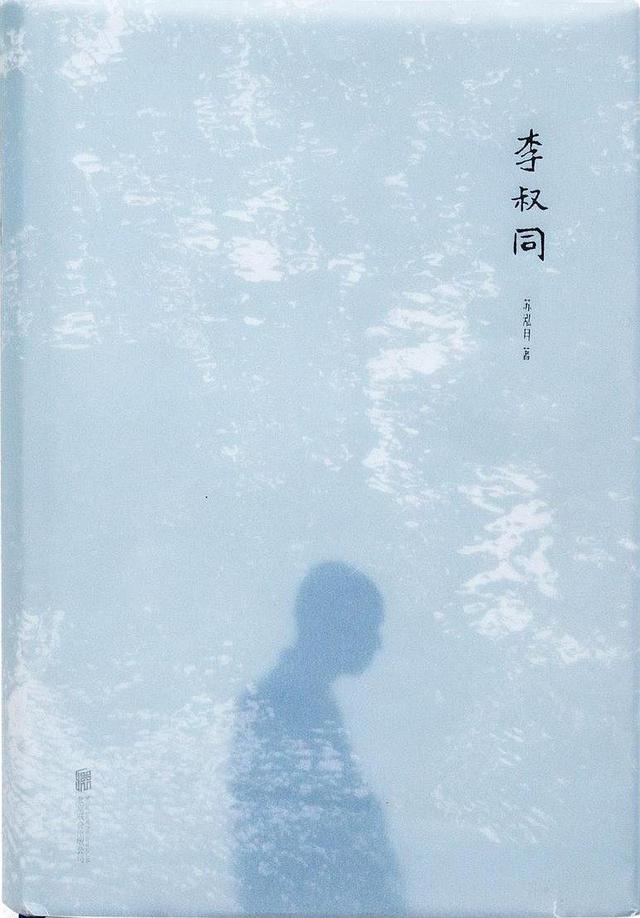
前半生他是风流才子李叔同,人间风月遍赏,后半生他是佛国高僧弘一大师,著书立说,播撒菩萨甘露。他是个大学者,琴棋书画篆刻样样精通。也是第一个将西洋美术与音乐简谱引入中国的好老师,平时对丰子恺、刘质平多有爱护和资助。但他唯独不是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甚至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一个“渣男”。因为这一生,他生命里的三个女人都很苦。

我的母亲有很多,但我的生母很苦
光绪六年九月二十,李叔同出生于天津的一个名门望族,标准的“富二代”。父亲李筱楼生他的时候,已经68岁,而母亲王凤玲才19岁。他父亲在娶王凤玲的时候,已经有了三房太太,王凤玲是四姨太,就连她的侄孙媳妇都比她年长。
老夫少妻的日子,注定是一场悲剧。幸好,有了李叔同。完成了传宗接代的任务后,李筱楼几乎再也没有跟王凤玲同过房,成日里做做佛事、修修佛经、喝喝禅茶。小小的李叔同,跟佛法的因缘也是由此而起。
在李叔同5岁那年,风烛残年的父亲去世,从此他便与年轻的母亲王凤玲相依为命。旧式的大家庭,一个失去丈夫庇护的小妾的日子有多落寞难捱,可想而知。
“我的母亲很多,我的母亲——生母很苦。”许多年后,已届不惑之年的李叔同,不,应该是弘一法师对学生丰子恺说。
多少次,她怀抱稚子,寂寞的双眼穿过草木繁茂的李家深宅,穿过游廊和阳光下的灰色影壁,望向远方,仿佛想看见儿子的未来。

儿子一天天地长大,却对科举毫无兴趣,每天谈情作画,纵情声色。王凤玲盼着儿子能够顶门立户,继承李家的生意,正正经经地做点事情,但富贵场中长大的李叔同对此毫无兴趣,依然固我。王凤玲明白,儿子不会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她只活了46岁,便去了,唯一的临终遗言是:“带娘回家”。
李叔同跪在灵堂大哭:“其实母亲这个身份在这样的社会里,是受迫害的身份!她们很苦的,生来就在樊笼里带着金枷锁,精神上的苦寂,又不轻易与人说……母亲的病,纯粹是精神上的抑郁造成的,而我就是那个杀手啊!我应该陪她一起进棺材!”
王凤玲的一生,活得寂寞又无助,虽然衣食无忧,但太过压抑。年轻守寡,儿子又耽于玩乐,很少陪伴。这份深入骨髓的孤寂,最终要了她的命。

母亲给我娶的发妻,我不爱她,任其枯萎
转眼李叔同成人,李家三公子的风流名声渐渐传到母亲和哥哥的耳朵里。他爱听戏,和戏园子里的名伶杨翠喜交好,才子佳人难舍难分。每次戏院散场之后,李叔同便提着灯笼送杨翠喜回家,两颗年轻的心炙热缠绵。但豪门贵公子终究不能娶一个戏子,母亲便开始着手替他物色妻子。
母亲选中的是一个茶商的女儿——俞氏。俞氏比李叔同大两岁,脸庞圆润白净、不艳丽也不平庸,刚好适度,神情温和恬静,看起来十分合眼缘,非常像年轻时的王凤玲。母亲看中的姑娘,叔同却百般不愿意。
二哥文熙为了让叔同答应这门婚事,提出可以拿出30万钱,在婚后支持他自立门户。母亲王凤玲,听了非常高兴,这些年在李家过得太压抑,离开这里,就能扬眉吐气地过点自己的随心小日子。叔同在得知杨翠喜被赎身卖入豪门之后,终于死心。为了母亲的心愿,叔同和俞氏成婚,一家人来到上海。

上海的花花世界,叔同如鱼得水。他的文采很快名震一方,许幻园夫妇邀请他们一家搬到城南草堂。从此后,李叔同热衷社交、沉迷诗词歌赋、耽于纵酒狂欢,过上了风流才子的生活。
家里,母亲有俞氏照料,他妥妥地做了“甩手大掌柜”,甚至妻子有了身孕依然如此。
俞氏知道丈夫心思活络,但从不过问他的事情。虽然自己有了喜,她还是每天尽儿媳本分,照顾婆婆的饮食起居,这是她的分内事,是她的使命,她的丈夫不需要她红袖添香,相伴书斋,她一切不会。
俞氏给李叔同生了3个儿子,却没有得到过丈夫的一丝温情。李叔同只不过将她当做一个家族礼物而已。初婚时不爱,生儿育女后依然冷落,而后甩下他们母子,独自一人去日本留学,在日本又娶了位妻子。回国之后,更是没有再踏入天津的家门半步,出家之后连家里寄来的信都不愿意拆,铁石心肠可见一斑。唯一一次回信,是给孙子起名字。直至俞氏病亡,都没有见到李叔同一面。俞氏这一生,走了婆婆的老路,孤独寂寞,在无望中挣扎。一个人带大儿子,替丈夫持家,丈夫却无情至此,连出家这么大的事情也不知会她,还是通过他人口中得知。可怜的俞氏,一生都没有得到过爱和尊重,47岁便枯萎死去。

日本的爱人雪子,我爱过她,但我更爱佛祖
母亲王凤玲去世后,李叔同将王凤玲送回老家天津安葬,也带回了妻子俞氏和儿子。做完这一切,他在国内的最后一丝牵挂也没了,于是抛下妻儿,径自去日本留学。
到了日本,他改头换面,给自己取名叫“李哀”,26岁,双亲健在,无妻无子,独身。他是东京美术学校西画科的新生,他正在学拉小提琴,最喜欢画油画。
他需要一位模特,美丽的19岁少女雪子闯入李哀的眼睛里。
她穿着淡色碎花和服,木屐里是一双完整的脚,是的,当她慢慢把脚从木屐里移出来,害羞地褪去白色袜子时,他看见一双如婴孩般微微泛着粉色的完整的脚,闪着贝壳般光泽的脚趾甲,一、二、三、四、五,他轻轻在心里数。脚趾甲由大及小,像刚结成的冰粒,粒粒饱满,他几乎从未见过如此漂亮的脚,这是他对女性认知的,第一双脚。
李哀疯狂地为雪子画画,最美的一幅是她的裸体画。从这一刻起,雪子全身心地爱上了这个中国男人。她从不过问他的过去,也不想知道,此刻的李哀只属于她一个人。很快两人在日本成婚。李哀终于回到中国,又成为李叔同,他带着雪子来到上海。可惜天津李家已不复当年繁华,李叔同再也不能安然地继续做个豪门公子,他得赚钱养家。天津虽说没落,但依然有口饭吃,他一点也不担心俞氏母子。但他需要养活雪子。凭着他的学识很快在杨白民的帮助下,找到一份城东女学教员的工作。
时局动荡,城东女学的薪水入不敷出。正在李叔同一筹莫展时,得到了浙江师范学校校长经享颐的邀请,去教授图画与音乐。他没有将雪子带在身边,独自一人去了杭州。
在这里,李叔同认识了夏丏尊。夏丏尊偶尔跟他提及日本杂志上的断食疗法,可以清心寡欲、重启身心。于是,李叔同给雪子写信,寒假晚归。灰布棉袍、布棉鞋,一些简单物品,不过蚊帐、洗漱、写字用具,一一齐备后,李叔同正式在虎跑寺实行断食。
正是这次断食,让李叔同生了向佛之心,此后每日烧香拜佛,抄写佛经。一年后,亲眼目睹了小说家彭逊之落发为僧后,皈依之心日盛。正月十五那天,正式拜了悟为师,剃度出家。法号演音,字弘一。从此之后,世间再也没有风流才子李叔同,只有普度众生的弘一大师。

雪子得知消息的时候,魂飞魄散,她不相信,她找到杨白民,央求这唯一相熟的朋友带她去杭州。她要见他一面。杨白民却拿出一个铜盒子和一个信封。铜盒慢慢打开,一缕胡须放在里面,拆开信,没有一个字,只有最后留给她的生活费。
西湖之西南,遥望大慈山。
山隐在暮色里,湖映出两边人。
水面波澜不惊,他衣袂飘飞,乘船而往。
她在岸边,等他靠岸。
而他只伫立船中,僧俗两界,水陆两隔。
“叔同……”她轻唤,泪水早已打湿衣衫。
“叔同已死,你看见的是弘一。”他低眉,平静地说。
“不!叔同,你叫弘一也好,我们回日本吧,日本的和尚是可以有妻室的。”她心存一线幻想。他要怎么样都行,只要还是夫妻。
但沉默是把最无情的刀,船桨打向湖面,如钝刀坎在柔软的心上。
船开动了。他最后凝望她,他的心似磐石,不见任何波纹。
自此,雪子回到日本,再无消息。雪子是他心里真正爱过的女人,虽然开始有欺骗,但日本女子的柔顺本性,使她并没有计较,一心一意地陪伴爱人。但不声不响间,李叔同变成了弘一大师,至此断了依靠。任由她异国他乡泪水翻飞、孤苦伶仃。

李叔同这一生,在家时在学问上做出许多杰出贡献,他是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最早将西方油画、钢琴、话剧等引入国内。擅长书法、诗词、音律、金石、表演等等不折不扣是个奇才。
出家后放弃了其他爱好,唯保留书法,潜心研究佛法。他为振兴律学,不畏艰难,花4年时间著成《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记》,跟晚年所撰的《南山律在家备览略篇》,后来都成为律宗的两大名著。僧俗两界里,论成就,他都是一等一的人物。但论薄情,他也是一等一的“渣男”无疑。对母亲,他未尽人子之孝,对妻子他冷漠忽视,对儿子他不闻不问,对爱人他始乱终弃。是不是一个男人只要在事业上做出成就,其他的瑕疵就能美化呢?
李叔同说起来也就是个“富二代”,靠着家族的财富过了二十几年衣食无忧的生活,用其他人的肩膀来丰富自己的人生。跟徐志摩一样的秉性,在学问上勇猛精进,但在感情上太过任性,带给妻儿无尽的伤害。这样的男人,不值得嫁,嫁给他,只会成为他人生的注脚而已。轻轻掩上这本苏泓月所著的《李叔同》,我真真是为李叔同生命中这三位可怜又可悲的女子感到伤心,她们的人生该由谁抒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