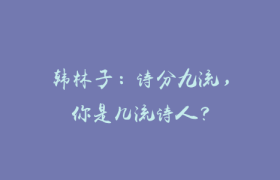爱情与死亡是文学作品中最常见的两大主题,二者常被认为最能体现人的自由意志之所在。古今中外,能写好爱情的作家不在少数,能写出真正自由爱情的却少之又少,绝大多数文本通过爱情悲剧而表现自由之不可得。如西方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中国古代传说”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以及”白蛇传”等。或许也正因为爱情这一特点,中国现当代文学常以这一主题作为反抗制度、追求自由的切入点,爱情开始越来越常见,并经历了一段非常值得关注的变迁。

现当代第一篇引起我关注的爱情主题小说是鲁迅的《伤逝》,我在这篇小说中甚至读出了尼采的”虚无”与加缪的”荒诞”,但这些不在爱情主题的讨论范围之内。我在网上搜到了《伤逝》的创作背景。”五四”时期争取恋爱婚姻自由成为当时追求个性解放思想的重要内容,20年代的小说创作,描写男女恋爱的占了全数的百分之九十八,其中最多的是写婚姻不自由。鲁迅在肯定这种反封建意义的同时也敏锐地发现了隐藏在恋爱婚姻自由背后的危机,即”娜拉走后怎样”,1928年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也表现了这一点。尼采主张否定,却在否定的同时强调肯定,意即解构必要建构。鲁迅无疑深谙这一道理,在反传统的同时也要同时考虑新的制度之可能,否则必然会产生很多问题。《伤逝》就是这一思想的文学表达,通过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表现人类亘古不变的问题——自由的难以实现。

旧社会无论什么小说都能牵扯到反封建反资本主义上去,直到解放区出现,歌颂革命的主题开始占据主流,爱情也逐渐与革命结合。赵树理《小二黑结婚》是最突出的一篇,这篇小说既是首次歌颂革命带来的”爱情婚姻自由”,也同时”规定”了爱情必须服从革命。共产党可以”让”小二黑与小芹结婚,自然也可以”不让”,爱情与婚姻实质上进入了一个新的”牢笼”。

50年代是爱情服从革命主题小说的一个兴盛时期。宗璞《红豆》、陆文夫《小巷深处》、邓友梅《在悬崖上》直至杨沫的《青春之歌》,都在这一原则之下。但此时一些作家对这种原则已经开始了一定程度的质疑,比如《红豆》,江玫虽然在爱情与革命之间选择了后者,但她无疑对齐虹保留着爱情,小说表达的正是在二者冲突之间产生的伤痛,也就是说,爱情虽然要服从革命,革命却也没有神圣到完全抹杀爱情。

这一原则一直到1979年张洁的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才正式打破。文革结束初期,人们对社会生活各方面进行反思,爱情的反思当然关乎自由,革命至高的原则受到质疑,爱情应当挣脱革命或以革命的名义套上的枷锁。这篇小说主要着眼点在于爱情,表现出的是对婚姻自由的追求。而1982年石言的小说《漆黑的羽毛》主要着眼点不在爱情,而在于个人理想与社会主义建设之间的冲突,反抗点在于制度的不合理,爱情只是一个切入点,却也反应了即使在文革之后,恋爱婚姻自由无法再受革命”正当”的干预,但制度依然对自由进行限制。80年代后期开始,陈染林白等女性作家开始个人化写作,她们作品中的爱情已经陷入了另一种新的牢笼之中,自由依旧不可得,虽然阻碍不再是明显可见的制度或传统,而是更为复杂的因素,尤其是个人因素。
下面我对石言《漆黑的羽毛》进行尝试性的叙事学分析。
《漆黑的羽毛》标题本身就很有意思。读完小说,读者明白漆黑的羽毛是指女主人翁陈静的头发,而小说语言充满了称呼上的比喻,如对陈静的称呼有”德芙”、”鸽子”和”猪圈女皇”等。交叉象征实现了文本的双重建构——表象与本质,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读者,在表象之下是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小说以讲故事的方式展开,这在文革前后相当常见,当时娱乐活动较少,思想管制较严,讲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娱乐,不少作家也真的在这种情况下得到素材,小说里作家首先提出讲故事并带着袖珍收音机就体现了这一点。那么石言可能就是听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经过改编写成小说。也可能完全不是,可能石言在写的是他自己,讲故事的方式则是小说的技巧手法,或是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事端,或是体现小说所揭示问题的客观性。一般情况下,听故事者都是第一人称,讲述者也是第一人称,第一人称嵌入第一人称,总体上形成第一与第三人称的对立,是这种讲述式小说常用的叙事角度,而这篇小说却采用第一人称嵌入第三人称之中,总体上形成第三人称之间的对立。小说首段,作家拟的酒令中要求故事”必须完全真实,不得虚构想象。”这一”真实宣言”存在于文本之中,其适用也仅在文本之中,所以小说的虚构性没有被触动,那么这句”宣言”的意义何在?这一”宣言”与刚所提到的叙事角度,这些都是为了强调小说的现实意义。也就是在虚构的基础上强调文学真实,进而强调其现实意义。一定意义上看,这篇小说属于社会问题小说,其对现实问题的揭示与思考是需要警醒读者将文本与现实进行对照,而不是仅仅作为审美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