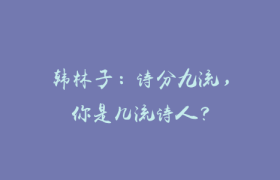日前,韩国艺人崔雪莉在家中自杀身亡,年仅25岁。外界纷纷怀疑,突然结束自己生命的她曾患有抑郁症。当一个人以决绝的姿态告别这个世界,便也带走了所有关于她的秘密与心事。尽管外界议论不断,人们再也无法打扰到她片刻的思绪。

如果你想了解一个抑郁者真实的内心世界,不妨读一读弗兰兹·卡夫卡。

第一次对卡夫卡产生好奇,还是缘于作家木心的调侃。在木心的心里,卡夫卡很像林黛玉,肺病,也焚稿,他戏言道,应该把林黛玉介绍给卡夫卡。与林黛玉不同的是,在卡夫卡的身边人看来,他是个非常幽默的人,爱讲笑话,喜欢搞些小的恶作剧,人缘很好,拍照时至少露出八颗牙齿。出生在犹太富商家庭的弗兰兹·卡夫卡,怎么看都已拥有了好文章所憎的“命达”。
卡夫卡本想保住他关于写作的所有秘密,临终前他嘱咐好友马克斯·勃罗德将他的作品“一点不剩地、未经阅读地予以焚毁”。
由于马克斯·勃罗德违背了挚友的请求,世人才得以一睹卡夫卡的文学世界:社会底层的小人物们游走在一个阴暗、扭曲的世界里,他们有的“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有的头上有一片“空洞虚无的幻景”。他的三部长篇小说均未完成,它们更像是一种关照社会的寓言,戛然而止,却让人不寒而栗。

卡夫卡以描写现代社会中人的异化和孤独见长,却让席卷世界的“卡夫卡热”持续了半个多世纪,他一生都在孤独和恐惧中写作,身后却被奉为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大师、超现实主义的鼻祖、荒诞派的先驱、“黑色幽默”的典范。
孤独与恐惧,是写作的能量
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认为,童年的创伤经历会对人的一生产生重要的影响,如果一个人有着悲惨的童年经历,长大后无论取得怎样的成就,心里终究还是有个洞。弗洛伊德眼中的“悲惨”,一般有两个指向:虐待和被忽视。卡夫卡的童年就属于后者。我们听过太多“用一生疗愈童年创伤”的故事,也可以从卡夫卡的人生及作品中得以一窥。
弗兰兹·卡夫卡出生时,他的父亲事业刚刚起步,整个家庭都以父亲的礼品店生意为焦点。卡夫卡的父亲是一个白手起家的“暴君”,不仅对员工极度苛刻,更以训斥代替管教,要求儿子像他一样坚强且勤劳。他曾因儿子半夜要水喝而发怒,将儿子从床上拽起,扔到阳台上,让年幼的卡夫卡穿着衬衫站在夜里。
母亲在家庭中是一个临时又贤惠的“和事佬”,白天她要在店里协助生意,夜晚还要陪丈夫打牌,每当丈夫和儿子之间发生冲突,她便用温柔将儿子反抗情绪消融殆尽,却始终无法给予儿子独立的支撑力量。
更为不幸的是,卡夫卡的哥哥们纷纷夭折,妹妹又是多年以后才出生的,童年时期的他承载了整个家庭的高压与冷漠。卡夫卡只得躲避父母,埋头书本。当32岁的卡夫卡终于鼓足勇气给父亲写信时,三万字的长信中尽是孤独与恐惧。
我成了一个奇想迭出,寒气逼人的孩子,怀着冷冰冰的,几乎不加掩饰的,不可摧毁的,像孩子般不知所措的,近乎可笑的,像动物般感到满足的淡泊冷漠心态。当然他也是我防止因恐惧和负罪意识而产生神经崩溃的唯一保护工具。
他曾说,“极度的孤独使我恐惧”。这封信后来被出版为《致父亲》一书,称为广大教育学者研究的样本,而卡夫卡的父亲终究也没有看到儿子这封没有勇气寄出的信。
大学期间,卡夫卡攻读了化学、日耳曼语言文学、艺术史及法律等众多学科,却始终深受哲学的影响,21岁时,他开始了写作。最初,小说片段是被卡夫卡写在日记里的,他的早期作品,他耗尽一生也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城堡》就是如此。
《城堡》的主人公K由于迷路进入了一个城堡旁的村落,为了留宿,他谎称自己是城堡的土地测量员。在村落的招待所里,筋疲力尽的K为了进入城堡与各色社会底层平民交涉。城堡虽近在咫尺,但K费尽周折,始终未能进入。
卡夫卡将K写作与自己一样的孤独与恐惧:孤身一人,在陌生的地界迷路,遇到身份各异的陌生人。卡夫卡也将K塑造成一个被忽视到底、奋斗无门的异乡人,暗含了犹太人在现实社会被排挤的事实与无奈。
木心认为,小说《城堡》具有更深层次的含义:所谓真理、自由、法律,应该都是存在的,可是荒诞的世界总是设置种种障碍,永远达不到;每当人想尽办法,以为得到一点点可能,结果又有了新的障碍。这正如小说开头对“城堡”的描写:
城堡山连影子也不见,浓雾和黑暗包围着它,也没有丝毫光亮让人能约略猜出那巨大城堡的方位。
在卡夫卡心中,也有一处永远无法抵达的城堡——极致的孤独,为此,他被困住了一生。卡夫卡41年的生命中曾三次订婚,又三次解除婚约。外界纷纷猜测,他始终对家庭生活将毁掉他的孤独感怀有恐惧,正如他所说,“为了我的写作我需要孤独”。
在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卡夫卡曾描述过自己最理想的生活方式:
带着纸笔和一盏灯待在一个宽敞的、关着门的地窖最里面的一间。饭由人送来,放在离我这间最远的地窖的第一道门后。穿着睡衣穿过地窖所有的房间去取饭将是我唯一的散步。然后我回到我的书桌旁,一边深思一边细嚼慢咽,紧接着又马上开始写作。
疏离与旁观,是故事的底色
中学时代,卡夫卡便开始接触尼采与亨利·柏格森等人的哲学思想。尼采擅用寓言写作的习惯、形象诗意的表达方式都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奠定了他此后大部分作品的风格。
写寓言的人总像先知,站在人群外,采用上帝视角俯瞰世界,告诉人们世界真实的样子和未来的走向。卡夫卡亦是如此。即使在明显带有自传性质的《变形记》中,卡夫卡也将人变作甲虫,再借甲虫之眼去审视异化的伦理与人类家庭,说出严肃又富有诗意的寓言:
青年充满阳光和爱。青年是幸福的,因为他们能看到美。这种能力一旦失去,毫无慰藉的老年就开始了,衰落和不幸就开始了。谁能保持发现美的能力,谁就不会变老。
尼采讲哲学时倾向于使用“形象思维”,将抽象的概念具像化,用意象揭示事物的本质,卡夫卡也深谙此道。用具体的形象与荒诞的故事情节讲道理,他手到擒来。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那一年卡夫卡开始动笔写作长篇小说《审判》。小说主人公是一个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而竭力证明自己无罪的人。虽然被捕,但他的行动并不受限,然而不定期的审判只要开始,就必然认定有罪,无法得到赦免。法庭并不审判人是否有罪,所谓审判不过是一种程序上的需要,区别只是“已经找上你了”和“暂时还没找上你”。

这个荒诞的故事被读者们津津乐道了近一个世纪,其中细节的象征意义众说纷纭,当人们在“时不时发现的一些暗示”中进行推理,他们忘了,卡夫卡像尼采一样批判理性。卡夫卡只是觉得《审判》在艺术上并不成功,一心想要将其列入焚毁的作品之列。
如果你能像卡夫卡凝视人类社会一样旁观他的写作,也许就能懂得他在那年8月2日写下的日记: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游泳。
斧子与爱意,是最后的告白
《人间喜剧》的作者、大文豪巴尔扎克与卡夫卡一样,法律专业出身。当年一心想要写出伟大文学作品的他为了写作曾不惜与父亲决裂,并在困顿之际花七百法郎买了一根镶着玛瑙石的粗大手杖,他在手杖上刻了一行字:我将摧毁一切障碍。
虽然此后卡夫卡曾说,他的手杖上刻着“一切障碍摧毁了我”,但面对挚爱的写作,卡夫卡有过更直白的表达:上帝不愿我写,然而我偏要写,我必须写。坚持写作还不足够,他还要写出像“能劈开我们心中冰封的大海的斧子”一样的书。正如尼采用锤子进行的哲学思考。
尼采在他的代表作《悲剧的诞生》中极力推崇“悲剧文化”,他解释道:
以坚定的目光凝视世界的完整图景,以亲切的爱意努力把世界的永恒痛苦当作自己的痛苦来把握。
相信青年时期的卡夫卡读到这句话时,内心一定深受触动。虽然一生以荒诞的外表游走在晦涩的文字里,虽然极少袒露自己的心事,他还是没能完全掩盖住他所秉持的“独特的人道主义”(木心语,出自《文学回忆录》):
谁若弃世,他必定爱所有的人,因为他连他们的世界也不要了,于是他就开始察觉真正的人的本质是什么,这种本质无非是被人爱,前提是:人们与他的本质是彼此相称的。
www.dushu2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