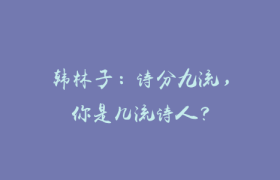古人崇尚清奇、简静、淡雅的画风,追求笔墨的纯净与透明,实际是追求心灵的质量。为了与自然一致,古来大多画家的生命态度保持着一种低调的寻常状态。低调是一种境界,很像一种信仰:艺术与生命合一,成为生命的展开与完成,而不是换取世俗利益的手段。只有这样,笔墨塑造的形象才能净化自己及他人。
在中国画中,由法而理,由理而道。道,便是中国画的最高学问。老子说:“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六朝王微说,绘画是“以一管之笔,拟太虚之体”。[1]这个“太虚”,大约就是“道”。同时代的宗炳说得更明白一些,“圣人含道暎物”,“山水以形媚道”。[2]这些早期的经典理论,规定了中国画的大致特点–“追太虚之体”。这是亲自然而远世俗,造型取其意象而淡于写实,强调精神主导,以道心观物。宗炳又说,绘画的目的是“畅神而已”。[3]
按老子和庄子的哲学,笔墨的修为离开世俗越远越好,尤其山水画,最好按“天人合一”的方向走下去,人间烟火气越少越好,从而实现“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境界。这种观点颇类今天的生态环境意识。所以,中国画不追求快节奏和高效率,而是从容不迫,如行云流水,是静下来、淡下来、慢下来的艺术。宋人“五日一石,十日一水”的观点便是这种一咏三叹的状态。这有些像太极拳,不绝如缕而又绵里藏针,令人周身通泰,体强心健。按历来的画论,中国书画从来就长于纯净心灵、陶冶灵智。所以,儒家把琴、棋、书、画作为造就理想人格的修为手段。而书画一途更能“涤烦襟,破孤闷,释躁心,迎静气”[4],是祛病增寿的良药。
西方人对中国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但他们更看好的是清代以前的中国画。他们虽然不易看懂山水画笔墨艺术的形式,但他们能感受到中国山水画里的精神旨趣,理解人对自然界的向往。他们完全接受中国画不表现张力,不强调形式感,不注重视觉冲击的特质。接受着那种与西方绘画不同的另一种趣味。中国画追求内美,初看可能很平常,但会久看不厌,人们能看见画家的心灵在笔下浮动。须假以时日去感受一幅好画经久的魅力。早在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曾评董源画说:“近视几不类物象,远观则景物桀然……”近观远观在郭熙的《林泉高致》中解释为“远取其势,近取其质”,这个“质”就是笔墨的质量。
南齐谢赫“六法”讲“气韵生动”[5],正是指“人”与“天”相通相融反馈互动所形成的一种生机勃勃、动静有序的生命韵律。这的确与西方重“形象”之画法有所不同。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儒家、道家、释家都受到“天人合一”精神的浸润和陶冶。所以,在中国古代画家的作品中,我们可以体悟到一种浓厚、深远、真挚、素朴的天人之情。画家如此,诗人亦然。在先秦哲学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古代画家建立了一种视万物为一体的宇宙观,认为人与自然的合一意味着人与自然的互相包容。如《庄子·达生》篇所说:“灵台者,天之在人中者也。”“灵台”即心,这是讲人心中包含着天地自然。《礼记·礼运》篇说:“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刘勰《文心雕龙?原道》篇据此而提出的人“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等,都是这一思想的延伸。当自然成为人的自觉的审美对象后,这一思想得到了更大的弘扬和更深入的表现。晋宋时期人们欣赏山水,由实入虚,超入玄境。画家宗炳云:“山水质而有灵趣。”晋宋人欣赏自然,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的超然玄远的意趣。这使中国山水画自始即是一种“意境中的山水”。宗炳画所游之山水悬于壁上,对之云:“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郭景纯有诗句曰:“林无静树,川无停流。”这玄远幽深的哲学意味无不渗透在中国古代画家的审美感受中。
笔墨文化是由中国哲学派生出的心灵艺术。由笔墨表现而成的“心象”与由自然到二维平面的“形象”有着本质的差异。所以,中国描绘自然的画不叫“风景画”,而叫做“山水画”。这是因为笔墨不是仅用来描摹自然的,是在创设第二自然心象的过程中表达心灵的诉求和审美理想。中国绘画崇尚简淡的原则:以墨或极少的色,用二维的方式描绘物象,并且有节制地利用空间。所谓计白当黑,这是艺术的极简原则,由它产生的艺术作品自然比不得西方古典油画那般具体细致而逼真,但中国人注重的是“传神”而非“传形”。为了这个“神”,哪怕牺牲形象。“形象”牺牲换得了“心象”即是成功,按照庄子的观点,对于个人来说,一切存在都是非真实的,只有画家自己活生生的生命是可以把握的唯一真实,而这生命和生命本身的诸般情感也是稍纵即逝,将情感的痕迹留在纸上,变得可以辨识,可以感受,可以玩味。中国的文人画家们以自身为自然抒发的基点,他们相信自己内心的体验,相信自己已经窥知了宇宙的精蕴,相信自己笔底下不假思索流露出的韵律与形式,正是自然最真实、最深刻的存在。于是,就把这种主观感受表达出来并形成图像–这就是“心象”。因为心象,而有了对心灵质量的要求。
古人崇尚清奇、简静、淡雅的画风,追求笔墨的纯净与透明,就像其追求心性之高洁一样。为了与自然一致,古来大多画家的生命态度往往保持着一种低调。因为低调,盈得更多的时间,从容地体味艺术的深刻性;因为低调,避免了很多与艺术无涉的生活内容,与艺术的纯粹性靠得更近。更重要的是,自省往往是艺术家的操守,在过程中享受艺术的愉悦。从纯化心灵的角度、自我角度看,过程即是笔墨艺术的自我意义。在这一基础上,艺术会更纯粹,也才能真正“成教化,助人伦”地发挥社会功能。低调是一种境界,很像一种信仰:艺术与生命合一。讲求心灵质量的完美。所以,真正的大家不仅是一位笔墨实践家,更是一位有人文关怀精神的人,通过笔墨映现出生命的本真,这种状况下笔墨塑造出的形象才能净化自己及他人的灵魂。
纵观历代绘画大家,为人真诚坦荡,为学探求真颐,因而其作品境界幽远深沉。《乐记》中说:“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传统艺术以“静”来抑制人动物性的本能冲动,从而达到“天地和”的理想状态。因而,传统的绘画作品不仅隐含着个体情感的信息,更注重了人性情感的传递,往往展现出温文尔雅、文质彬彬的君子风范。抵达庄子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在画面中,不论山川河流、亭台楼榭,还是人物走兽、花草鱼虫,皆透露出画家中和平静,追求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审美心胸,隐匿着画家人格自我完善的印迹。
“静”,这种中国式的审美气质承载着传统艺术的优良文化基因,曾经一度为世人所崇敬。“静”则深,能思考更深层面的问题,体现了人性的自觉和人文精神。然而,近百年来,画家身上那一份“静”的文化基因,却在所谓时代大潮的喧闹中悄然消逝。那些抄袭西方艺术样式的艺术也仅靠贴上一个民族艺术的标签,诸如“中国符号”之类,以展示“民族精神”,实则已与民族精神相去甚远。
历代画论提出“清心地”“善读书”“却早誉”“亲风雅”“不可有名利之见”,不能“沉湎于酒,贪恋于色,剥削于财,任性于气”等,是说高尚的人品能影响到笔墨。明代李日华在《紫桃轩杂缀》中说:“文徵老自题《米山》曰:‘人品不高,用墨无法。’乃知点墨落纸,大非细事,必须胸中廓然无一物,然后烟云秀色,与天地生生之气,自然凑泊,笔下幻出奇诡。若是营营世念,澡雪未尽,即日对丘壑,日摹妙迹,到头只与髹采圬墁之工(指漆匠、泥水匠)争巧拙于毫厘也。”清代沈宗骞说得更具体:“笔格之高下,亦如人品,故凡记载所传,其卓乎昭著者,代惟数人,盖于几千百人中始得此数人耳。苟非品格之超绝,何能独传于后耶?”然后,沈宗骞指明了道路,说:“夫求格之高,其道有四:一曰清心地以消俗虑,二曰善读书以明理境,三曰却早誉以几远到,四曰亲风雅以正体裁。具此四者,格不求高而自高矣。”这种具体的要求几乎成为画家,尤其是文人画家的自觉意识,进而成为自觉状态。数百年而流传,形成了古代画家的做人传统。
清代画家盛大士曾著文批评世风,和今天有些相像,他认为“近世士人沉溺于利欲之场,其作诗不过欲干求卿相,结交贵游,弋取货利,以肥其身家耳。作画亦然,初下笔时胸中先有成算,某幅赠某达官必不虚发,某幅赠某富翁必得厚惠,使其卑鄙陋劣之见,已不可向迩,无论其必不工也,即工亦不过诗画之蠹耳。”[6]
画家的浮躁心态在画面上是能反映出来的,那种力图取悦于他人的作品常常有“做”的刻意,情不真无以动人,连自己都敷衍,如何能打动观者呢?所以,画面的深层问题与人品关系至为密切。
人品不高,难得有境界。中国古代有一种对画家极其严厉的批评–俗,并认为“俗病难医”。但清人王概开出药方:“去俗无他法,多读书则书卷之气上升,市俗之气下降矣。”[7]往往是俗人不读书,少读书,或读不进去书。作画一味求熟练,须知“熟”与“俗”就隔着一层纸。“熟能生巧”,巧则落得下乘。熟而巧便是匠人了。而熟后生才是艺术的活路。不读书,不注重修养和体悟,很难达到“熟后生”的境界。
明代画家董其昌强调心悟,强调以心应物,以情应心,作画不为造物役。董其昌的书画艺术没有功利色彩。在他的心中,艺术完全是心灵的需要。他写字作画,进入了一派安详宁静、散淡冲和的状态,心与作品融为一体,绘画不再是一种负担,而成为没有痛苦,只有愉悦的享受。正因如此,董其昌从书画艺术中发现了“烟云供养”的养生之道。他写道:“画之道,所谓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这句话被历史一直证明着,这正是中国书画艺术的奇妙之处,大约也是让西人难于理解的地方。[8]
董其昌还认为,“绘画之事,胸中造化吐露于笔端,恍惚变幻,象其物宜。足以启人之高志,发人之浩气。”在他看来,绘画是高尚其志的精神活动,不是随便玩玩的,而代表着一种精神的追求。董其昌主张艺术家要纯洁自己的心灵。因为只有纯净、静谧的心灵才能抽绎、表现出天地的大美,像倪云林那样,“洗尽尘滓,独存孤迥”,像恽南田那样“迁移造化而与天游”,才能体验自然的精神,使澄澈的自然山川映照出自己光明朗彻的心胸;才能不事刻削,浑然天成;才能如山川之有云雾,草木之有华实,充满勃郁而见于物外。他精通禅理,懂得简约才能高华,繁缛却落下乘,故其绘画自然简淡,藏而不露,虚和空灵,进入了笔墨艺术的最高境界。
仅仅有才华是达不到这个境界的,必须要辅以知识修养和人生阅历,这也体现着中国笔墨文化的文人性特征。中国书画是需要知识平台的,没有文化的滋养,书画便失去了根基。
历代大家均持一种安详的心态。“安”是意识宁静后的自我感受与表现;详是吉祥、合善之意,是充满生气的各种美善的表现。安祥是对生命有所领悟后的一种境界,是“欢愉、自然、端庄”的综合体现,是意识领域的矛盾淡化、身心得到了统一的结果。现之于外表,就会呈现出慈祥、安稳、宽惠乃至举措自如,止其所止、行其所行,这是心安理得不为外物所扰的“自由、自觉”的境界。这种境界下的笔墨自然是轻松自然而又生机勃发的,是与宇宙天地规律和谐一致的。
徐复观认为:“中国的山水画,是在长期专制政治的压迫,及一般士大夫利欲熏心的现实下,想超越向自然中去,以获得精神的自由,保持精神的纯洁,恢复生命的疲困而产生的。”[9]但仅此产生的山水画还不能达到很高的境界。作画的动机绝不仅是逃逸。文人对山水有着天然的亲近,所谓“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是中国古典哲学反映出的人与自然高度的一致性所形成的艺术状态。画家的心地要干净,所谓“澄怀观道”,“澄怀”是“观道”的前提。优秀的作品必须建立在画家的人格德行完善的修为过程中。清代王昱强调:“学画者先贵立品。立品之人,笔墨外自有一种正大光明之概。否则,画虽可观,却有一种不正之气隐约毫端。所以,历来‘端正’二字极为重要。”这样的论述自宋以来,蔚为大观。“画如其人”已成为中国笔墨文化的古训。画家注意修养心性品格,“则理正气清,胸中自发浩荡之思,腕底乃生奇逸之趣”。[10]“绘宗十二忌”和明清以来各家论述的用笔之忌,如“忌滑”“忌尖”“忌流”“忌薄”“忌浮”“忌轻”等,也正是做人之忌。
六朝王微主张画山水要“以神明降之”。唐张彦远进一步阐述为“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到了清代方熏则更具体为“画家一丘一壑,一草一花,皆使望者息心,览者动色,以为绝构”。画家王原祁结合笔墨实践指出,笔法“可以通性情,释犹豫,画者不自知,观者得从而知之”,画已进入调息状态,与养生相关,故“古来各家享大耋者居多”[11],画家长寿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中国古典哲学认为,宇宙自然生生不息,人体也是真气流转,关照笔法应是元气充沛,如行云流水。当外部的不利环境影响到心理和生理时,元气会产生变化,出现气虚、烦躁等,反映在笔墨上乃出现“浮”“躁”之气。修养不够时,难以克服。而一味讨好市俗,急于求得别人的赞扬的画家,则常出现匠气。所以,养气是中国画家的功课,要能做到气脉不断、笔不困、墨不涩,元气安稳、神闲意定。勿促迫、勿怠缓、勿陡削、勿散神、勿太舒,务先精思天蒙。山川步伍,林木位置……以我襟舍气度,不在山川林木之内,精神驾驶于山川林木之外。这里已透露出“气韵”的妙诀–心神高远笔自深厚,心境旷达境自高迈。
如此看来,当代画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洗尽尘滓”的问题了。
注释
[1][2][3] [南朝·宋]宗炳:《画山水序》,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5年。
[4] [清]王昱:《东庄论画》,见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87页。
[5] [南朝·齐]谢赫:《古画品录》,见王伯敏注释:《中国画论丛书》,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59年。
[6] [清]盛大士:《溪山卧游录》,见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257页。
[7] [清]王概:《画学浅说》,见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102页。
[8] [明]董其昌:《画禅室随笔》,见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720页。
[9] 徐复观:《中国艺术精神》,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页。
[10] [清]王昱:《东庄画论》,见俞剑华编著:《中国画论类编》,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6年,第189-190页。
[11] 周积寅编著:《中国历代画论》,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07年。
程大利: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画学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