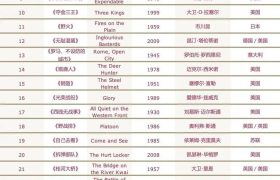这是陈凯歌对民族命运的侧面写照,也是对经历过此类神话破灭的人的体认。电影中的老瞎子自己走下神坛,成为了历史中的“牺牲者”与“无辜者”,这也是陈凯歌对那些虚无的形而上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伍辉

有学者曾论,20世纪80年代的先锋文学“一个以启蒙主义思想为内核,以现代性的价值标尺为指向,以现代主义的表现方法与文本追求为基本载体,以一个不断幻形递变的系列文学现象为存在形式的文学与文化的变革潮流”,时代浪潮中的“中国第五代导演们”也将“先锋文学”影像化,用美学与电影语言的高度浓缩塑造了电影中有关民族命运主题的寓言。
但自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以来,中国社会进入了文化转型期,以商业和和娱乐为核心的大众文化语境扑面而来,文化与影像也开始出现了转换。

王岳川先生曾如此论述道
“对‘精神理性’的关注日渐让位于对‘感性肉身’的关注,‘生命’变成了一个本体论的重要范畴。从世纪之初的尼采、狄尔泰、西美尔、伯格森的生命哲学到以后的存在主义哲学以及福科和拉康哲学,都将生命作为理性化本质飘散以后意义空白的填充物,于是,现代性标明这样一个事实:感性肉体取代了理性逻各斯,肉体的解放成为‘现代性运动’中的重大母题。”
张艺谋所执导的《红高粱》明显是带有感性色彩的娱乐性艺术倾斜在里面,而同年陈凯歌所执导的《黄土地》却依旧是在“理性”上的自我决绝抗争与孤独的救赎。

张艺谋所执导的《红高粱》在以西方语境为主的世界电影圈内大获全胜,给第五代导演们提供了,在压抑封闭诡瑰丽的民族文化空间里讲述着生命如何解放和感性主体如何抗争故事的蓝本,陈凯歌最终也选择了这种蓝本。
1991年,陈凯歌执导了《边走边唱》,学者将其编入“中国第五代导演序列作品”之中。作为陈凯歌早期所执导的作品,是“第五代导演们”的“民族史诗自叙”的重要之作,但由于陈凯歌一度“矛盾”与“妥协”,也让《边走边唱》也被认为是其精神的自叙传,是陈凯歌转型过渡的重要独立电影。

边走边唱
影片改自史铁生的中篇小说《命若琴弦》,小说主要讲述的是”老瞎子倾其一生心血弹断了1千根弦,结果却发现师傅给的治疗药方却是一张无字的白纸。” 故事虽简单,但陈凯歌对小说进行大幅度的改动与删减,遮蔽了原来小说的主题“人与历史的命题循环”。
这种散落在民间的人生朴素感悟,在电影中被陈凯歌用多重化于所糅杂消解,他更希望看到朴素的人与朴素的情感,用大的视角与小的消解去重新获得民族文化身份的认知。但时代与民族认同的焦虑却也让陈凯歌希冀能获得以“西方中心主义”意识形态为主的世界电影圈的认可。
这些都造就了哈姆雷特式文化英雄的踌躇与孤独,侧面写照陈凯歌自己的生命意识与文化形态,他在通过《边走边唱》在向娱乐与电影国际化进行“协调”与“沟通”。

瞎子
整部影片强调的是“看”与“被看”的关键词。老瞎子是希望能够通过师父给的药方看见世界的色彩的,而这个药方也恰恰是整个老瞎子看到世界的途径与方式,
“瞎子”是整部影片的关键设定。师傅给的药方能给老瞎子带来光明看见世界,药方是老瞎子能够睁开眼看世界的方式和途径,同时老瞎子也是通过药方最终完成了自我形象的确认。影片中的配药虽然是主要线索,但还暂时不能够成为个人与民族命运共同体和遭遇。陈凯歌刻意加了一场:老瞎子唱歌化解孙李两大家族的仇恨与斗争,这才使得影片完成了个体与民族命运的共同遭遇的母题。

在“瞎子”的设定上,其实是类似于“疯子”与“小丑”的设定,如同在姜文所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古伦木”的存在就是起着“警示”与“反思”的作用,他看着马小军与众人的随波逐流,而他自己在封闭的空间内自我洗礼。等到了《边走边唱》,“瞎子”也成为了“警示”与“沟通”的作用,他是沟通精神与文化世界的桥梁。
那些精神上或者文化上的盲人构成了社会的残疾,而这些都只需要老瞎子唱歌才能调停。这个设定,也正是陈凯歌借盲人的“眼”,去看到整个世界的残缺与焦虑,这也是陈凯歌叙事与寄情的主要动力。

神坛
陈凯歌将“老瞎子推向了神坛”,却用“民众无限的崇奉”来完成这场仪式。这种自信与自我,确立了老瞎子的中心地位,但是配药的那场戏却又完成了历史的虚无与无辜者的自述。当师傅所给的无字药方拿出来的时候,把老瞎子的中心也给放逐了,把主题撵出了虚幻的中心。
老瞎子不过甚至是连普通人都不如的瞎子而已。而所谓的无字药方不过是写照了老瞎子的自我形象,当那个吸引,诱惑,支撑着寄托消失殆尽之后,他自己也开始变得虚无与焦躁起来。
这是陈凯歌对民族命运的侧面写照,也是对经历过此类神话破灭的人的体认。电影中的老瞎子自己走下神坛,成为了历史中的“牺牲者”与“无辜者”,这也是陈凯歌对那些虚无的形而上性的意识形态的否定。

束缚
老瞎子自己走下神坛,但也开始了寻找了自己新的形象。原来的启蒙者陷入了失语的困境,这是陈凯歌寄寓对陈凯歌对本土“国民性”的批判和历史的文化深刻反思:历史的偶然与模式的可能性,加强了老瞎子的个人力量与社会定位,并在后来的社会系统中不断被加以创造与神话,说明还是“时势造英雄”但在这个万压的集体力量,又总是能够把个人力量所压制。

老瞎子最后承认自己不过只是个瞎子,但村民们却依旧还是请求老瞎子帮他们驱逐黑暗,迎来关明,即使已经告诉众人真相,却依旧还是想象愚昧与无知。影片的最后小瞎子把老瞎子留下的药方留在了神像面前,把兰秀的自画像装进了自己的琴匣,说明他任然坚持这种看世界的方式。
他制止村民抬行,独自踏步向前走去,他拒绝中心位,不愿意像师傅老瞎子一样被历史局限于束缚。陈凯歌对这师徒二人的不同定位,是他已经意识到文化语境下的大众与平民意识铺面开来,而那些精英阶层与知识分子意识已经正在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不再居于历史的舞台中央。

寓言
杰姆逊曾指出: “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力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
陈凯歌是诗性导演,他的电影通常是用“民族的宏大视角讲述普通人故事的同时,包含对整个民族集体的叙事”,所以到了《边走边唱》即使对启蒙者语境失语的某种暗喻,也同时提出了神话破灭之后的文化重构。

电影《边走边唱》是陈凯歌在20世纪90年代之初的“境遇意识”的产物,也是陈凯歌为自己理想主义的最后的挽歌。他与其他“第五代导演”一起走下神坛,被文化放逐,优越感失存下之后。他们也在开始思考自己要到哪里去,要去哪里。他们自己仿佛也成为了那个瞎子,行成了一个圆形的封闭式的轮回,历史的轮回让他们难以抉择,但也依旧要活出自己的人生意义。
因此《边走边唱》不仅仅是寓言与哲学的探讨,是陈凯歌诗性的表达,也是陈凯歌自我的精神作品。人生道路是曲折的,选择觉醒代价虽大,但路终究是要一直走下去的。

参考文献
[1] 李欧梵、罗岗《视觉文化·历史记忆·中国经验(代序)》,引自罗岗、顾铮主编《视觉文化读本》,广西师大出版社2003 年版
[2] [美] 弗雷德里克·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18页。
[3] [法]罗兰·巴特《神话——大众文化诠释》,许蔷蔷、许绮玲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23 页。
[4] 储双月 感性生命·启蒙话语·民族寓言 ——重读《边走边唱》